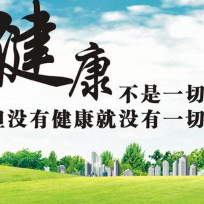凌晨四点半的城郊公交站,我裹紧褪色的工装外套,看着手机地图上蜿蜒的紫红色拥堵路线,把冻僵的手指贴在豆浆杯壁上。这是我来上海工作的第三个月,也是第89次被地铁早高峰的人流挤掉第二颗纽扣。当身后大叔的煎饼油星溅在刚干洗的衬衫上时,我终于在备忘录里写下:必须买车。

我把全家桶套餐从外卖清单里划掉那天,母亲打来电话:“你爸腰伤复发了,县医院让准备两万...”存折上的数字变成五千七的那个雨夜,我在24小时便利店数了137枚硬币,给老周发了条“再留它三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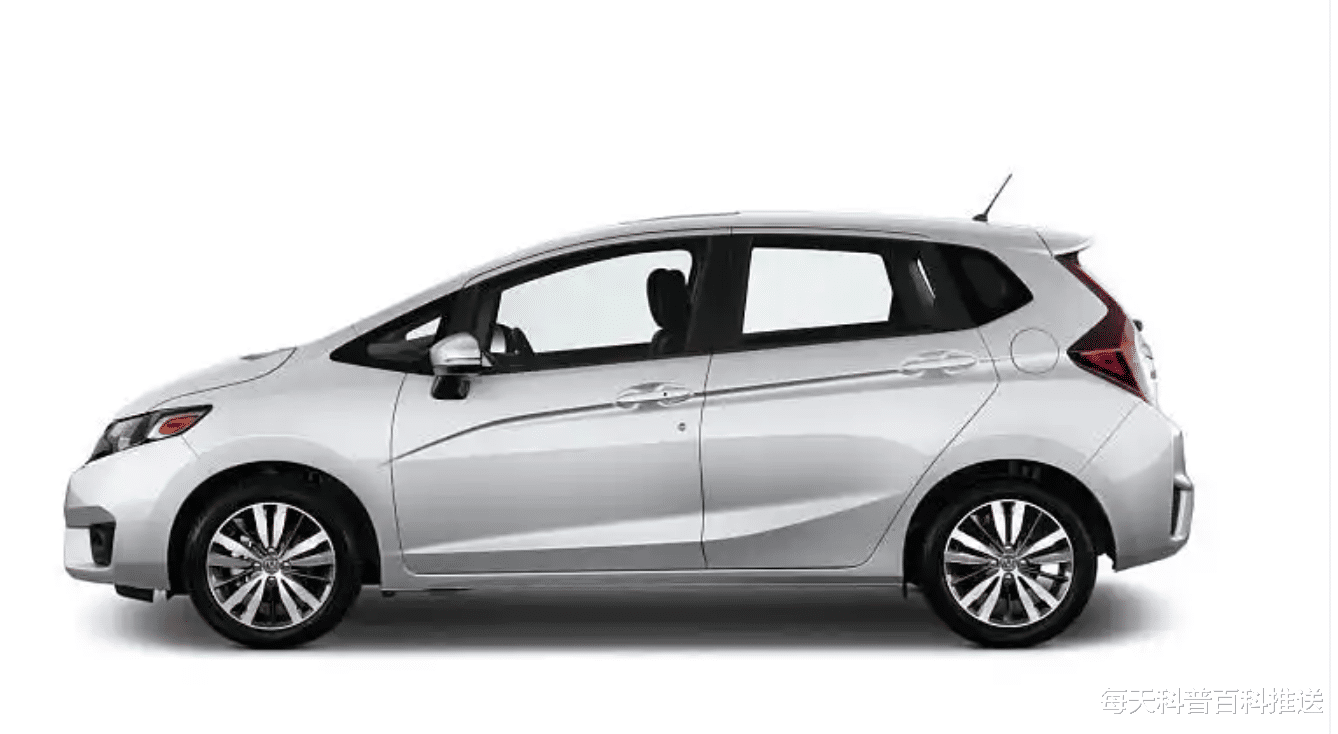
第二场雪落下时,老周发来视频。那辆飞度停在梧桐树下,仪表盘里程数定格在86666公里。后视镜上系着的红绸缎褪成粉色,却让我想起离家时母亲塞进行李箱的红枣。
车管所大厅的空调喷着白雾,我攥着大绿本看工作人员敲钢印。忽然瞥见老周在门外搓着手哈气,黑色貂绒大衣肩头落满雪。“送你个礼物。”他掀开后备箱,里面躺着全套工具包,扳手上系着中国结,“当年我媳妇就是坐这辆车嫁给我的”。
第一次开车去甲方公司,保安指着掉漆的轮眉皱眉。我却看见挡风玻璃上跳动的光斑——那是穿过梧桐叶的阳光在模仿当年城中村的月光。导航提示“途经延安高架”,车载收音机突然响起《夜空中最亮的星》,副驾上给父亲买的膏药袋沙沙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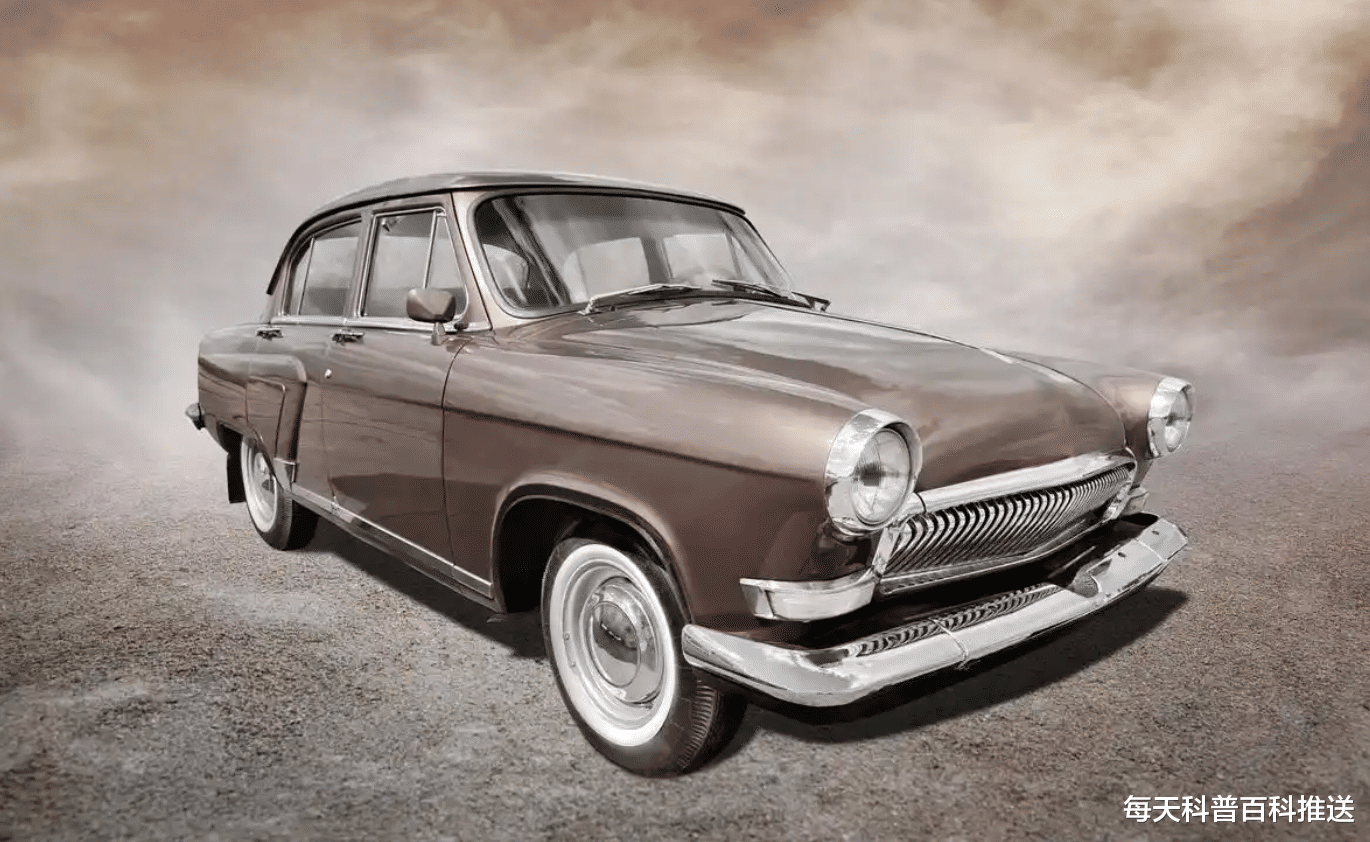
上周在充电站遇见个盯着车发呆的年轻人,他工牌绳磨得起毛边,像我当初别着25元胸针去面试的模样。“这车...很贵吧?”我按下后备箱按钮,露出里面折叠电动车:“要搭一段吗?雨刷器左边是除雾键。”
或许每个奋斗者的第一辆车都是艘诺亚方舟,载着深夜加班时的泡面香气,副驾上父母的叹息与期望,后视镜里不断远去的昨日星辰。当你们看到这篇文字时,我的老飞度正停在苏州河畔,后备箱里装着要捐给山区学校的200本旧书。它的引擎声依然像老式打字机,继续书写着下一个春天的故事。
感谢您与我共乘这段旅程
如果您也曾为某个目标咬紧牙关攒过硬币,或正握着方向盘在人生路上跋涉,请为这份普通人间的温暖点个赞;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车辙印记;关注我,让我们在各自征途的鸣笛声里,成为彼此的后视镜。前方匝道即将分叉,但那些共享过的星光,永远在油箱里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