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著名民歌歌唱家郭颂,带着一首《乌苏里船歌》震撼了整个乐坛。
下至国内的民俗音乐界,上至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音乐界,皆被这首幽婉而绝妙的民歌给迷得神魂颠倒。
尤其是后者,更是在1980年时,将其录入联合国的国际音乐教材中。
而身为演唱者的郭颂呢,也因此而红极一时,甚至还因此成了东北民歌的宣传大使。
再加上他本人在出道以来洁身自好,且没有半点黑料的缘故。
彼时的郭颂,无论是在发展上,还是在名气上,都站在了乐坛顶端中的顶端。

顶端到什么地步呢?纵观同时期的民歌歌唱家们,几乎没人可以比郭颂更加成功。
可正当郭颂打算去安享成功的晚年时,曾一度被他视为骄傲,视为荣誉的代表作《乌苏里船歌》,却在某些有心人的针对下,成了致使其走向“陨落”的关键。

2001年一场有关“创作版权”的官司,在极短时间就登顶了国内外各大知名报纸的“头条”。
也许某些不明真相者,会觉得它何德何能,可真当他们去了解这场官司的具体内容时,却又能惊惧地察觉,这场官司的“登顶”其实并不奇怪。

在那一年,已有七十多岁高龄的著名民歌歌唱家郭颂,却因代表作《乌苏里船歌》侵犯了赫哲族民歌的著作权,也伤害了赫哲族的民族感情,甚至还要其去赔偿整整五十多万的巨款(以当时的角度看)!
可刚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人们还觉得奇怪,任他们怎么也想不通,郭颂这位优秀的歌唱家,怎么能跟抄袭搭边呢?

纵观郭颂老先生这一路,他总是兢兢业业从不弄虚作假,甚至连一点品德败坏的事都不愿去做,这样的人真的会成抄袭者吗?
至少,大部分得知消息的歌迷打心底不信,甚至还一个劲地想还郭颂一个清白。

但遗憾的是,在第一次判决中,法院不光站在了原告一边,甚至还判决郭颂赔款,让他去登报道歉。
让他去以一种诚恳的态度表明,这首享誉全球的名歌《乌苏里船歌》并非由他作曲,而是由赫哲族(原告)的民歌改编而来!

由于当时的老百姓对“什么是创作版权,创作版权又如何去定义”知道的并不清楚,再加上郭颂在官司中显出颓势的缘故。

不明所以的老百姓们,真的就觉得这首《乌苏里船歌》是郭颂的“抄袭”之作,甚至还对这位曾享誉全球的顶级民歌歌唱家一面倒的攻击。

“我是抄袭?可我怎么能是抄袭,又怎么该是抄袭?!”
在被人打上“抄袭”标签后,心急如焚的郭颂老师一面与身为原告的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对峙,一面又焦急地在公众面前澄清。

可这标签啊,一旦被打上就极难以撕下,而这也一度让郭颂老师,成了无力反抗的“众矢之的”。
在撕不下“抄袭”标签的那段时间,是郭颂人生中,最黑暗,且最为绝望的时段。

那时的郭颂老师不光一身清誉被毁得干净,就连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过度伤心的缘故,而加重了本能好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甚至还直接给郭颂老师的人生,踩了“加速”。
在那之后,心力交瘁的郭颂老师被迫成了医院的常客,病得再也没法在病床上站起,甚至还在2016年5月20日上午,带着痛苦与无力,永远,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人世……

他想不通,这首被自己倾注心血,亦被自己给视为荣耀的《乌苏里船歌》,怎么就成了自己的“催命符”呢?
民歌,本是他情感的表达郭颂是辽宁沈阳人,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出生的他,即便自出生时,就遭受了战火,受尽了委屈,可他心里面,却仍对这片黑土地爱得深沉。

以至于在懂事了之后,郭颂还曾无数次地想过,自己到底该怎么去报答这片土地。
去当兵?郭颂深知自己不是这块料,至于去搞建设,郭颂也不觉得自己能真的搞好。
然而正当郭颂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位好友却让他豁然开朗。

“我看你挺有歌唱天赋的,为什么不去用这种方式来宣传你的家乡呢?”
郭颂在唱歌方面岂止有天赋,甚至都可以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天才。

要知道,郭颂并未接受过什么在歌曲方面的系统化教育,他的演唱能力,他的创作技巧,绝大部分都是靠自己自学出来的。
他甚至仅仅只是凭借自学成才,就得到了黑龙江省文工团的青睐与关注。

甚至在被调入文工团后,才情绝佳的郭颂,又在登台表演时,凭借一首《丢戒指》,便在团里红得一塌糊涂,连当时被誉为音乐界顶流的马可、李劫夫两位大家,都觉得歌唱界后继有人。
本来嘛,有这样的才华,就已经能算是一件可贵的事,但更可贵的是,郭颂这人还坚守着本心。

当其在歌唱界有所名气后,深爱东北三省的郭颂先生,又专门为东北黑龙江的劳动人民,创作了一首《越走越亮堂》的好曲子。
更令人叹服的是,这首歌,别说是东北人喜爱了,就连全国人民也都打心底喜欢。

毕竟,能像《越走越亮堂》一样赞颂劳动人民的好曲子,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而郭颂呢,也因此而在全国老百姓心底红得一塌糊涂,就连其在歌唱界的资源也变得相当之好。

可郭颂呢,却觉得还不够,他觉得自己并未能在根本性的,宣传起自己的家乡,东北。
于是乎,郭颂几位朋友便在1962年想了个招,他们打算以东北人的原始情怀为蓝本,创作出一个能更好体现东北民族情怀,民族艺术的好曲子。

因此在那年夏天,郭颂便带着王云才、胡小石等几位朋友,来到黑龙江省的赫哲族地区采风。
他们想去了解当地的族群文化,去想去体会他们的族群精神。
可还没等三人了解多久,郭颂就被眼前这个勤劳善良,且乐观积极的族群给迷住。

甚至让郭颂一下子就打定主意,一定要以赫哲族为蓝本写歌。
不过,为了写得更好,郭颂等人可谓是尽心焉耳矣。
光是给他们写歌词,郭颂等人就改了三十多版,写了整整半年左右。

再配上作曲,和演唱,其中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更是高得让常人没法想象。
不过好在这事虽然辛苦了点,但总归是做出来了首《乌苏里船歌》。
更令人激动的是,由于这首民歌被创作得过于完美,自打它在1962年问世以后,这歌就受到了全国听众的喜爱,甚至还一度将其捧上神坛。

更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歌爆红后,它不光让郭颂三人红得发紫,还增加了赫哲族的名气,甚至还让整个东北三省的民族文化,都得到了极高的关注。
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可又有谁知道,本该是一件好事的它,却被人搞得乌烟瘴气。
委屈的郭颂自打被赫哲族以疑似抄袭为由告上法庭后,郭颂就觉得自己委屈。

且不说他为这首歌的作词编曲费心费力,更重要的是,他的好心还被人当成了驴肝肺。
在这首歌爆红后,本没什么名气的赫哲族也开始渐渐为人所熟知。
这让郭颂觉得,自己应当是有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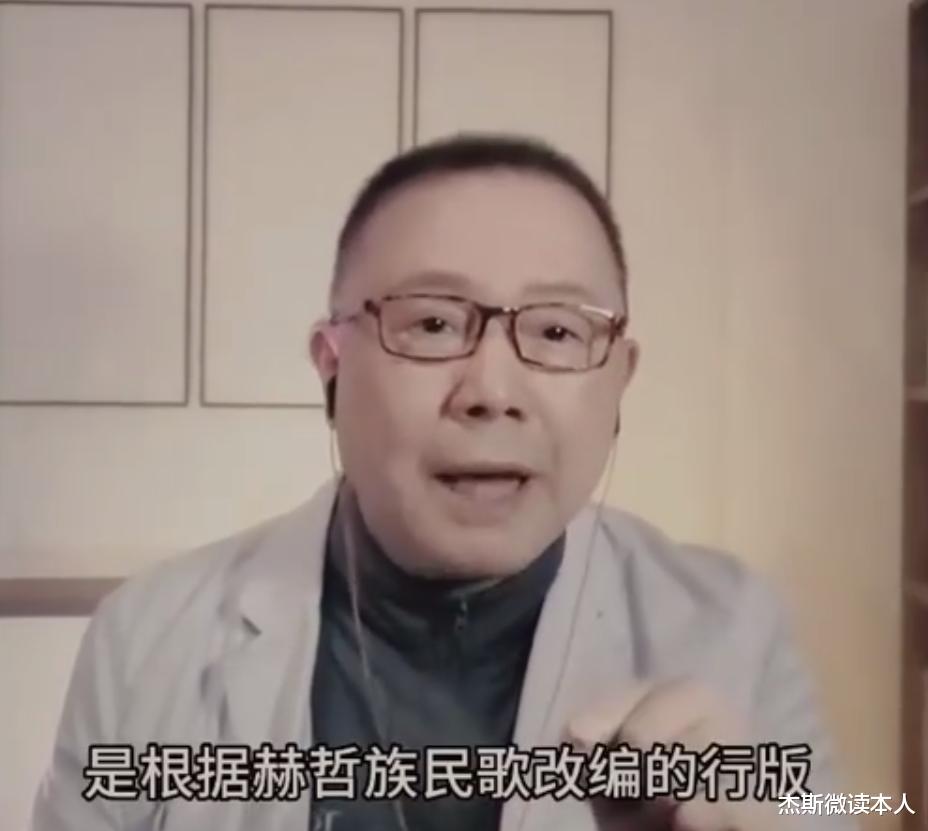
可让他没法理解的是,在这首歌成名的近四十年后,赫哲族却以《乌苏里船歌》中的某小部分的曲调与他们民歌相似的缘故,告他抄袭。
别说是当时的郭颂了,就连如今的网友都觉得郭颂委屈。

且不说以创作版权的角度来看,存在近千年的民歌,由于没有什么明确的创作者,且时间过于久远的缘故,也就谈不上什么创作版权,更何况,若连这首仅仅采用极短民歌旋律的《乌苏里船歌》都能称得上抄袭,那么绝大部分名曲恐怕都能称得上“抄袭”。
我国著名作曲家朱践耳曾表示,引用取材民歌的作品太多太多了,甚至在他眼里,引用自己国家的民歌,算是一件宣传民族文化,且应该鼓励的好事。

若连这都被告侵权,未免也太滑天之稽了。
但可惜,在那个创作版权的相关法律并未完善的年代,敢于为郭颂发声者,也就仅有朱践耳等小部分人,而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郭颂先生晚年的“悲剧”。

纵观郭颂老先生的一生,高风亮节到了极点,唯一的污点也仅仅只是这场“官司”。

甚至连这场“污点”,都是因多种原因而被迫造成的不可抗力因素。

只可惜,郭颂老先生清白一生,却在晚年被迫以此收尾,实在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