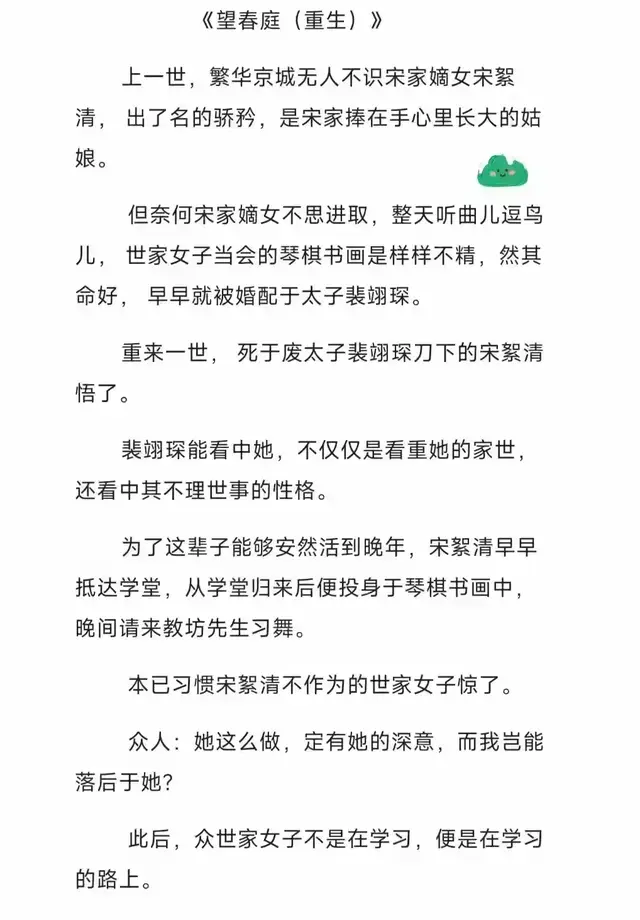我和孟迢做了十年夫妻,有名无实。
他一心为失踪的白月光守贞,对我说:「反正你嫁我,图只是侯夫人的虚名。」
后来,白月光归来,人人都说,我这个侯夫人做到头了。
孟迢安慰我:「你放心,我不会休你,往后你与她平齐,照旧是侯夫人。」
我似笑非笑看他:「也照旧守活寡么?」
他怫然不悦:「侯夫人的尊荣还不够让你满意吗?姜梨,做人要知足感恩。」
我点头称是。
却反手拿出了休夫信。
1、
孟迢来我房中时,我正在吃馄饨。
汤头清澈,葱花碧绿。
我吃的不亦乐乎,只拿余光睨他:「哟,稀客,吃饭没,要不要我分你几只馄饨。」
我嫁给孟迢十年,便守了十年活寡。
十年夫妻,这才是他第二次来我房里。
孟迢道:「不了,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想向圣上请旨,赐婚我和朝阳。」
我不答话,只用嘴吹馄饨汤。
孟迢蹙眉:「我敬你是我名义上的夫人,便不说也没什么。」
又道:「你不该有怨怼,若不是我救你,你怕早已死在北凉。」
十年前,我曾被封公主,出塞北凉和亲。
和亲队伍已经出了雁门关,却被单枪匹马的孟迢赶上,硬带回了京城。
汤吹凉了,我送进嘴里,悠悠道:「我求你救来着?若不是你横插一脚,如今我已是北凉王后。」
孟迢冷笑:「倒是我耽误你大好前程了,所以你才伙同父兄做局,给自己谋个侯夫人做补偿?」
孟迢在雁门关前那一拦,传回京城后,人人都道,定然是出于私情。
我父兄急的团团转,女子名节大过天,有此绯闻,以后我还有哪个像样婆家肯要?
于是明面上以酬谢为由,邀了孟迢来家中做客。
暗地里,却在他和我的酒里下了药。
我醒来时赤条条和孟迢拥在床上,正惊慌着,房门被踹开,我父兄冲进来,抄起桌上的凉茶盏泼醒尚在沉睡的孟迢:「好哇,你果然与我阿梨有私情!」
孟迢被逼的答应了娶我,走时,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你是想给自己找个依靠,我不怪你。」
一句话,便给我的人品判了死刑,笃定了我和父兄是同谋。
我咬着勺子笑:「你搅合了我的北凉王后,还我个威凤侯夫人,也不算冤枉吧?」
我这不紧不慢、打太极的姿态,惹的孟迢着了恼,他焦躁道:「我一早就告诉你了,我心里有别人。你已经霸占了我半世,难道还不肯知足?」
我避而不答,只舀起最后一个馄饨笑问:「就剩最后一个了,你真不吃啊?」
孟迢愤怒地起身离开。
临走,泄愤似的踹了一脚凳子。
2、
孟迢走后,我独自坐了许久。
是啊,他一早就告诉过我,他心里有别人。
十年前,新婚夜,我在洞房里独坐了半宿,红烛泪都冷透了,他的副将才匆匆来告诉我,侯爷有急事离京了。
过了小半个月才回来。
一回来就躲进了书房。
我主动去书房找他,打算与他解释那天在我家的事是父兄设局,与我无关。
我是真的,想与他好好过日子的。
解释的话在心里排练了千百遍:「夫君,我心知你对我有误会,觉得我是伙同父兄做局赖上你,但我……」
去找他前,还特地特地亲自下厨,包了一碗馄饨。
我最擅长包馄饨,我包的馄饨汤底鲜到掉眉毛,吃过的人都说,就只我这包馄饨的手艺,未来的夫婿真好大福气。
可我夫君孟迢只扫了一眼,便说:「我是北人,吃不惯江南的精致小点,你以后不必费心。」
又说:「有些话我要与你说分明。我娶你是因道义,威凤侯夫人的尊荣我都会给你,只除了感情,因为我的心里早已有了别人。」
我才当新嫁娘半个月,就知道我夫君心里有别人了。
一瞬间,满腔解释的话都化作了烟云。
万千误会易开解,一颗真心怎求得?
我点点头:「侯爷放心,我图的也原不是你这个人,是威凤侯夫人的虚名。只要威凤侯夫人是我,侯爷心里是谁,我不在意。」
亲口坐实了自己是父兄的同谋。
把孟迢眼里的自己,从「身不由己听命父兄的小女子」,升格成了「处心积虑贪慕虚荣的坏女人」。
孟迢诧异地看我一眼。
眼底那抹本就不多的温和怜悯,化作了冷冷的薄冰。
我端着那碗馄饨离了孟迢书房,回到厨房。
厨娘问:「怎的又端了回来?」
我说:「侯爷说他不喜欢馄饨这种江南小点。」
厨娘惊讶:「怎么会,以前我包馄饨,侯爷都吃两大碗呢。」
他不是不喜欢馄饨。
他只是不喜欢我。
十年过去了,他从未尝过我做的馄饨,也从没忘记过心里的那个人。
孟迢的背影彻底看不见了,我收回视线,把最后一个馄饨送进嘴里。
冷了的馄饨,一点也不好吃。
3、
惊蛰过后,百花复苏,又赶上北凉遣使者来拜谒。
故而皇后在中宫设「花朝宴」。
我这个威凤侯夫人也受邀在列。
夜来月升,梨花树下,坐满了皇亲国戚、权臣贵女。
或是夫君相陪,柔情蜜意,或是三五成群,嘈嘈切切。
唯独我人缘惨淡,独斟自饮。
不远处,与我不睦的东乡侯夫人和清嘉郡主正在嚼舌根子。
「……真正是情感动天,威凤侯找了朝阳公主十几年,终于叫他给找着了,可见苍天也是有心的。」
「我看是苍天有眼,谁不知道当初是那女人贪慕虚荣,为当侯夫人恩将仇报暗算了威凤侯,这下好了,朝阳公主回来了,那女人的美梦到头了!」
她们说的大声,好叫我在场人都听见,给我难堪。
人人都侧目看我,我却不在意,只斜倚在榻上,望着那梨花树自斟自饮。
酒意微醺时,不自觉地又想起旧事。
那年,我和孟迢初见,也是在花朝宴上。
我家祖上是世袭昌乐王,传到曾祖父那辈时,因卷进谋逆大案,被褫夺封号贬为庶人,赶出京城,去到姑苏讨生活。
我父兄惦记着祖上的荣光,每日只知道赊账喝酒哭祖宗。
我呢,我在葑门横街上挑个担子卖馄饨,好付他们的酒账。
我以为自己会卖一辈子的馄饨。
直到有一天,京里来人,说皇上赦免了我家的罪,让我们回京去。
那时,我还不知,这次赦免,是因为大云朝要和北凉和亲,皇上和得势的皇亲们谁也舍不得自己的亲女儿,便打起了我这种戴罪宗室女的主意。
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进了京,刚安顿下来,皇后就差人来传旨,命我参加今年的花朝宴。
还给了一百两银子,说置装使。
我把银子昧下,只拿出来十两,请巷子口裁缝铺老板帮我裁一身衣裳,嘱咐他能见人就行,怎么省钱怎么来。
天恩难测,万一我家又遭难呢?
不如省下银子,假如真的有万一,我还能回苏州去,买间店面,把「阿梨馄饨」做大做强。
到了夜宴那日,众贵女这个苏杭绫罗,那个巴蜀锦绣,争奇斗艳。
清嘉郡主看我寒酸,便揶揄我:「这是哪家丫鬟?小姐这样小气,带进宫也不给赐件好衣裳穿。」
我不还嘴,只乐呵呵地看表演。
正在表演的,就是刚受封威凤侯的孟迢。
他可真好看哪。
长身细腰,剑眉星目,一身皂衣,在梨花树下舞剑,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我看的目不转睛。
清嘉郡主嘲笑我:「痴心妄想,京中有的是配你的好亲事,听说礼部张尚书想要纳个妾,刑部王尚书的公子也要娶妻。」
张尚书年逾六旬,王尚书的公子么,倒是青春少艾,只可惜是个傻子。
我笑了一笑,不欲搭理。
却见梨花树下那身影纵身一跃,转瞬间,寒水般的剑蛟龙般游到我面前,剑锋上一朵梨花洁白如雪。
月光下,孟迢目若朗星:「君子佩宝剑,姣梨赠佳人,这朵梨花送给姑娘。」
4、
他听到了清嘉郡主贬低我的话。
他在隐晦地为我出头。
后来,他在雁门关前拦住和亲队伍,少年将军白马银枪地立在我马车前,一肩风雪,双目炯炯,誓言掷地作金石声:「有我威凤侯孟迢在一日,大云朝的安危便不会系于一个女子之身。」
和亲队伍回了京,满朝皆惊,指责孟迢不该把一个女子看的比国家百姓重要。
孟迢反问:「难道女子就不是大云朝的百姓?孟某与众将士在沙场浴血,为的就是保家卫国,倘若家国要靠一个弱女子扛起,那又要我们做什么?」
「何况这小女子早已不是宗室之人,未曾受过一点民脂民膏供养,诸位将自家女儿护得紧,又如何能理直气壮地把家国大义压在她肩上?」
话传到我耳朵里,百感交集。
北凉是蛮夷之地,历来和亲公主都没有好结局。
上一个和亲公主朝阳,嫁过去没两年,就因北凉内乱不知所踪。
这次和亲的对象是北凉四皇子,传说是个肩上跑马、臂上站人的壮汉,还杀过两房妻妾。
我怕的要死,百般不愿,可父兄劝我:「那是以前,说不定现在不杀了呢。」
连我娘也哭着劝我:「阿梨,你哥哥如今快三十了,连门亲事都说不上,你真忍心看他孤独终老?」
至亲之人都不在意我的死活,只想着拿我换一家老小的荣华富贵。
可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孟迢,却顶着千夫所指,将我护在身后呢。
人人都说,我嫁给孟迢,是图威凤侯夫人的虚名。
连我自己,都这样告诉孟迢。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嫁他,是因心悦于他。
至少是曾经心悦于他。
往事就酒,容易上头,孟迢在我身边坐下时,我已醉的眼都花了。
将他看在眼里,仿佛仍是当年赠我以梨花的少年。
直到他开口:「我想过了,你在意的不过是威凤侯夫人的名头,这你大可放心,我与朝阳商量过了,你们俩是平妻,你照旧做你的威凤侯夫人。」
我托腮冲他笑:「行啊,但只一件事,威凤侯夫人能有两个,世子却只有一个,以后我跟她,谁的孩子做世子呢?」
孟迢不可思议:「我和你怎么会有孩子。」
……未必,我悄悄摸了下肚子。
嘴上却说:「意思是,我照旧做威凤侯夫人,也照旧守活寡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