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伴随着法国国歌《马赛曲》,十座女性镀金雕像缓缓升起,雕像人物代表了十位在法国各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女性:有起草女性权利宣言的女政治家、有创办女子运动会的优秀女运动员、有维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女律师……法国一直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者,作为诞生过玛丽·居里、圣女贞德、政治家薇依、哲学家波伏瓦等诸多伟大女性的国度,一直致力于将男女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之一,开幕式上巴黎带领全世界致敬伟大的女性。

巴黎奥运会将有1050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男运动员5250名、女运动员5250名。这是奥运会首次在参赛人数上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从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没有女运动员参加,到现在的男女运动员各占一半,女运动员比例从0到50%,这条路走了128年。
想要清晰地了解女性主义运动的来龙去脉,确实需要关注法国,它是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阿信今天要推荐的新书,是来自法国历史学家马蒂尔德·拉雷尔的振聋发聩之作——《去他的父权制》。拉雷尔文笔犀利幽默,插画师趣味手绘漫画,这本书带我们回顾了法国至今200多年的女性主义之路。

《去他的父权制》
[法]玛蒂尔德·拉雷尔 著 [法]弗雷德·索查德 绘
通过18世纪至今,法国女性200多年的平权运动之路历经的十几个关键节点,我们看到,女性踏过多少荆棘才走到了今天。
穿长裤、接受教育与参加考试、选择工作、获得财产保护、在银行开户、申请离婚、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抗议月经羞耻、接受无痛分娩等,都是女性在时代的激流中一次次与父权制博弈而获得的。

插画师弗雷德·索查德绘制的漫画

插画师弗雷德·索查德绘制的女性主义先锋的漫画
在受到鼓舞的同时,也不得不警醒,为什么她们都被遗忘了?为什么这些极其基础的质问至今还需要被一次次提起?
争取女性的权益,是一条曲折反复的道路,任何已经赢取的成果,仍有随时破碎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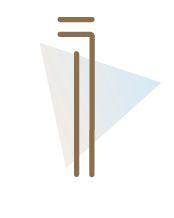
“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到“不结婚的快乐女人”
1804年,诞生于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民法典》,是罗马法体系、 法国大革命遗产,以及一些旧制度惯例的复杂混合。拿破仑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但说到女性权益,他绝对算是“第一”终结者。
依照当时的法典,妻子完全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和未成年人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丈夫的准许,女性不能工作,不能开户,不能提起诉讼,不能签署文件,不能参加考试。就算“夫君”大发善心准她上班,她的工钱也会直接转给丈夫。她唯一享有的权利是对陪嫁财产的监督权,这是婚姻契约保证的,因为陪嫁财产是家庭财富的一部分。

通常来说,夫妻双方都应当对彼此忠诚,但事实上,男女在这项义务上并不平等。妻子出轨会被视为犯罪,要吃两个月到3年不等的牢饭,而且法官常常会从严量刑。而男人呢,除非把情妇带回家,否则就不算犯罪,就算被逮住,交点罚款就可以了结。
到了1816年,“博纳尔德法”则直接禁止离婚。自此,离婚再度成为妇女需要努力争取的权利。
当时的人们还相信,有些活动非常危险,容易导致女性歇斯底里发作,比如说——读书。当年的医生坚信,阅读的女人更容易染上呼吸系统疾病,也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最终导致疯癫。包法利夫人就是一个典型。
当然,女性最危险的活动还得数投身女性权益的斗争。女权主义者们尖锐地指出,抬高家庭主妇,本质上是男权统治的烟幕弹。

争取受教育权是妇女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最早取得成果的斗争之一。
自17世纪以来,女童的教育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女孩们被教导要做好妻子、好妈妈,要学习如何持家和举办沙龙,却从有没有接受过像样的教育。
19世纪,许多争取性别平等的女性活动家是教师,其中比较知名的几位有让娜·德鲁安、波利娜·凯戈马尔、路易丝·米歇尔、波利娜·罗兰,以及后来的埃莱娜·布里翁。作为教师,她们都深刻地体会到男女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也都意识到妇女的解放必须通过教育来完成——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于是一些女性行动起来,誓要冲破这扇紧闭的大门。1861年8月16日,朱莉 – 维克图瓦·多比耶在37岁的年纪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成了第一个打破这项特权的女性。在此之前,只有男性才有权参加中学毕业会考。两年后,又一位女性,埃玛·舍尼,获得了中学毕业文凭。很快,舍尼在1868年成了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女性,拿的是理学与数学学位,而多比耶则在1871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还有一部分女性致力于为女同胞开办学校,她们满腔热忱,感人至深。埃莉萨·勒莫尼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1862年,她在巴黎珍珠街9号租下一间工坊,为年轻女孩开设了第一所职业学校。头十个月,只有80名女学生报名上课;两个月之后就翻了近一倍,一年内接收了150人。学生越来越多,只好再开办新的学校。到1890年,“勒莫尼耶学校”的数量达到了8所,培养了大约500名年轻女孩。
1972年,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向女性开放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安妮·肖皮内的年轻女子摘得了入学考试的第一名——她同时也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的第一名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第二名!
记者向她提问:“你不怕别人把你当成怪物吗?”肖皮内的回答简洁明了:“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毕竟每年总要有一个第一名。”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19世纪末开始,“不结婚的快乐女人”这一形象逐渐变得广为人知:她们大多是城里人,出身不错,有家产继承或靠年金生活,周游各国,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传统价值观指派给女性的角色一律不理不睬。
直到1967年,妇女才有权独立在银行开户;从1970年起,妇女住在哪里不用再听人吩咐了。然而,婚姻中支配权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要想在家务劳动、子女教育以及情感付出等方面平等承担义务,还有很长的路。
正如女权主义记者蒂蒂乌·勒科克所言:“女权主义的斗争是在脏衣篮前取得胜利的。”

“沉默不会保护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海报:

上面一个女人的脸叠着一层环靶的纹路,四周围绕着这些文字:
“的确,不是每个女人都被强奸过,可在大街上、工作中,我们哪个女人没被骚扰过、骂过或瞧不起过?哪个女人每次和男友或者丈夫发生关系都是心甘情愿,从来没有身不由己过?哪个女人没有过想出门玩又却步,想旅游又打退堂鼓,就怕遭到侵犯?当广告和色情作品拿女人的身体当卖点,又有哪个女人没被冒犯呢?”
你猜这张海报是什么年代的产物?
看上去,这些话格外紧跟时事,然而事实上,这张海报要追溯到1976年6月26日的一场集会。那一天,女权主义者们在巴黎的“互助会之家”公开提出了强奸及其相关量刑(不当)的问题。
针对女性的暴力,特别是性暴力,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法律的认定和制裁。
毕竟,女性赋权的形式之一,就是勇敢地对簿公堂,把那些侵犯、强奸她们的人通通告上法庭。

这句话出自奥德丽·洛德的《将沉默转变为话语和行动》(1977)
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强奸(当时称为“诱拐”或“奸污”)被视作犯罪,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人们对强奸口诛笔伐,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总是网开一面。
直到如今,我们仍旧会在法庭或媒体上看到对强奸受害者“品行”的质疑:从性取向到裙子的长度,全都可以拿来解读。

面对这样的情况,妇女们并没有缴械投降。尽管为数不多,但仍有一部分受害者坚持不懈,从地方法院一步步告到最高法院,誓要将强奸犯绳之以法,同时也迫使法学家们反思“同意”的问题。
1832年,法律先是承认儿童不具备性同意能力,接下来又将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全体女性。

我的身体,我的权利,我的选择
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妇女解放运动最初关注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人的妇女,为她们争取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一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讨论的中心从女性的社会身份逐渐转移到了女性的身体。
月经,这恼人的、顽固的身体分泌物,不是稀罕事物,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然而长久以来,所有人对它的印象都是负面的,说起来都没有好话。将月经视作一种疾病而非正常生理现象的传统,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国家阴魂不散,滋生出数目繁多的禁忌、偏见、厌恶和迷信。
女权主义斗士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破月经羞耻,鼓励人们在公开场合谈论月经。
20世纪70年代由“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编辑出版的标志性女权主义刊物《拖把在燃烧》,面世时就自称“月经刊”——以此表示会不定期更新。
她们提倡在中学和公共场所设置自动售货机,要求从幼儿阶段开始普及正确的月经教育,避免月经被污名化,敦促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的原材料透明,推进跟月经相关的感染疾病的研究和科普。
1953年,法国共产党提交了一项法案,倡议将分娩准备教育纳入社保报销体系,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
法国医师协会和右翼保守派立即表示抵制——他们才不在意产妇的痛苦……多名医学专家在著作中表示,疼痛让女性“更有价值”,为她们带来了一种“道德美感”。
直到1956年,共计9课时的分娩准备教育最终被宣布可由社保报销(1956年法案表决通过,1959年正式实施)。

阅读《去他的父权制》这本书,回顾200年来法国女性抗争的历程,时常让人边读边发出感叹:原来这个问题早就有女性前辈讨论过了?!
因为,回顾整个女性斗争的历史,几乎所有诉求都是一并提出的。
我们今天获得的权利和认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母亲曾经拥有的,而我们的母亲又比她们的母亲拥有更多的权利。
“对于每一个今天仍在为性别平等而奋斗的人来说,能够了解这段漫长而复杂的斗争历史都非常重要。”
当我们对未来的道路感到迷茫时,不妨回顾过去,未来的方向,过去已经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