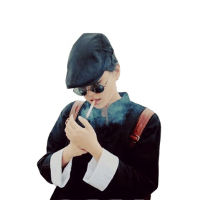"人心中的成见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哪吒2之魔童闹海》中申公豹的这句话引得无数人共鸣,道出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偏见。但细究之,这座看似不可逾越的大山,或许只是我们内心投射的幻影。
电影中申公豹的悲鸣回荡在影院,却让观众想起明代王阳明剿匪时的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五千年文明史中,偏见从来不是压垮人的大山,而是照见人心的镜子——楚霸王自刎乌江时,看见的是"天要亡我"的宿命;而司马迁受刑后,却在竹简上刻出了"究天人之际"的星辉。成见的重量,终究取决于背负者的眼睛。
苏轼:把贬谪路走成桃花源元丰二年,御史台的槐树飘落黄叶时,44岁的苏轼戴着枷锁走出汴京城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评语,像钉子般将他钉在旧党新党共同的偏见墙上。黄州江边的东坡上,这个"不务正业"的犯官却在《寒食帖》中写下"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的从容。当朝堂视他为政治负资产时,他给长江注入"大江东去"的豪迈,给岭南瘴气披上"日啖荔枝三百颗"的甜香。
在儋州贬所,土著居民最初用"汉官皆虎狼"的成见防备他。苏轼没有试图搬动这座大山,而是摘下官帽走进槟榔林,用黎族方言唱起《减字木兰花》。三年后他北归时,岛上百姓"争遗黎布"相送。那些曾经敌视他的目光,最终化作《伏波庙记》中"沧海何曾断地脉"的和解。偏见的大山没有消失,但行走其间的苏轼已活成自己的光。
王阳明:龙场驿的破壁者正德元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在诏狱中受完廷杖,带着"狂悖"的标签发配贵州龙场。当地苗民眼中,这个瘸腿汉官不过是中原抛弃的废物。在漏雨的茅屋中,王阳明看着石棺自省:"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当京城清流们忙着给他贴上"伪学"标签时,他在晨雾中顿悟"心即理"——不是程朱理学错了,而是世人把成见当作了真理。
龙场驿丞开始用苗语讲授《大学》,把中原典籍翻译成俚俗故事。当土司质疑"汉官皆贪"时,他指着衙门外的菜园笑道:"此吾俸禄所出。"数年后,书院里汉苗子弟共读《传习录》,贵阳城头竖起"知行合一"的匾额。那些曾将他隔绝在文明之外的偏见,反而成了照亮黔中山水的火把。后来宁王叛乱时,这个"书呆子"用三十五日平定十万叛军,证明成见筑起的高墙永远困不住自由的灵魂。
楚汉相争时,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却在兵法中写下"陷之死地而后生";敦煌藏经洞的写经生法成,顶着"胡僧"的偏见,用汉藏双语抄录佛经;左思写《三都赋》被嘲"粗鄙",他选择用十年光阴把"洛阳纸贵"变成对偏见的优雅嘲讽。这些穿越偏见迷障的勇者,都窥见了同一个真相:成见从来不是客观存在的大山,而是内心的投影。五千年文明长河里,所有搬动偏见大山的人,不过是先移除了自己眼里的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