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仲夏夜,5岁的海来阿木趴在阿爸背上穿越山林。月光把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老式录音机里飘出山鹰组合的《走出大凉山》。
父亲突然停步:“木啊,将来你也要把我们的歌唱给山外听。”这句话在男孩心里埋下种子,二十年后长成参天巨树。

2011年寒冬,18岁的海来阿木蜷缩在春熙路地下通道。褪色的吉他盒里零星散落着硬币,他反复弹唱自创的《甘洛河》。

女儿夭折次日,海来阿木在货运途中遭遇车祸。满脸是血的他死死护住副驾上的吉他,交警赶到时听见他哼着未完成的旋律——那是《点歌的人》的最初版本。
躺在病床上,他收到妻子离婚协议,签字笔在纸上洇出大团墨迹。护士回忆:“他整夜盯着窗外,把输液的滴答声编成了节奏。”

2015年立秋,重庆磁器口青石板路上,舞蹈教师陈琳被沙哑的歌声吸引。巷角抱琴的男人正在唱《月亮妈妈》,脚边纸板写着“筹钱录专辑”。
她连续三天来听歌,第四天带来婚庆公司的合作邀约。婚礼现场,新郎突然逃单,海来阿木即兴改编祝酒歌救场,这场意外让他收获了第二任妻子。

2024年央视春晚后台,海来阿木的化妆镜上贴着泛黄的便签纸,那是女儿出生时写的歌词片段。
与单依纯合唱《不如见一面》前,他悄悄在西装内袋放了张女儿照片。
导播切近景时,观众发现他眼角有泪光闪烁——这天恰是女儿11岁冥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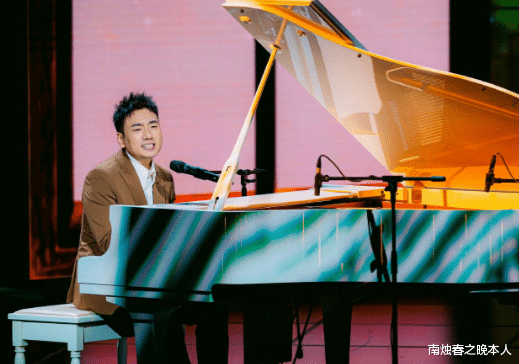
从大凉山牧童到春晚舞台,海来阿木用三十一年完成命运的逆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