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问世的《元气骑士》,凭借丧心病狂打怪兽的像素风,以及近乎“零氪”的良心设计,迅速风靡全球。
它既是独立游戏的突破口,也是一群青年开发者的梦想寄托。
正值国产独立游戏崛起浪潮,从初创失败到年入数亿元,凉屋游戏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中寻得平衡?

一、移动互联网浪潮
“那时候移动互联网风头很劲……我们就简单地报了个名,然后就把我们飞回来了。” ——曹侃
2010年代初,移动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投身其中。
彼时,曹侃和李泽阳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受到投资机构的高度关注。
曹侃提到,真格基金当时正在“搜罗”各个学校里的华人项目提案,对于回国创业的想法,他们原本就已有深层次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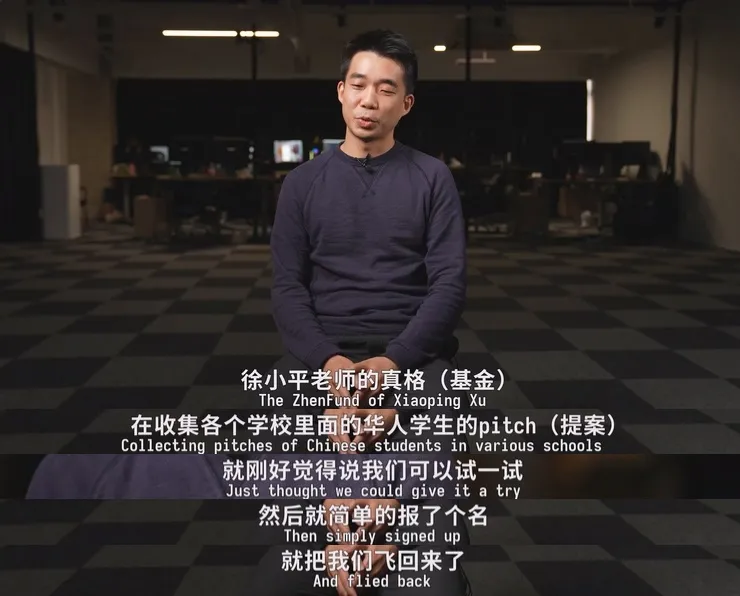
两位80后留学生在美国见证了极具规模的游戏产业,却也看见了华人程序员在本土大厂难以突破“天花板”的局限。
因此,一旦出现机会,他们迅速回国,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启创业征程。
曹侃回忆:“我们在美国留下来,天花板非常低。”在他看来,回国或许能让年轻人拥有更大的空间施展抱负。
最初,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定调“要做游戏”,而是摆出姿态:做任何能抓住时代与市场风口的方向。
AR技术、APP应用乃至其他技术开发,都曾在他们的待选清单上。
然而,李泽阳说,“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资深的游戏玩家”,对游戏有着天然的热情和情感投射,也最终让他们的船帆渐渐驶向游戏世界。
二、初次创业的折戟:看清“边际”与定位
“我没有认清这个边际,就是我们这个组合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 ——曹侃
回国后的第一家公司,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人休学,另两人辞职,决心“背水一战”。
团队抱着昂扬的斗志和对创业的投入,一度想在市场中大展拳脚。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更为困难:AR技术离成熟商业化尚有距离,APP产品的竞争异常激烈,资金持续消耗而回收不理想,从而令他们在14年遭遇了第一次严重的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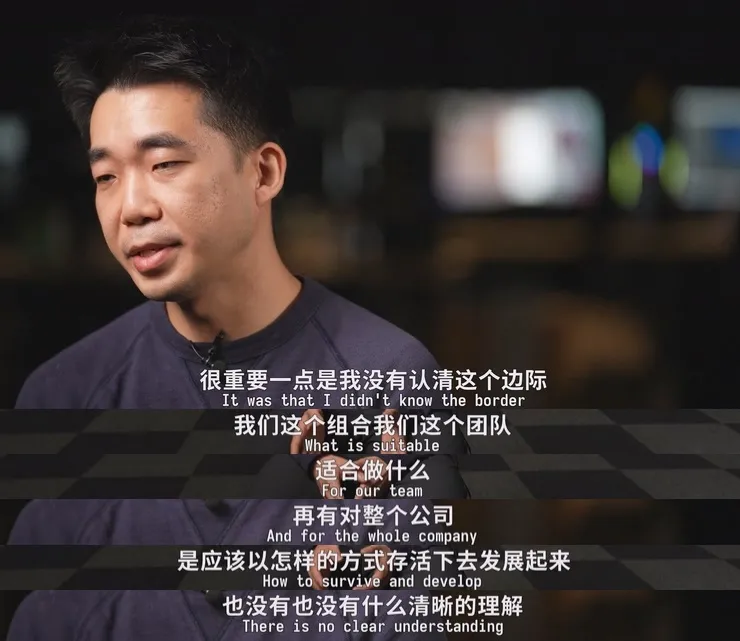
“那时候确实撑不下去了。”曹侃感慨道,团队最后只能解散,甚至为发不出工资的同事承担负债压力。
团队成员对游戏行业确实痴迷,但在策略上,李泽阳认为是“踩到边缘却不知道怎么往下走”。
曾经理想中的“高歌猛进”化作惨痛教训,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究竟该如何把创作热情和商业逻辑有效结合,才是能否生存下来的关键。
三、“元气骑士”的诞生
“最开始是用枪涂地板,后来发现不太给力,就干脆把涂地板部分拿掉了。” ——泽荣
这次失败之后,团队不得不搬到更小的住所,反倒在狭小空间里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转而聚焦小游戏项目,做轻度却有趣的玩法雏形。
彼时还在实习的程序员泽荣,开始基于射击机制,尝试用“涂地板”的创意原型来做一个Dem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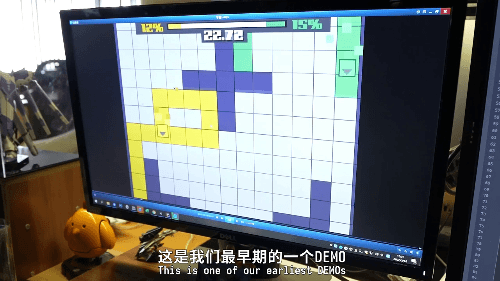
这个Demo最早看起来“极其简约、甚至有点简陋”,但却操作流畅、节奏明快。
随着快速迭代,团队删除了涂地板部分,而保留了核心的射击玩法。
就是这样一个“化繁为简”的选择,让《元气骑士》在2017年2月正式上线后,意外收获了全球玩家的喜爱与追捧。
全球2亿用户下载:
曹侃回忆:“到现在为止,应该有超过2亿的用户。”
凭借高完成度、经典“像素风”以及埋在细节里的创意彩蛋,《元气骑士》在国内外都收获了可观的拥趸,也得到了苹果商店、Google Play、TapTap等平台的高分肯定。
轻量化的商业思路:
与市面上流行的“重量氪金”做法不同,《元气骑士》的主要收入来自“轻氪”。
“可能单个用户均摊下来就几毛钱的收入”,曹侃并不忌讳谈钱,但依然坚持:“我们其实还是很注重玩法,没有特别大的氪金。”
这种思路在玩家群体中积累了良好口碑,也让游戏能持续更新迭代,走过五年的岁月。
四、制作人更迭:从一代目到三代目
“元气骑士其实经历过三个制作人,这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 ——李泽阳
一代目:泽荣——从涂地板到射击核心

泽荣是程序出身,初入凉屋时“并没有对游戏行业有多大包袱”。
由他做出的原型,从无到有地搭建了元气骑士的底层框架,也使得游戏的许多基础逻辑延续至今。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当初并未计划长期、不间断地更新,早期代码略显粗糙,导致在后来服役数年后依然会出现一些“遗留Bug”。
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快速迭代的开发方式,让《元气骑士》能尽早问世。
二代目:阿波——网络化与更新的承接

随着游戏上线并不断更新,一代制作人对于持久维护产生疲惫,身体状况也需调整。
阿波起初是负责SDK接入与公共服务的技术人员,因为熟悉元气的各项逻辑,顺理成章成为了二代制作人。
他在任期间,面对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玩法本身,而是网络化带来的玩家期待。
当玩家呼吁“能不能加云存档”“能不能做联机”时,他们又不得不投入大量技术力量去支持。
阿波坦承:“其实我们都没想到会做联机,是玩家需求在倒逼我们前进。”
三代目:王豌豆——美术人接过制作大旗

2019年底,《元气骑士》迎来第三任制作人王豌豆。
他自称“内蒙古少儿美术大赛银奖”得主,本以为会专注在美术和设计领域。
出于项目内的自然分工演化,他肩负起总体把控的职责。
王豌豆说:“当你真正上手制作人一职时,才知道要顾及的事情很多。”
一个版本上线,数以千计的反馈随之汹涌而来,玩家需求和意见铺天盖地,稍不留神就会被情绪和质疑吞没。
王豌豆感叹,这是一段不断锻炼“强心脏”的过程,必须学会把情绪过滤成可执行信息,再有条不紊地推动更新,方能保持游戏长线的热度与口碑。
五、“轻氪”:独立游戏的价值与商业思考
“我们都是小的时候没啥钱的人,为什么没有钱就不能感受到游戏的快乐?” ——阿波
在竞争激烈、商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的游戏市场,凉屋游戏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条路:轻度付费,不做重度黑箱氪金。

这样的理念在他们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尤其突出。
一方面,团队成员都有过“当年买盗版不想花钱”的经历;另一方面,经过APP和抽卡项目的碰壁,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擅长、更不喜欢“氪金陷阱”那一套。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经济压力。
公司从最初的几人拓至上百人,房租、人员薪资、更新迭代的维护成本都成倍增长。
如何能让《元气骑士》这款单个玩家贡献极少的游戏在市场中依旧生存?答案就是持续的内容输出和玩家的稳定投入。
曹侃说:“我们没有要求团队今年一定要赚多少,但基本的内容量要有保证。”游戏公司要发展,也需要收入支撑。
“回本”在凉屋内部是一个必要且底线的目标,它既保证了创作团队的生存,也平衡了他们的独立探索欲望与商业回报之间的关系。
六、创作的可持续
“如果你只堆在一个项目上,当它衰退就会发现根本没法再创造。” ——李泽阳
如今的凉屋游戏,并不仅仅依赖《元气骑士》。
他们在公司内部开启了多个项目的并行研发:既有《元气骑士前传》这样延续IP的新作,也有更具新意、暂未公开的全新题材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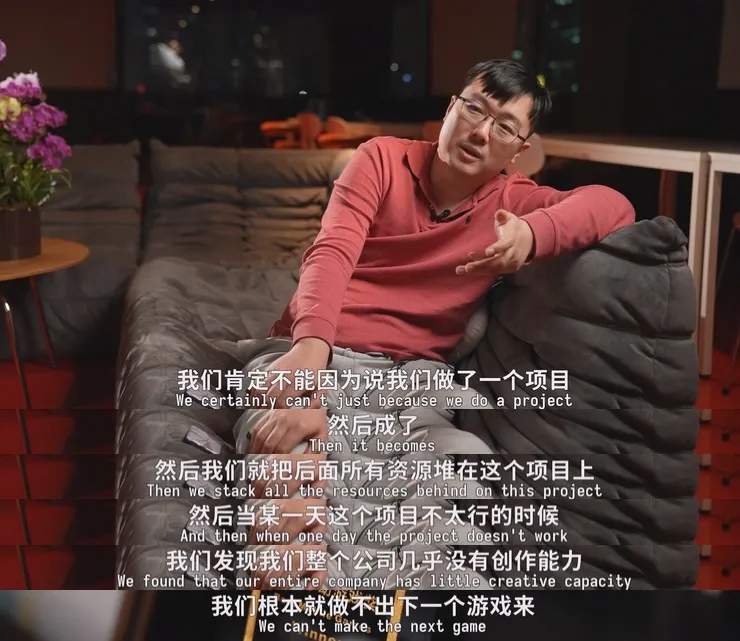
李泽阳认为,这种做法的核心逻辑是:只要人数、资金和时间条件允许,就应该给更多创作者机会进行尝试,从而形成一种“百花齐放、互相扶持”的内部氛围。
为了丰富创作手段,他们搭建了动捕棚(动作捕捉设备),试图让部分项目结合更高精度与更具表现力的技术。
虽然动捕设备不会马上投入到《元气骑士》这样的2D像素类游戏中,但在更新颖的3D项目、新技术内容里,它或许大有可为。
对于公司管理者来说,“这是一种必要的升级,才能在未来有更多可能”。
在团队文化上,他们并没有过度强调层级。
李泽阳、曹侃等核心人物与大家一起坐在开放式办公区域,并无独立老板办公室。
相应地,制作人也需要亲自与程序、美术、运营沟通,甚至有时还要屏蔽外界情绪,确保专注在产品的需求本身。
有开心也有沮丧,但每个人都相对平等。
如王豌豆所说,“这儿就像一个‘巴黎公社’,每个人有话都能说,也要一起承担决策后果。”
七、热爱与野心的隐形平衡
“我们更指望的是总有一些游戏值得被做出来。” ——曹侃
作为一家游戏公司,凉屋游戏始终笼罩着一种低调且朴素的理想主义。
他们比谁都清楚:游戏是需要赚钱的;然而,他们也同样渴望在商业逻辑之外,为游戏带来更多有趣的设计、真正能让玩家快乐的创意。
在外界看来,《元气骑士》轻氪金、全球2亿用户的模式独特。
曹侃则一语道破原因:游戏玩家愿意为优质、充满诚意的内容付费。
他们见证了从小时候“玩盗版”到真正懂得付费支持的转变,也看到了玩家群体的逐年成熟。
或许,这才是独立游戏在中国市场不断壮大的底层逻辑:一方面,玩家们找到了物美价廉、更新频繁却不失乐趣的内容;另一方面,开发者也保持了持续创作的热情与尊严。
时代向前,团队更迭,在五年、十年之后,他们也许会带来更多元有趣的新作;但“元气骑士”所蕴含的那种真挚和热血,或许会一直保留下来,成为凝聚未来一代代开发者与玩家的共同纽带。
导演BK
专注游戏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