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凌烟阁上,李世民画像高悬首位,但若论军事造诣,另一位名将的功绩却鲜少被后世真正读懂——他一生灭三国、定四方,门生遍布初唐将星,却因低调隐忍,成了被帝王光环遮蔽的传奇。

李靖的三重身份:灭国者、兵圣与宗师武德四年,李靖以行军总管之职悄然南下。世人只知李孝恭挂帅征讨萧铣,却不知真正的指挥中枢藏在这位“副将”手中。他仅用两个月便突破长江天险,以水陆并进之势连克荆门、宜都,最终兵不血刃降服南梁十万大军。此战不仅展现其精准的战略预判,更独创“因粮于敌”战术,将后勤压力转化为战力优势。
贞观四年的雪夜,花甲之年的李靖亲率三千铁骑突袭定襄。当颉利可汗在帐中醉饮时,唐军如神兵天降,突厥王庭一夜倾覆。此战他大胆分兵五路,纵横草原数千里,将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反向利用,堪称古代战争史上的“闪电战”模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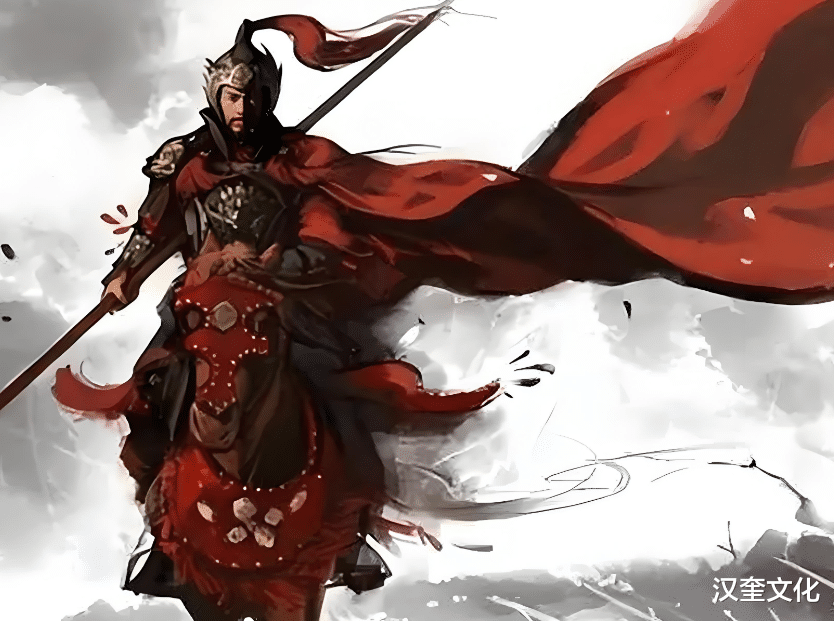
最令人惊叹的是征吐谷浑之战。面对高原反应、补给断绝等绝境,李靖以六旬病躯率军深入柴达木盆地,用“分进合击”战术将伏允可汗逼至绝路。此役后,河西走廊再无烽烟,其作战半径之广、地形适应之强,至今令兵家叹服。
李世民的进阶之路:从败军之将到帝国剑锋武德元年的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十万大军迎战薛举,却因冒进导致全军覆没。这场惨败被史书归咎于“主帅患病”,却暴露了青年李世民的战术短板。直至柏壁之战,他学会“坚壁清野”消耗宋金刚,才真正蜕变为成熟统帅。

虎牢关双灭王世充、窦建德固然精彩,但细究其过程:若非窦建德轻敌冒进、王世充民心尽失,战局或未可知。相较于李靖在各种极端条件下的稳定发挥,李世民的胜利更多依赖于对手失误。正如其自评:“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这恰是猛将而非战略家的思维方式。
被遗忘的将星:那些本可封神的军事天才李道宗22岁随李靖灭突厥,28岁独当一面击退吐蕃。征高句丽时,他率偏师连破十城,展现出不逊李世民的战场嗅觉。若给予更多独立指挥权,其成就未必在堂兄之下。
苏定方的遭遇更令人唏嘘。作为李靖亲传弟子,他在夜袭颉利可汗时率二百骑直捣牙帐,却因朝堂倾轧被雪藏25年。直到花甲之年西征突厥,以一万步骑灭西突厥汗国,创下“一人灭三国”神话。若早获重用,大唐疆域或将再度改写。

李勣的成长轨迹则印证了环境的重要性。从瓦岗谋士到灭高句丽主帅,他凭借李靖教导的“慎战”理念,成为唯一历经四朝而不倒的名将。其临终前布置的契丹防线,更是保大唐北疆三十年太平。
历史的选择与遗憾李渊最初忌惮李靖曾揭发自己谋反,仅委以副职;李世民登基后,又因其功高慎用。这位兵圣不得不在巅峰期急流勇退,将心血倾注于著书授徒。反观李世民,凭借皇子的特权,在一次次试错中成长为顶级战术家——这恰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残酷真相。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李靖位列第八,低于房玄龄、长孙无忌等文臣。但翻开《李卫公问对》,其中“奇正相生”“攻守转化”的辩证思想,至今仍是现代军事学院的必修课。当我们在长安城凭吊李世民时,或许更该记住:那个真正让大唐军威震慑四海的影子统帅,叫李药师。

李二是被皇帝光辉掩盖起来的战神,不仅仅是在隋唐,就是全史里也是顶级的存在。上文提到这几位大神的确牛逼,但要说能压李二一头那也就只有小编敢说,他们自己绝不敢说
李世民一生就一场败绩,那还是因为他生病了
大唐初期,第一代战神 李靖【李世民也可以为战神 当皇帝后 不适合这个称呼了】第二代苏定方
公认的大唐军神,武庙十哲之一,还被神话成为天庭降魔大元帅、托塔天王,李靖都上天了[抠鼻]
唐初的徐茂公的确是第一战神
宋金刚,李密,王世充,刘黑闼,这四位比李世民李靖低一档,但对上李唐阵营的其他人,绝对虐杀
嗯,对的
李世民实在太强了,如果不是皇帝加身,他足以列入跟白起等四大战神之列
王不过项,将不过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