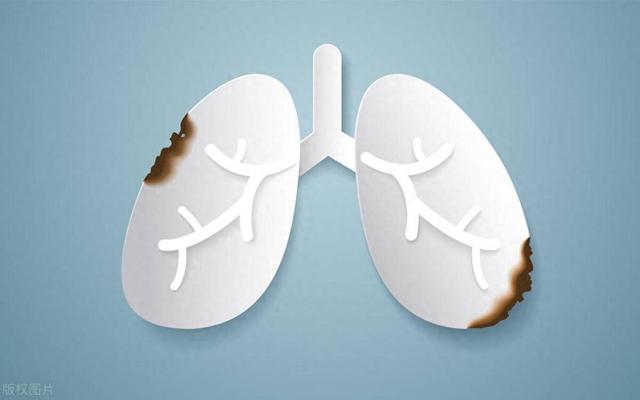“好好一个病理大夫,让淋巴瘤毁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曾笑言。
淋巴瘤是最常见的恶性血液肿瘤之一,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新发淋巴瘤病例,每5分钟就有1人确诊淋巴瘤。对淋巴瘤治疗而言,如何通过病理诊断确定病理类型,从而指导淋巴瘤治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要。但淋巴瘤分型多达上百种,精准识别的难度可想而知。
4月15日-21日为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新京报记者对话高子芬教授,探秘病理医生面对棘手的淋巴瘤如何“火眼辨型”。

受访者供图
谈定位:
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
新京报:在肿瘤诊疗中,患者面对的往往是临床医生,病理医生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高子芬: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是“幕后英雄”,但压力也很大,因为病理诊断被认定为是诊断的金标准,临床治疗需要依据病理诊断报告来进行,而影像学报告、化验结果仅供参考。但面对疑难病例,也会有诊断错误的时候,这种错误属于执业允许范围,因此病理诊断报告有一定的容错率。
由于诊断报告的价值,我们希望能给出一级诊断,明确到底是什么疾病,以指导临床治疗。但有些疾病,如淋巴瘤的病理诊断难度大,有些病理医生担心诊断出错,只敢给出二级诊断,诊断报告上会使用“考虑”“不除外”“高度怀疑”等表述。但这样的表述,可能会导致临床医生无法给出进一步的诊疗方案。
谈难点:
淋巴瘤分型上百种,误诊率高
新京报:《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提及,淋巴瘤存在很高的误诊比例,受调者中43%曾被误诊,51%的患者辗转多家医院后才确诊。你经手的淋巴瘤病例,这种情况多吗?
高子芬:淋巴瘤诊断错误率相对更高,不单是在中国,因为诊断非常难。我从1992年开始学做淋巴瘤的病理诊断,当时想一定要做到最好,但直到现在我也有诊断不出来的时候,这样的疑难病例需要和临床医生一起会诊讨论,甚至和国外的病理专家、血液病临床医生讨论。
我们曾遇到过辗转七八家医院还没有明确诊断的淋巴瘤患者,不同医院的诊断甚至是完全矛盾的,误差率非常大。接到这样的病例,我们会看患者之前做的病理诊断来自哪家医疗机构,出诊断报告的医生是不是专注血液病亚专科的病理医生,分析无法精准诊断的原因,矛盾在哪里等。对淋巴瘤的病理诊断而言,医生的经验非常重要。我现在一年要看5000多例,而基层医生可能一年只有百八十例,积累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经验丰富的病理医生能够在复杂的病理切片中找出哪个是肿瘤细胞。
新京报:淋巴瘤误诊率为什么这么高,到底难在哪里?
高子芬:病理诊断最传统的手段就是靠病理医生看细胞形态,包括细胞的大小、排列等特征。如最容易诊断的肺腺癌,或者胃食道鳞癌,这些腺上皮细胞、鳞状上皮细胞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排列,一旦细胞形态变了,如变大、异形或排列紊乱了,就可以明确诊断。但淋巴瘤不同,淋巴瘤的瘤细胞形态,就是淋巴细胞分化过程中某一个阶段的正常形态,只有当它位置不对了、结构不对了、免疫表型异常了,才考虑是肿瘤。比如免疫母细胞淋巴瘤,在分化过程中,免疫母细胞就那个样子,它在正确的位置是正常的,但位置变了就不行。又比如套细胞淋巴瘤,套细胞在滤泡的套区,一定的数量,增殖活性很低是正常的,如果套区弥漫增生,破坏相近的结构,并且增生活跃了,出现了表型上的异常,就要考虑是肿瘤性增生了。
其次,淋巴瘤病理诊断,对病理切片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要固定及时、脱水到位、切得很薄且平,如果切片厚、不平,细胞重叠,导致观察细胞特点的不准确,就会误导医师的初步判定,导致进一步工作的误差。所以淋巴瘤诊断的正确与否,对技术环节要求比较高。
第三,淋巴细胞是免疫细胞,免疫系统本来就复杂,淋巴细胞有不同的抗原和分类,得了肿瘤以后就更加复杂。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医师资格考试,免疫这门学科太难了,放弃算了。正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病理医生不愿意搞淋巴瘤的诊断,和肺癌、肠癌等肿瘤相比,全国知名的病理专家也很少。
谈进步:
技术发展助力降低诊断错误率
新京报:淋巴瘤的分型有上百种,像你这样有经验的病理医生是如何“火眼辨型”的?可以使用的“武器”有哪些?
高子芬:老同志以往主要是单纯看细胞形态来诊断,可以使用的技术手段少,所以熟悉淋巴瘤的病理医生就是最好的“武器”,病理切片出来后,首先要靠病理医生来对形态进行判断,当然诊断会存在不少的问题,现在有了免疫组化检查、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技术手段助力,淋巴瘤诊断的错误率大大降低。近代淋巴瘤病理诊断免疫组化的方法是必需的,给肿瘤细胞“穿衣服”,看细胞表达的是T细胞标记物还是B细胞标记物。还可以用流式细胞仪标记异常细胞的免疫表型,更加精准;克隆性分析则可以分析增生细胞是否为单克隆性,即肿瘤是否由一个细胞发展而来,如果是,那就可能是肿瘤。基因检测的手段也可以帮助病理医生发现某种分型的淋巴瘤会出现一些异常基因。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对老的病理医生而言,还需要不断学习如何合理使用。
新京报:人工智能在病理科是否有应用场景,尤其在淋巴瘤诊断方面?
高子芬: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在肝癌、前列腺癌、肺癌、胃癌等肿瘤方面都已有应用,但在淋巴瘤这块儿很难,针对淋巴瘤的诊断,病理医生的火眼金睛最重要,AI永远不会让病理医生失业,但可以赋能,有应用前景。
谈人才培养:
练就 “火眼金睛”,兴趣最重要
新京报:如何培养新一代病理医生,提高诊断淋巴瘤的能力?
高子芬:兴趣最重要,一定要喜欢,病理医生面对淋巴瘤诊断时一定会面临很多困难,很累很苦,如果没有兴趣,很难做下去,但要能把淋巴瘤的诊断难题解决了,就没什么难的了。淋巴瘤的病理诊断很具有挑战性,但淋巴瘤的药物研发非常活跃,检测技术在淋巴瘤的诊断应用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年轻一代的血液病理医生需熟练掌握淋巴细胞分化和抗原表达、流式细胞术及分子病理检测等技术,并跟着临床医生一起查房学习,历经两年的专科培训下来,病理诊断水平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也希望在管理模式不同于西方的病理科建制前提下,推动淋巴瘤病例各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共享,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