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考中进士对每一位读书之人都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与诱惑力。
考中进士,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拿到了一纸通往官场仕途的门票,其实不然。事实上,在我国明清历史上考中进士后,而没有出来做官步入仕途的人也不乏其人。
既然不做官,那为何要去参加朝廷三年才一度的抡才大典会试呢?答案是,好处很多。考中进士,意味着一个人在读书上是成功的,至少进入了“士大夫”的行列,与普通百姓有了天壤之别。
一个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即使他放弃做官机会回到家乡,那也是一种超级的存在,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地方倍受人尊敬。在一府一州一县之地,拥有进士身份的人,可以与地方知府、地方县令平起平坐,即便因事犯了什么法律法规,官府可以抓捕,但在审讯之中是不可用刑的。这在大清律法中便有明文规定。此外,拥有进士身份,意味着一个人拥有进退自由的巨大空间。进可步入仕途为官,退可在一省、一州、一县任地方最高书院山长兼首席教习。
我国古代历史上,除了战争乱世,有少听说有进士一生穷困潦倒的,其生活都相对比较惬意。至于在历史书上读到的那些穷困潦倒的诗人,他们的确有才,但是他们中绝大绝大部分就根本没有进士身份。所以,在我国古代读书人中,对考中进士几乎没有不向往的。自然,左宗棠也不会例外。
左宗棠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11月,湖南长沙湘阴县人,其祖上七代人是地方秀才。到了左宗棠这一代,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一下子出了两位举人,即左宗棠与其二哥左宗植,而且左宗植还是乡试的第一名,即乡试“解元”。左宗棠则是这一年的第十八名举人。

在古代,有举人身份便拥有了进入仕途的入场券。但是,举人能不能入仕那要看命运与机会。而进士则不同,考中进士则意味着一个读书之人步入了仕途,即可在京由从七品京官起步,也可被朝廷外放全国各县为县令。
左宗棠考中举人的次年春,便去京城首次参加了会试,但失利未中。
这一次失利,左宗棠似乎没有丝毫在意。从京城返回长沙后,他还一度把早年撰写的一副对联重写后挂于书房,有点悠然自得,一种从容淡定的姿态,给人宣示其早晚必中的自信。该联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此联虽有点自侃自嘲,但其实是在向世人自我营销,尤其是联语落款处,钤印“今亮”,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三年后,即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在夫人周怡端的支持下,再次进京会试。
按惯例,本来这一年是没有全国性会试的,但适逢孝和睿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朝廷特开丙申恩科会试。因此,比正常会考时间提前了一年。
此时,左宗棠已经入赘湘潭周家有四年了。由于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来源,所以吃住在岳父周家的左宗棠,在面子上很是挂不住。对于一位已经24岁的读书士子举人,还要依靠岳丈家里的帮助,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所以,左宗棠亟需考中进士,博取仕途功名,步入官场干出一番事业,同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处境。

左宗棠
在当时,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已有两岁多,次女左孝琪亦有一岁多了。一家四口人的用度,让左宗棠苦不堪言,幸好有妻子周夫人的勉力支撑。
这次会考,颇富戏剧性,甚至可以说左宗棠是“考中”了进士。
这一年阅卷的同考官翰林院检讨温葆深,很是欣赏左宗棠的卷子,极力推荐了上去。主考官潘世恩、王鼎、吴杰、王植四人在看过温葆深推荐上来的卷子后,认为“立言有体”,于是取中为第十五名。然而,到了最后发榜前夕审查各省进士名额时,朝廷吏部与礼部发现湖北省少了一名,而湖南省多了一名。
在当时,进士名额各省都有一定的限额。需要兼顾各省的平衡,并不是完全依据文化水准的高低录取。于是,“考中”进士的左宗棠名字又从进士名单中被拿掉了,补上了一名湖北考生。就这样“路转峰不回”,左宗棠与进士擦肩而过。
这一次左宗棠有点失落,没有在京师驻留,放榜之日后便水陆并用,不到一个月便回到了长沙。这就是左宗棠的第二次会考失利。

左宗棠
道光十七年(1837年)冬,左宗棠再一次北上进京准备参加会考。由于时间尚早,左宗棠到武昌后,在武昌的湖南长沙郡馆住了一些时日温习功课,又游历了武昌周边一些名胜。次年初春,左宗棠才赶到北京。这一次,左宗棠会考又失利了。这也是他的第三次会考失利。自此他决计不复会试,回到湘阴柳庄会开始钻研农学,准备以“湘上农人”老死于家乡。
关于左宗棠这一次会考失利的历史细节,从目前现有的史学资料来看,记载极其少,仅记录过他与胡林翼在京城周振之家有过一次见面晤谈,至于考试中的具体情况细节,语焉不详。以上便是左宗棠年轻时代三次赴京会试的情况。
总的结果是,左宗棠没有通过会试与殿试,未能以考试的方式获得正榜进士称号。那么,他晚年的进士身份是从何处得来的呢?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上,朝廷为何突然要赐予其“同进士出身”的身份呢?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九月朝廷将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处理西部内乱。两年后的四月,西捻军在河北沧州吴桥附近被全歼,西捻军覆灭。
同治七年(1868年)8月,左宗棠首次至京师觐见两宫太后。
慈禧太后询问左宗棠:“西事何时可定?”左宗棠答曰:“以五年为期。”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好五年期限时,西北陕甘内乱在左宗棠的抚剿并用之下,已经基本平定。

左宗棠
为了褒奖左宗棠这一重大功绩,同年八月,朝廷下旨诏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称号,加一等轻车都尉。然而,此时的左宗棠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起来,心中早已放下的一个包袱重新又浮了起来。
左宗棠获此殊荣,一只脚已经迈了拜相入阁的门槛,为什么反而没有一丝高兴呢?原来是当朝廷授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时,朝野上下纷纷议论开了,说什么左宗棠平定西北有功固然当赏,但他连个进士都不是,怎么能授予协办大学士的头衔呢?我朝早有定制——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院进士,不得授予“大学士”之位。现在倒好,全为左宗棠一人打破了。所以各种议论传闻一下子在朝野广泛流传。
左宗棠一生是一个自尊心极强之人,此时虽已年过花甲,身居陕甘总督之位,又早有了太子太保之衔,本已看淡了不少。但是目前社会上这一股清议让他很是烦心闹心。
此时,另有一件事从朝廷传来。朝廷中已经就“海防与塞防”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江西巡抚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沈葆桢等人为代表的“海防派”主张重海防,新疆的事再放一放,避免因收复新疆而与沙俄和英国发主军事冲突,好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建设大清海防,应对列强来自海上的威胁。以军机大臣文祥、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为代表的“塞防派”则主张收复新疆,西北塞防不可削弱。
当时大清最高当局两宫太后与军机处左右摇摆,不能作出最后的决策。这让力主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忧心忡忡。

由于西北兰州距京师几千公里,奏折信函往返一次需一两个月,若如此争辩下去,久拖不决,势必葬送收复新疆的良机。因为,当时的俄国正在中亚与土耳其开战,根本抽不出兵力干涉中国收复新疆。英国则根本没陆军力量进入新疆,也不敢进入新疆。如果等俄土二国战争结束后,再来言收复新疆,则不仅错过了最佳时机,而且即使收得回来,恐怕付出的代价将呈几何级增加。而且更糟糕的是,远在京师军机处的一众大员与地方督抚根本不了解西北的形势与沙俄、英国的情况,与李鸿章一唱一和。若再如此下去,新疆非完蛋不可!
但远在西北的左宗棠身肩重担,总不能自己甩手回京师觐见两宫及同治皇帝力陈新疆之事吧?
在这种情形之下,左宗棠于是投石问路,采取了一个让朝廷左右为难的行动方案: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上旬,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另派大臣出任陕甘总督,自己要回京参加该年春三月中旬的甲戌科会考。
按大清规定,凡四品及四品以上官员均不得再参加朝廷会试,若要参加会试,需自我申请降至四品以下后给吏部审查通过,可以特例参加会试。很显然,左宗棠的情况非常特别。其身居陕甘总督,加太子太保衔,并且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朝廷又诏授了他协办大学士,此时的左宗棠不仅是朝廷一品大员,而且是入阁大臣。朝廷的会考规章,很显然不适应他。但是朝廷军机处在收到他的奏折时,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因此十分为难。于是就采取了拖迟的策略,等拖到该年会考结束后,也就可不了了之。但左宗棠却去函几次催办,无奈之下,军机处只好把他的请辞来京的奏折上报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
慈禧太后收到这份奇怪的奏折后,起初也十分奇怪。但她毕竟是影响中国的四个女人之一,在政界玩弄权术的能力毋庸置疑,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宫皇太后对此哭笑不得,于是在同年七月,慈禧太后命朝廷下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身份”,并晋东阁大学士头衔。
此事在《清史稿・左宗棠传》中虽未明确记载,但该事依然有迹可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为民国袁世凯时期赵尔巽领衔编纂,并不严谨。所以,赵尔巽生前称之为“清史稿”,而非“清正史”。以此表示此史并未定稿,有待后人完善。

《清史稿》
在《清史稿・左宗棠传》中,是有少许记载在时间上是有误的。
《清史稿》上讲同治十三年(1874年)晋左宗棠协办大学士,这一点在时间上便是错的。
依民国初期秦翰才先生所著《左宗棠全传》及《左宗棠年谱》记载表示,朝廷授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并非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而是同治十二年七月(1873年9月)。授协办大学士在前,赐同进士身份并晋东阁大学士在后。
关于这个时间先后次序问题,在《左宗棠全书》书信卷中亦有所记录。在民间史料,如秦翰才先先的《左宗棠逸事汇编》、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声木所著《苌楚斋随笔・卷九》中也都有记载。所以说,朝廷在左宗棠晚年赐其“同进士身份”一事是史实,这点用不着多怀疑。
下面再接着谈另外一个关联问题:为什么朝廷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授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头衔时,左宗棠并不高兴,而是烦心闹心?
这中间有两个问题,朝廷没有考虑周全。一是按大清官制规定,凡非进士身份者,不得入翰林院;凡是非进士出身者,不可授大学士之位。但是朝廷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授左宗棠协办大学士时,并没有同时赐予其“同进士”身份。那么,这样一来,左宗棠的“协办大学士”头衔就显得尤为尴尬,是一个无根的“大学士”,会被天下读书之人所讥笑。左宗棠一生自视极高,自尊心又极强,他当然不希望授人以柄,为天下笑。所以要完美解决此事,那朝廷必须特赐其“同进士”身份,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此时左宗棠年事已高,已经是62岁的人了,这在古代已是高危年龄人群了,今生明死,谁也说不准。由于宋朝以来的崇文抑武政策,导致后世很多人都不希望以武将身份出现。而一生自视甚高的左宗棠不希望自己在去世之后,朝廷给他一个武将的“谥号”。

左宗棠
左宗棠在骨子里一直以文人自命,但这些年来带兵打仗,干的全是武将的事。他内心十分清楚,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死后是得不到文官大臣的“谥号”的。那么既然朝廷授予了自己“大学士”头衔,为何还要吝啬赐一个“同进士”身份呢?所以说,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7月,朝廷在授予其协办大学士后,不到半年又晋升其“东阁大学士”,并同时赐“同进士”出身。
至此,一切都名正言顺了。
左宗棠对于朝廷赐予自己“同进士”身份后,他本人持何态度?有何感受?同治十三年(1874年)7月,朝廷赐左宗棠“同进士”身份,并晋升其东阁大学士后,左宗棠本人内心是喜悦的。他不再担心朝野学子士林的讥讽。因为他的“进士”身份是朝廷特赐予的,谁也说不起。一句话,这是凭本事得来的。
至于说死后,他也不必担忧朝廷会给他一个武官的“谥号”了。因为以其生前战功官位,加之又有了进士身份,其死后朝廷必会给其一个带“文”字的谥号。后来的历史表示,左宗棠生前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后,朝廷赐予的谥号即为“文襄”。该谥号含金量极高,在大清一朝获得“文襄”谥号的人极少,268年中只有15人获得过。在晚清七十二年历史中,就只有左宗棠与后来任过两广总督、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他们二人获得过“文襄”的谥号。
所以说,对于在晚年获得“进士”身份、晋东阁大学士一事上,左宗棠是喜悦的,完成了自己一生出将入相的文人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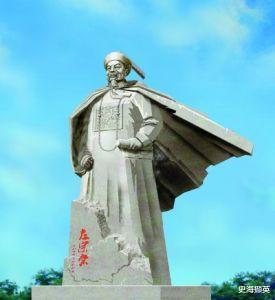
左宗棠
当然了,他也是无愧这些荣耀的。
左宗棠一生十分传奇。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晚清一个异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晚清,他一个普通书香农耕家庭子弟,在未踏入仕途之前,几乎与晚清著名历史人物如陶澍、林则徐、肃顺、曾国藩、胡林翼、张亮基、骆秉章、郭嵩焘、潘祖荫等人都产生了人生的交集。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在大清一朝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
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正式出山,他一路平太平军之乱、平西捻之乱、平陕甘内乱、收复西北新疆全境,到光绪十年(1884年)痛击法军,取得对法作战的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这一切的惊世骇俗的人生功业,只在短暂的二十五年中便全部完成了。
左宗棠这一生,对个人有交待,对国家有担当,对民族有大功。他生前名震中外,身后美名远扬。他这样的人,在我国历史上真是少见。对于左宗棠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今天除了纪念他,怀念他,宣扬他,继承他伟大的家国情怀外,若再谈他晚年是否获得过进士身份,这还有什么意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