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而言之,我的人生三分之一是致力于阅读,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写作,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和光一起生活。
——大江健三郎,引自《巴黎评论》Vol.183作家访谈
当一个人的本性已经同一切肉体的冲动割断,并且剥夺了一切超自然的光,却能做出完全符合超自然光——如果这种光存在的话——所要求必须做到的事情,这就是圆满的纯洁。这就是耶稣受难的核心。
——西蒙娜·薇依,《重负与神恩》
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出生时头部畸形,“看起来像长了两个脑袋”。当母亲问他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的时候,大江随口回答,“就叫他乌鸦吧”。
母亲不解其意,生气离开。但到了第二天,她又回到医院,对大江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但这时大江也改了主意,最终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大江光”。

根据《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乌鸦”这个名字来自他阅读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作品时得到的启发。薇伊在书里引用了一则因纽特寓言,说创世之初世界一片漆黑,乌鸦想吃地上的豆子却看不清,于是就想,要有光该多好。这么想着,世界便光亮起来。
大江光生于1963年,次年大江健三郎写出了长篇代表作《个人的体验》。书中主人公“鸟”在畸形的儿子出生后,曾想尽一切办法逃避,但最终还是选择照顾这个孩子。很多人都对这个突兀的转折感到不满,其中三岛由纪夫尤甚——毕竟,两位大作家都在试图处理无妄之灾降临后的人性与人生,三岛为了解决这个命题甚至要诉诸毁天灭地的美与死,然而大江却让一切如此轻描淡写,仿佛无事发生。

像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到1967年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大江为“转变”而进行的铺垫变得异常充分,整个故事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回忆之间不断翻转,几乎令读者感到窒息:在战后日本,“我”(蜜三郎)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在社会上混得开”,尚且可以躲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当老友以惨烈而诡异的方式自我了断,妻子在生下畸形的孩子后陷入抑郁,整日借酒浇愁,“我”其实已经陷入了在遛狗时跌了一跤,便“在暮秋的黎明前膝上抱着条狗坐在坑底”的状态;甚至老友的死也是值得羡慕的——他毕竟感受到了“某种东西”,而“我”即便是连死的道路也看不明晰。
就在这时,弟弟(鹰四)从美国回来了。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失败后,鹰四作为“悔过学生领袖”加入学生剧团赴美,右翼政党计划让这个剧团通过表演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就妨碍美国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民众道歉。然而一到美国,鹰四便从剧团逃走,四处游荡,在流浪数年后又决定归国。尽管蜜三郎并不喜欢弟弟的激进姿态,但当后者提出要回到故乡生活,他也选择一同前往。
鹰四回归故里的动机是明确的:他们的家族——根所一族——祖上曾有一位“斗争领袖”,此人正是兄弟二人曾祖父的弟弟。万延元年,即1860年,他煽动村民造反,响应当时如火如荼的“倒幕运动”,可惜功败垂成。失败之后,据传为保住根所一族,作为家主的曾祖父亲手将弟弟杀死;但亦有传言,称弟弟在起义失败后单独逃走,任由同志惨遭屠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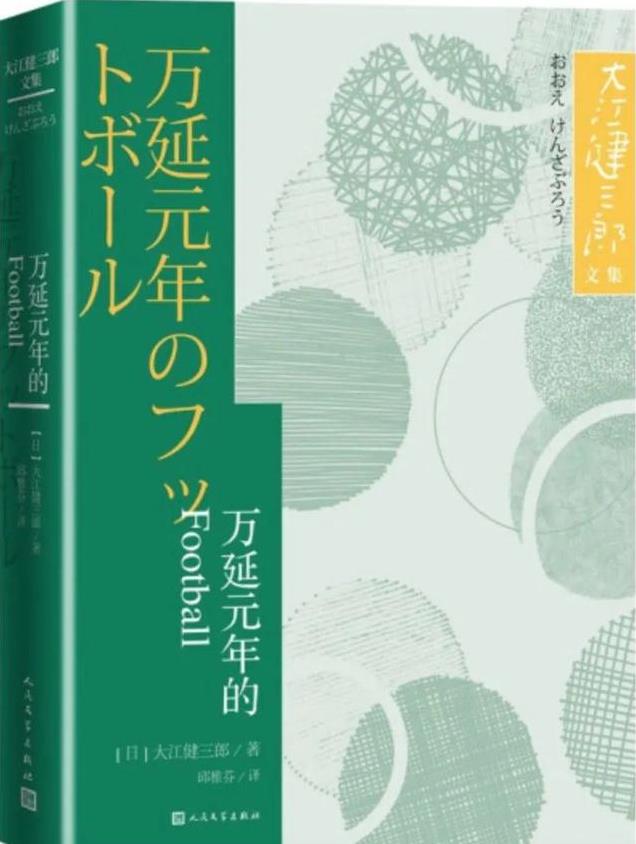
小说的主线由此才真正显露:1960年运动失败的鹰四,试图追寻万延元年“斗争先祖”的脚步。他在村子里组织青年练习足球,正是效仿先祖当年组织青年练武——小说题名“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由此而来。按照大江自己的说法,“成为支持我把这部小说写下去的动力的是农民暴动……一个男人砍下对方首领的脑袋,用布块儿将其包裹起来,然后返回农民们出来迎接自己的那个村子。”(《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尽管一个人单枪匹马护送一个“球”这样的意象更贴近橄榄球,但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的足球更能代表底层大众激情的宣泄——而它也只能是激情的宣泄,正如小说中蜜三郎的妻子的议论:“他们不表现出来,可确实满腹牢骚。前途真是黯淡啊,不论他们是多么老实能干的青年!那些孩子才不是喜欢踢足球的,实在是因为没别的事情可做,才左思右想一脚踢向乌云。”
然而鹰四的野心,绝不止于丰富乡村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他是当真把足球看做一种“训练”——训练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而召唤曾经改写历史的所谓“斗争精神”:
我要他们把自己与万延元年的青年同一化,既然那小伙子身上已经表现出了最初的征兆,那么,这个倾向可能很快传给整个足球队!我还要把它传给山脚上所有的人。我要把一百年前祖先的暴动唤回山谷……阿蜜,这不是不可能的!

大江健三郎
然而“阿蜜”怎么想呢?按照作为“剧本”的历史传说,蜜三郎是作为家主的曾祖父,正是他亲手斩杀了成为领袖的弟弟。但不同于要守护家族的曾祖父,蜜三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守护的了。他当然不看好鹰四的事业,但他亦如在老友自杀时一样,认为鹰四同样感受到了他无法感受到的“某种东西”,并因此自惭形秽:
在这山谷中,我不过是一个按年纪来讲有些臃肿肥胖的独眼过客而已,除了我的这种形象之外,山谷中的事物已唤不起其他任何真我的记忆和幻觉,我可以主张过客的identity,老鼠也有老鼠的identity。既然我是老鼠,那么人家说“你真跟老鼠一模一样!”我就不会有太大的惊讶,那只即使被骂得狗血喷头也目不斜视跑回自己窝里的小家鼠就是我。我无声地笑了。
于是蜜三郎从头到尾,只是作为“过客”,冷眼旁观了弟弟对于作为仪式的暴动的继承。但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关于曾祖父弟弟的历史传说有两种——既然蜜三郎没有通过扮演他的角色,来帮助鹰四完成他的英雄传说,那么鹰四的独角戏,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第二种;或者说,关于“英雄”与“叛徒”的identity一直在鹰四身上并存——他参加安保斗争失败去往大洋彼岸“谢罪”可以看作逃离,而从悔过剧团中逃走同样也是如此——这便意味着他与他的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撕裂与毁灭。
然而毁灭鹰四的终究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传说——小说的神来之笔,直到尾声才真正出现。蜜三郎最终发现,万延元年的领袖并没有随着那次暴动的失败就义或是叛逃,而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参与到真实的历史当中。非此即彼的传说之外才是真实——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暧昧性,而倘若这种暧昧性能够早一点为鹰四所知,他的命运或许也会随之改变。

1958 年,大江健三郎成为最年轻的芥川奖获得者(当时)
至少,这已经足够蜜三郎实现他的转变了。他终于破解了友人和鹰四所感知到的“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存在主义的偈语“他人即地狱”。他们都确信自己看到了地狱最惨烈的景象,或者宁愿相信唯有让自己投身其中,才能使地狱的惨烈得以完成。而当蜜三郎目送弟弟走完了这一程,他也看清了存在主义的另一面:“此世,如行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小林一茶俳句)
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是我青春时代的作品,缺陷是明显的。但我觉得它是最成功的,连缺陷都是。”至于同样写作于野心勃勃的青春时代的《个人的体验》,在出版多年后,大江却仿佛自嘲一般,推出了一个“私家版”,改掉了那个饱受争议的“大团圆”结局。最初的版本是幡然醒悟的主人公前往医院,将本打算弃置不管的儿子安然无恙地接了回来,而在“私家版”中,结局变成了主人公赶到医院,然而等待他的却只有冷漠的医生:
——孩子?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场的路上。您知道,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重新来过的。(大江健三郎《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
足够聪明的大江,足够清楚世事不过一念之间。这一念是母亲回到医院,尽管并不理解,但仍要说“乌鸦是个好名字”;也是这“乌鸦”可以来自因纽特人关于光的传说,也可以来自爱伦·坡的《乌鸦》:“Nevermore”——永不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