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前言诗话所拓展出来的新的兴趣领域中,最大的一个是关于诗歌艺术或技巧,正式的文论、序言、书信、散文总是不愿意过多关注技巧这样的东西。
这可能根源于长久以来儒家对实用专业知识的轻视,儒家传统总是把“工”,尤其是“巧”,跟虚伪、做作联系在一起,这种偏见阻碍了人们对专门技术的研究。
 诗艺
诗艺六朝末和唐代编纂的韵律手册和作诗指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终至湮没无闻,也就不是没有原因的了。

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俗”指称的对象不是平民,而是官僚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官僚而非学者。
我们从宋代士大夫大量的关于陶潜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他们对文学技巧是不屑一顾的,陶潜从来不关注诗歌法则或规范,因此他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诗话摆脱了严肃文论的束缚,所以它是相对自由的,人们对正统文论的厌倦使诗话有了谈论诗歌技巧的机会。

诗话拥有轻松的形式,能够较多地触及知识分子禁忌的话题,作家们当然十分渴望分析和思考诸如遣词、对偶、押韵、用典以及诗歌的结构这样的问题。
在欧阳修最早的诗话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不同层次的文本看法上的分歧,其中包括欧阳修和梅尧臣讨论韩愈诗歌押韵问题的那一则条目,我们知道,韩愈是欧阳修心目中的文化巨擘。

在诗话之外,欧阳修常常在文章中谈及唐代的这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作为排佛反道的儒者,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或者作为延续孟子、扬雄传统的圣贤道德典范。
但是欧阳修几乎从不谈论作为诗人的韩愈,即使偶有提及,也仅限于讨论他诗歌中涉及儒学政治家形象的方面。
 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理解
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理解因此,当欧阳修的诗话中出现一则探讨韩愈诗歌技巧的条目时,人们就感到意外了,这说明欧阳修是韩愈诗歌的细心且富有洞察力的读者。

在其他地方,欧阳修从来没有表露这一点,欧阳修在为自己提出这一话题进行了充分辩护后说:
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

参考资料
我们看到,即使是在诗话里,欧阳修也觉得应该为提出这样的话题道歉,但是一旦话题展开之后,他细致和敏锐的观察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说明欧阳修对韩愈诗歌“固不足论”的特点有着深刻的见解。

一旦诗歌技巧的主题被提出,接踵而来的许多内容就会对其进行拓展,最早的诗话在材料类型方面体现出很大的不同:文人轶事或诗歌本事占了很大的比重。
虽然文学批评和分析的成分从一开始就存在(如欧阳修的诗话),但并不突出,正如在诗话尚不成熟的早期阶段,司马光将诗话的目的定义为“记事”。

这类记事性的条目在诗话中总是会被认可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纯粹的轶事逐渐失去优势,越来越多的篇幅让给了评论和分析。
诗话的创作诗话的关注点集中在诗歌技巧问题上,这不仅仅是形式本身的解放,也不仅仅意味着它们从此摆脱了正统文论的束缚。

我们同时也看到两个群体之间的鸿沟:最有声望的精英作家与诗话创作者之间的鸿沟,这一差别在最早期的欧阳修、司马光和刘放的诗话里并不存在,只是在下一代文人那里才变得明显起来。
第二代诗人的领袖苏轼和黄庭坚都不创作诗话,苏轼的兄弟苏辙,苏轼主要的门徒(秦观、张耒、晁补之)也都不写。

陈师道除外,但作品是否归属于陈师道还存在疑问,王安石没有采用诗话的形式,贺铸和陈与义也一样,直到南宋,像杨万里和刘克庄这样的主要诗人才又开始诗话的创作。
北宋最后的几十年里,诗话由那些可称为文坛的“旁观者”群体——僧人或不知名的作家来创作。

参考资料
比如惠洪(黄庭坚的佛教朋友)、王直方(苏轼的晚辈)、范温(秦观的女婿)、洪刍(黄庭坚的外甥)、蔡條(蔡京的儿子)、阮阅(一个生平不详的人物)以及叶梦得(因记录大量的文人轶事而知名)。

这些人当然渴望成为诗人,在他们许多富有洞察力和鉴别力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能够领会文学艺术的精妙之处并渴望将其展现出来。
北宋晚期的诗话,经常会直接或间接引用苏轼和黄庭坚这两位在当时最受尊敬作家的风趣、精辟的评论。

但苏轼和黄庭坚自己并不写诗话,这和他们一贯的主张有关,他们认为最好的诗歌并非来源于过分的修饰或苦吟,他们把对诗歌优劣的书面分析让给天资不高的人去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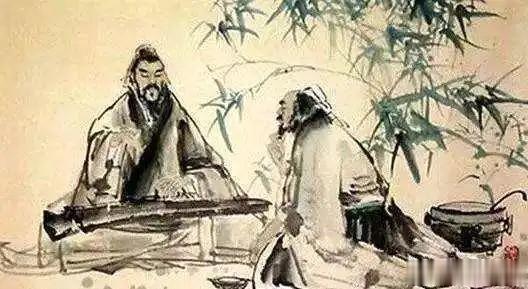
我们来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出自北宋末的二流诗人之手的诗话条目,都是关于杜甫的,这些诗话的重点在于突出杜甫如何重视遣词造句,并对杜甫的这种能力深表赞赏:
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鸟过林分外明。”谢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陈师道《后山诗话》

这些条目充满洞见,而且它们并不提及好诗应该是什么样或力求怎样等标准或信条,杜甫对统治者的忠诚以及对民众疾苦的关心在这里未被提及。
他高远的“志”未被提及,优秀的诗作来源于诗人优秀的品格,也未被提及,没有提到“道”,没有讨论诗人如何达到“文”的理想,没有关于感情表达的“诚”或“真”的论述。

当作者把精力完全集中在他感兴趣的技巧方面时,所有传统的观念都被抛在一边,联句被看成是独立的单位,注意力完全放在遣词造句方面。
在此基础之上批评家进行他的分析,评判这些诗句的唯一标准是用词的有效性,作者的兴趣在于找出并玩味那些熟练写就的诗句。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浅析韩愈诗歌对欧阳修的影响》张宁。
【2】中国知网——《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谭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