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美学与后现代思潮交锋中的中国美学
吴娱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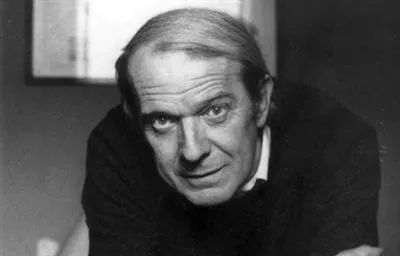
从18世纪鲍姆加登开创了美学,经过康德、黑格尔、谢林等的发展,德国古典美学已经成为一个精致经典且无与伦比的水晶宫殿,它具有宏伟精巧的结构、包罗万象的内容、缜密思辨的系统。这对习惯于顿悟、朦胧、散文化的中国文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中国现代美学就是在西方异质思维的影响下构建起来的。王国维最先接受了康德、叔本华的美学观念,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后的美学大师蔡元培、蔡仪都受到德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国美学对德国的借鉴侧重于理论资源,那么到了1950年代之后更着力于体系化的方法论,最著名的是1956年的当代美学大讨论。在争论中,德国古典美学的思维方式和建构方法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在整个美学界铺开,集中体现在王朝闻编写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美学教材《美学原理》,当时的青年编者李泽厚、刘纲纪、马奇、洪毅然、周来祥、李醒尘、朱狄、叶秀山、杨辛等日后成长为中国美学的半壁江山。就这样德国古典美学在中国的美学土壤中生根发芽,其研究方法、逻辑框架、论证内容都成为中国建构现代美学的基本参照和重要支柱。
由于195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在198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被更加全面地引入,德国古典美学严密的思维体系也深入人心。我们告别了中国古典文论零散破碎、含混感性的思维模式,开始建构一种严谨系统的现代美学的深度模式。但随着思维的解放和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之后的中国学界几乎在短短数十年间见证了西方百余年形成的各种思想。现代思潮、后现代理论以折叠压缩的高浓度方式奔涌而来。我们发现德国古典美学的精密性和系统性不断受到攻击,尤其是来自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和拆解。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思想交锋中,我们获得了另一种视野去重新反思中国现代美学模式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价值。
01
黑格尔美学的内在理路及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前30年,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被翻译得最多。在中国现代美学蓬勃发展且最具活力的1930年代,学界对黑格尔研究的热情与日俱增。“1928至1937年,关于黑格尔的文章约100篇,几乎是康德研究的三倍”(朱立元2016:2),特别是1933年为了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年,瞿世英、张君劢、贺麟、朱光潜等重要的美学家在《哲学评论》上以“黑格尔号”发表的一组文章影响深远。到了1950年代,中国学界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接受是根据政治坐标筛选的,虽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译本在1964年出版,但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质的语境中,康德被冠以“德国唯心主义美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的反动美学”而受到冷遇。1950到1970年代,由于尼采与法西斯主义连带而被屏蔽,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潮相左而被打入冷宫,席勒、谢林也没有被重视,而黑格尔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所以黑格尔被当作认识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一环,且马克思理论缺失的美学部分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补充。1959年,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出版,黑格尔美学在中国学界亮相;1979年《美学》二、三卷出版,黑格尔的影响更加深入,“黑格尔在哲学中确实达到超过前此一切哲学家的成就。在美学方面也是如此”(朱光潜1979:460)。1963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体现了他对黑格尔的思想化用,作为西方美学史的开山之作,它为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奠基了基本思路,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建构具有导向性,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一)逻辑推演:美的概念黑格尔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影响体现在美这一概念所蕴含着的逻辑理路。首先,美是超越感性的理性精神。美学在鲍姆加登意义上是“感性学”。Aesthetica所对应的德语词是sthetik,但从黑格尔学生的美学笔记中可以发现,黑格尔非常反对用sthetik,而是采用了“艺术哲学”。黑格尔认为感性是基本的低级的一种应激或接受能力,感觉作为“人和动物共有的”能力是灵魂最原始的能力,是对世界万物最直接的知觉接受;作为刚刚从自然回到自身的精神那无意识的、未被规定的愚钝的存在形式,感觉的核心规定乃是有如物质材料那般的直接性,还没有同外部实存区分开来。在黑格尔看来感性是初级的,而美/艺术的感性形式也是为了显示蕴藏着的理性精神,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黑格尔那里,理念有一群概念星丛:“真者”“绝对者”“精神”“理性”“上帝”,黑格尔“不是从感性的经验出发,而是从抽象的思辨出发”(周来祥286-287)。
其次,概念推演。美/艺术是绝对精神自我显现,如何表达精神?黑格尔提出了概念。在《美学讲演录(1820/1821)》中,黑格尔阐述了概念(内在精神)和实在性(外在表现)的关系:“概念与实在性之统一是真,实在性对概念并不十分重要,只是概念之表现,与概念相比就如肉体之于灵魂”(Hegel47),(1)1也就是说,“美”作为概念和实在性的统一,是理念/真的显像,美/艺术的逻辑植根于黑格尔的精神学说。而那些复杂多样、生动活泼、转瞬即逝的感性经验就被删选剪辑、提升抽象为概念,并在概念的逻辑中进行运动和演进。“黑格尔总是从绝对精神逻辑演进的角度来谈论艺术”(朱立元2019:156),“形成一种概念到概念、范畴到范畴的纯粹抽象形式的推移。[……]黑格尔美学中[……]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深刻的发展观、历史观。猜测到一些美学规律。”(周来祥286-287)概念以一种强大的逻辑思维和清晰的表达方式为感性经验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代言,某种意义上是对感觉经验的删减、改造和遮蔽。
不仅如此,这种概念推演的逻辑运动预设了一种先验性和必然性,事物的发展是在既定的逻辑框架内进行的,美学亦是如此。黑格尔从美的概念出发,辨析了美的基本问题、研究方法,并用这种预先推导出来的逻辑框架解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从而印证逻辑推理的合理性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黑格尔“完全运用理论思考的方式[……]美既然应该从它的本质和概念去认识,唯一的路径就是通过思考的概念作用”,“这种必然联系是一种向后的联系,从这向后的联系里它自己生发出来;也是一种向前的联系,从这向前的联系,它自己推动自己,因为它很丰富多产地从它本身又产生出其他东西,这样就让科学认识一直进展下去”(黑格尔1979:27-32)。黑格尔的方法论是“演变轴线”和“深层结构”(德勒兹、加塔利2010:14),演变轴线是作为客观的、中枢性的同一性,使得连续的阶段被系统地组建起来;深层结构则更像是一个基本的序列,它可以分解成同一性的基因密码,注入不同的事物,形成一种全面的复制。黑格尔的方法论在中国现代美学开山之作《美学概论》得到了全面运用,作者直言不讳地说:“美学研究的任务和方法”是学习并“力图运用”黑格尔《美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王朝闻8)。这造就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路径:一、将概念的逻辑推演架构放置在具体历史发展中,逻辑、理性即历史的本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二、逻辑思维的经验对象是高度同一的,设置了一个严丝合缝的美学框架。这以后中国现代美学著作基本沿用了这一思路,在美学史方面,在逻辑框架和概念推演中填充历史材料,从历史演进的纵向维度上展开美学问题的讨论;在美学原理方面,以抽象理论和思辨方法对各种美学问题进行横向铺展。
(二)世界的结构:有机体黑格尔的方法论即逻辑学,事物本身的规律就体现为逻辑,这个方法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事物本身的规律性。黑格尔的理论模型不是外在于事物的机器,而是一个内在自发的有机体。如同《美学》从美/艺术的概念出发,将艺术从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历史发展,并分析了各门艺术自身的理论,从一个事物的特殊本质,层层推进进而构造出庞大的理论体系。黑格尔受18世纪德国浪漫派“有机体”理论的启发,这一生物学概念被用于解释文学艺术、社会政治,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机械论的、内在的、可生长、可修复的自然模式。黑格尔认为:“在这个有机体中,每一个部分同时就是整体,因为它作为与绝对者的关系而持存;作为部分,它在机身之外还有别的部分,它是一个受限制者,并且只有通过这些别的部分才存在;他孤立地作为限制,是有缺陷的;只有通过与整体的关联,他才有意义和重要性”(1994:16)。如同树的逻辑:它的各部分相互交替地作为自身形式的原因和结果,有机体的其内在合目的性不仅表现为部分通过整体而可能,还表现为整体通过部分的自我产生而可能,是一种“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存在者”(康德223)。
事实上,有机内在性展现一种复制模式,树的逻辑遵循一生二、二生四的法则,树形结构有主杆、有枝杈,自身可以衍生出侧根,复制出了相似的衍生物,主杆先天拥有一个固定的内在逻辑,枝杈是不断模仿的结果,它是基于“一”来复制“多”,看似无限延伸,实则是闭合单一,它预设一种根本的、强有力的同一,遵循一种最高精神来达到二、三、四;树形逻辑等级分明,树形的整体逻辑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其中包含着核心部分、复制部分和自动生长机制,其运作模式是:局部只能从一个中心接受信息,并沿着预先确定的路径实施,这种等级化结构予树形结构以某种特权。
以德国古典哲学这一系统模式考察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中国无哲学。黑格尔认为哲学不是零碎知识的堆积,哲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整体。“真正的哲学是从西方开始。唯有在西方这种自我意识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在希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自由在开花”(黑格尔1959:106-107),“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史”(103)。同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朱光潜认为:“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鼓舞的力量”(1989a:301-302)。这蕴含了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力量,呈现出一种深度模式。而中国文化是一种平面的伦理秩序,多是“大团圆”结构:“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中国戏剧的关键往往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突变’的地方,很少在最后的结尾。剧本给人的总印象很少是阴郁的。仅仅元代(即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有五百多部剧作,但其中没有一部可以真正算得悲剧。”(朱光潜1989b:120-121)在这种语境中,在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思维模式对于非系统、散文化的中国传统文论来说,是一种极具吸引力和可操作性的异质思维,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们已经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体系重要思想资源,而中国古典文化也在这种视野下被删改、矮化、遮蔽。
02德勒兹对黑格尔体系的反思20世纪前半叶,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们不再相信精确缜密的世界秩序,黑格尔的完美体系也受到了后学者的反思,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解构主义理论家,他们认为如果上帝确如黑格尔所说通过计算来创造世界,他的计算始终不准确。正是这种不可还原的“不等性”成为世界得以存在的条件,世界是一个“余数”,一切现象都取决于偏斜与差异。在弑父的一代中,德勒兹最具代表性,他跟康德、黑格尔一样从形而上的角度思考世界,同时又将他们当作潜在对手逐一批判,试图开创一种全新的打开世界的方式。首先,德勒兹认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一种“纵向性”的思维方式,为了建立起一种体系,从一个不证自明的原初原则出发进行逻辑推理,按照不同的等级来安排“事理”,形成一个严整的等级体系,背后的指挥棒始终是同一。而德勒兹认为世界即差异,他将差异上升到本体地位。这是一个非中心化的系统,每个事物都是一个“场”上的一个自由粒子,它具有绝对差异,没有固定指向,有跨越层级自动游离的潜能,始终是不断运动、变化和生成的。其次,概念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命门,“黑格尔提出概念的抽象运动,而不是自然和心理的运动。黑格尔用特殊之于一般概念的抽象关系代替理念中独特之于普遍的真实关系。因此,他仍然存在于‘表征’的被反映因素之中,在简单的一般性之内。他再现概念,而不是戏剧性地表现理念:他创造了一个虚假的剧院,一种虚假的戏剧,一种虚假的运动。我们必须看到黑格尔如何背叛和曲解了直观的东西,以便把他的辩证法置于那种非内涵之中,以便把中介引入一种运动之中,而这种运动不过是他自己的思想及其一般性而已”(陈永国40)。德勒兹、迦塔利认为概念并非预先假设,而是一种创造:“概念不同于已经造就、静等人们去发现的天体。概念没有天空。它们必须被发明,被制造,或更准确地说,被创造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创造者的署名,概念便毫无价值”(德勒兹、迦塔利206)。具体到美学上,德勒兹与黑格尔针锋相对,提出了新的概念“感觉”“情动”和“无器官的身体”,试图解放传统美学对感觉的束缚。
(一)感觉的逻辑德勒兹将黑格尔贬低的感觉重新打捞起来,他通过层层否定的方式来重塑感觉。首先,感觉“不可缩减”(德勒兹2017:50),它拒绝再现事物、叙述故事,不能被简化、被通约;其次,感觉也不是感情,而是本能,即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力量;再次,感觉并非源于运动,速度和力量都不是感觉;最后,感觉不是单义的,而是一种变幻的延续性或系列。德勒兹用塞尚的画来谈感觉,塞尚的画不是在描摹事物、复刻景致、叙述故事,而是要画出感觉与身体,感觉从一个范畴到另一个范畴,主宰了变形,是身体变形的催化剂。绘画中形象就是被拉到了感觉层面,可感觉的形状,它直接对神经系统起作用,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而是肉体的感觉。它一面是朝向主体,一面朝向客体。感觉的逻辑破除主体的认知模式,让感觉的多样性、繁复性和游牧性充分地展现出来,即感觉强度在不断交流、回旋、共振。感觉穿过了有机组织到达身体,直接诉诸生命,宛如一道波与在身体上的各种力量的相遇。
感觉的逻辑批判了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通感/常识”(德文gemeinsinn,法文bonsens)。康德在解决美学问题的时候求助于常识,认为要使普遍有效的趣味判断成为可能,必须假定一个对一切主体都共同的常识,借助这一理想标准达成一致的判断。德勒兹认为“通感”蕴含着同一思维,各种感觉被综合在“我思”这一主体中。通感/常识看似遵循公平原则,却通过固定的、成比例的规定区分种类、确定界限,使事物各自拥有自己的范畴、属性,这是对感觉的一种钳制。而德勒兹感觉的逻辑是让身体所有感知能力都挣脱通感/常识的铰链。“为了达到超越性运用中的悖论元素,每一种能力都在其自身秩序中打碎了那将它维持在意见之经验元素之中的通感[常识]形式。所有能力聚合于一处,并为对一个对象进行认知的共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情形已不复存在。所有能力都参与到了一种发散的努力之中,每一种能力都在那根本性地关涉着它自身的东西那里直面着自己的‘特性’”(德勒兹2019:246)。德勒兹认为,感觉的多样性不应该被整合到一个更高的同一性中,而是要呈现自己的特性和差异,在不协调的节奏中,每种能力都逼近自身的极限,并与其他能力交织、滑动、相互作用。
(二)情动与身体在灵肉二分的传统哲学里,身体总是低级、脆弱、堕落的,而德勒兹突出了身体的重要性。他重新思考斯宾诺莎提出的问题“身体能做什么”,谈到一个关键概念“情动”。情动意味着身体(crops)之间的感触,是无数复杂的、“多元的力”相互碰撞产生的涌流;身体属于一个相遇的世界,世界属于不同的身体。德勒兹谈到,译者将斯宾诺莎拉丁语著作中affectio和affeaus不加区分的做法是“灾难性的”(2016:3),法语中affection、affect与affectio和affectus有严格对应。affectio即情状,指“一个物体(corps)在承受另一个物体作用之时的状态,‘我感觉太阳晒在身上’或者‘一束阳光落在你身上’即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上产生的作用”(9),是一种静态的效果;affectus即情动,指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之转变,是一个动态的变化。德勒兹认为:“通过我所拥有的情状—观念,我不停地穿越着这些行动能力之流变,通过我所拥有的情状—观念以及我所发生的际遇,我不停地追随着情动的连续流变之线,以至于在每个时刻,我的承受情动的力量都得以完全实现。”(14)可以看出,情动是存在之力与行动之力体现出一种强弱交替进行的连续流变。情动是对主体的批判和情绪的弃绝,情绪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而情动强调的是身体。西蒙·汤普森认为affect对立于emotion:“一个affect(如焦虑)是以身体的方式体验,而emotion(如嫉妒)是直接指向对象(爱人),予它以意义、重点和意向性。emotion是嵌入话语中的,而affect则似乎是从中脱离的”(Thompson3)。emotion依赖主体的形成,而affect强调身体之间的影响关系,一种纯粹强度和关系性的存在,这意味着身体没有固定的、先验的本质,只有不同事物的相遇和不同的影响,身体就这样从伦理秩序、灵肉二分的框架中脱离出来,被摆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三)不是有机体,而是无器官的身体德勒兹的“身体”与黑格尔的“有机体”针锋相对,他认为有机体不是身体,而是身体的敌人,有机体“将形式、功能、束缚、支配性和等级化的组织以及被组织的超越性强加给无器官身体,而这些都是为了从中获取一种有效的功用”(德勒兹、加塔利220)。德勒兹提出“无器官身体”,这并不是指没有器官的身体,而是指根据强度生成的自由的身体。无器官身体是逃脱组织的身体状态,是去机体化过程,也正是强度贯穿的过程,时而固定,时而迁移,“根据超前或滞后的波的来回摆动而出现加速、超前或迟缓的现象,即事后的动作,根据起作用的力量大小而出现的器官的确定性只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德勒兹2017:45)。
有机论、意义论、主体性与各种社会权力编码相关,是一种中心化、等级制的身体,而无器官身体是非中心的、解科层化的身体。瓦解有机体是“将身体向以下的事物开放:以一整套配置为前提的连接,流通循环,结合,分层和阈限,强度的流通和分布,以一个土地测量员的方式来度量的界域和解域”(德勒兹、加塔利222)。以塞尚的苹果为例,眼睛凝视苹果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心理投射,眼睛不是作为固定的器官,而是作为多维度、多功能、不确定的无机身体。塞尚画的不是苹果这个具象,而是身体这个形象。“绘画在我们身上都安了眼睛,在耳朵里、在肚子里、在肺部(绘画作品是有呼吸的……)。这是对绘画的双重定义:主观地,它进入了我们的眼睛,眼睛不再是有机的,成为多功能的、过渡性质的器官;客观地,它将一个身体的现实性展现在我们眼前,也就是从有机的再现中解脱了的线条与色彩。[……]身体的纯粹在场感将是可以被看到的,同时,眼睛将是获取这一在场感的器官”(德勒兹2017:69)。眼睛成为所有能感受的器官,从有机体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多维的、无机的身体器官;艺术超越了再现,通过形象使无器官的身体得以展现。只有摆脱主客二分的思想范式,我们的感觉才不被固定的范式组织,不被理性的框架钳制,是游牧的、自在的。
03
后现代理论视域下中国美学的再发现
(一)树的逻辑与块茎思维黑格尔树的逻辑意味着在树的凹陷处、分枝处,会形成一个新的枝杈,即便是主根夭折,但根的统一性仍然持存,这意味着始终有一种替补维度,同一性在其中继续运作着。根的系统尚未真正摆脱二元论,它具有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一种自然实在和一种精神实在之间的互补性:在客体中,统一性不断遭到阻碍,但在主体中,一种新的统一性却获得胜利。而德勒兹提出块茎思维,块茎自身具有异常多样的形态,从在各个方向上分叉的表面延展,到凝聚成块茎的形态,是一个网状的多元体,不是tobe...to be结构,而是and...and...and结构,可以无限衍生,不断生成状态,在无限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性。
首先,“多”与“一”的关系:块茎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是异质性的共通体。“多元体是块茎式的,它揭穿了树形的伪-多元体。统一性不再作为客体的中枢,不再被分化于主客体之中。多元体既无主体,也无客体,只有规定性、数量、维度———只有在多元体改变自身的同时才能获得增长”(德勒兹、加塔利8)。在块茎中,我们无法发现点或位置,只存在线。我们不再有度量的单位,而只有度量的多元体或多变体。所有的多元体都是平伸的,无数抽象线、逃逸线占据了其所有的维度,形成多元体的平面,它们在与其他多元体建立连接时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本质。
其次,断裂和逃逸:“一个块茎可以在任意部分瓦解、中断,但它会沿着自身的某条线重新开始,正如人们无法消灭蚂蚁,它们形成了一个动物的块茎:即使绝大部分被消灭,仍然能不断地重新构成自身。所有块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territorialiser)、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德勒兹、加塔利10)每当节段线爆裂为一条逃逸线时,块茎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构成了块茎的一部分,这些线不停地相互联结,人们再也无法用二元论或二分法将其归类定性。然而,多元体可能遭遇到再度将其层化的组织、权力的构型,试图重新构造出一个主体,这需要永不停止的解域。
再次,不是模仿,拒绝复制。树的逻辑通过模仿和复制而形成一种等级,模仿将树的逻辑转译成一种形象,将主杆的逻辑植入为枝杈。模仿看似无限地生产他者,但只是单一地复现自身。而块茎拒绝模仿。德勒兹认为,块茎“可以在其所有的维度之中被连接,它可分解,可翻转,易于接受不断的变化。它可以被撕裂、被翻转,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剪接,可以被某个个体、群体、或社会重新加工”(德勒兹、加塔利15)。块茎是一种“反-谱系”,它不存在相似,不能被归属于任何固定的框架。
(二)中国传统美学价值的再发现首先,中国美学的“千高原”。
德勒兹认为树的逻辑主宰了西方思想,东方则呈现出另一种形象:它与庭园、草原(而非森林和耕地)相关联;通过个体的碎片化来培育块茎;将局限于封闭空间之中的畜牧业置于从属、次要的地位,或将其推向游牧民族出没的草原。西方是农业,它基于一条选定的谱系(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可变的个体);东方是园艺学,它基于少数(来自范围广泛的“无性繁殖系”的)个体(德勒兹、加塔利23)。德勒兹认为在西方,树的逻辑根深蒂固而失去了块茎。块茎通过变化、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始终是可分解、可连接、可翻转、可转变的,有多重入口、出口和无数逃逸线。块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通所界定。一座高原始终是处于中间,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点。一个块茎是由高原构成,高原即一个连续的、自振动的强度区域,不根据某个最高预设或外在目的,而是通过浅层的块茎与其他的块茎相连接的多元体来构造自己。每座高原都可以从任意角度被阅读,也可以与任意其他的高原建立关联。德勒兹认为,“西方欠缺的正是一门游牧学(Nomadologie)”(德勒兹、加塔利30),它与历史学相对立,让叙事增殖,就像是如此众多且具有多变维度的高原、一个多元体。
具体到美学,美是形容词,形容一种自由、美好的快乐和满足,可是一旦被加以冠词、从形容词变为名词时(lebeau),这是一个从感受差异到追问本质的转变过程,美在不停的追问中从驳杂的感觉简化为单一的美的定义。朱利安认为,“从品质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普遍:不再指认,而是定义”(3)。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一路走来,美成了与概念相一致的现象表征,通过美的事物的特殊性达到普世性,复数之美被删减成单数的美。而中国文化中,不需追问美的本质,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概念。比如《世说新语》中,美是“骨气”“简秀”“韶润”“思致”;在《二十四诗品》中,美是“元气”“冲淡”“纤浓”“沉着”“高古”等等,不一而足。美多种多样、相互补充,却从没有赋予某一个视点权威性和永久性,使其本质化、固定化,从而独占优势。以后现代思维去看中国传统美学,中国非本质化的特点恰恰是德国古典哲学无法涵盖的部分,中国美学就是一种相互映射、彼此交流的千高原。
其次,中国美学非本质化,更强调身体感觉。
块茎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树的逻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存有”(être),在这关系中,暗含着探寻一个开端、本质或基础的强力,而另一种方式从中间、经由中间出发,并非要抵达本质,它善于在事物之间运动,建立起一种“之间”的逻辑,颠覆了本体论,废黜了基础,取消了开端和终结。而“之间”(l.entre)的介词地位注定了它无焦点、不固定、非实存的特征。它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不拘泥于任何本质实存,游走在两者之间。朱利安认为,在本体论思想笼罩之下的欧洲思想无法捕捉到“之间”:因为本体论关注事物之“存有”,并赋予它们属性,而“之间”不具本性,不能被赋予实质;欧洲哲学无法抵达之处,中国文化却在发端处就已拥有,“人们将风景称之为‘山水’,将世界称之为‘天地’,将事物称之为‘东西’,将宇宙称之为‘乾坤’,这其中都有一种‘之间’思维,它并没有使某一方孤立存在进而本质化神圣化,而是非此非彼,若即若离,形成配比关系,开辟出一条通道”(吴娱玉162-170)。中国山水画从不像西方一样清晰明白、界限分明,而是擅长画欲晴还雨、朦胧缥缈的时分;不在“形似”,而在“传神”;不被某一个事物绑架,而是要展现变化、差异、瞬间和感觉,在高低、动静、明暗、固体液体、视觉听觉之间,敞开一个虚空容纳世界万象。在手法上处处留白,呈现出虚虚实实的风格。中国美学孕育着“之间”思维,它不否认差别,不刻意区分或凝化,而使差别得以相通、彼此转化,获得活力。
再次,中国美学的“生成”特质。
中国传统美学不让风景一览无余,甚至为了凸显其美,需要隐藏之,回避之,如此形成两重效果:一是显与隐,可见不可见相互映衬,形成一种变幻不断、无穷无尽之效果———美人一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若隐若现,才显芳姿;园林亦是如此,曲径通幽,一步一景。二是有无对立互补,阴阳相生相克,如蛟龙“藏于孕”“垂半尾”,隐显叵测,生气彰显,这使得在场/缺席和主体/客体的界限变得模糊,既可触知又在逃逸,在运动变化中,逃离本质化的辖制,不断自我生成。“生成”是德勒兹的重要概念,它“是特殊事件之间产生变化的一种纯粹运动,这不是说‘生成’是两种状态之间那个变化过程的呈现,相比于生产、最终和之间,‘生成’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处于成分混杂的术语之间,它不朝向特别的目标或者最终状态,‘生成’始终进行着”(Parr21)。差异化即是生成,“是一个根茎,它不是一棵分类树或谱系树。生成断然不是模仿,也不是同一化;它不再是退化—发展;它不再是对应,不再建立起对应的关系;它不再是繁衍,不再繁衍出一个家系,不再通过血缘关系而进行繁衍。生成是一个动词,具有其自身的容贯性;它不再导向,不再将我们导向‘出现’‘存在’‘相等’,或‘繁衍’”(德勒兹、加塔利336)。德勒兹的“生成”意味着非中心、非组织、注重差异、创造,始终处于一种无限的动态变化中。
论述至此,我们发现中国美学在德国古典美学与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交锋中呈现不同的思想特质:在德国古典美学的视域中,中国无哲学,无悲剧,无系统,是人类文明的“幼年”;而在后现代思潮中,中国传统美学成了西方思想无法抵达的“飞地”,无数理论家运用中国的思想反思西方的本质主义与二元模式,试图重新寻求一种认知世界的新模式。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我们一度因为西方的尺度而改变、反思,也误读着传统美学。这启示我们,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需要牢牢扎根于本土问题,批判地学习西方,批判地吸收古典,不拘泥于某一种思潮,不信奉某一种权威,将所有的理论当作中介,在开放的视域中完成新的知识生产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