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场,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谚语,其寓意为:即便出任知府一职者秉持清正廉洁之操守,在三年任期内亦能获取十万两白银之收益。无独有偶,针对知县这一官职,亦存在“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之谚,用以描述其收入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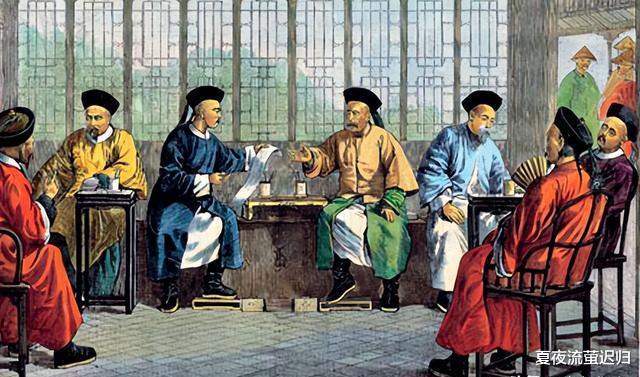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一表述,并非仅流传于民间,在清代官场亦得到广泛认同。据刑部所征引的相关资料显示,彼时将一年三万两白银界定为知县的额外收入基准数额。据此逻辑,在量刑判定时,若某位知县的年度收入未超出此数额,则不宜判定其为贪腐官员。
或有诸多读者对御史所陈观点存疑,无妨,不妨以详实史料为据,对知县之收支情况展开精确梳理与核算。
若旨在论证“一年三万”这一观点,理应排除对贪官事例的列举。经御史对相关资料的详细查阅与审慎分析,认定乾、嘉时期河南鲁山知县董作栋的情形颇具典型性,能够为该论证提供有力支撑。
董作栋,以进士身份入仕,据《鲁山县志》所载,其乃鲁山历史上备受赞誉的清廉官员。在当地历史长河中,董作栋声誉卓然。接下来,值得探究的是,这位清廉之吏,其年度收支状况究竟怎样。

【先来说收入。】
在清代,地方官员的收入主要涵盖两个类别。其一为经制内收入,亦称作合法收入。此类收入遵循既定规制,账目清晰、明示于众。依据清代文官俸禄体系,七品知县的年俸标准设定为45两白银。然而,就实际情形而言,彼时全国共计一千三百余名七品知县,鲜少有人能够全额领取俸禄。经实际考量,其到手俸禄通常介于41.5两至43.8两之间。
乾隆二年推行了一项名为“均摊俸银”的制度。关于负责该事宜的具体御史,因非核心要点,在此暂不赘述,只需知悉此制度的存在即可。
除法定正俸之外,地方官员还享有养廉银。由于各省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养廉银的设定标准亦随之有所不同。
据《清会典》记载,在全国范围内,河南省的养廉银水平处于中等层次。其中,河南巡抚的养廉银数额为15000两,布政使为8000两,知府的养廉银介于4000两至3000两之间,知县的养廉银则在2000两至1000两区间。在河南省诸多县域中,鲁山县的养廉银标准同样处于中等水平,其知县的养廉银为1400两。
经严谨核算,董作栋的合法收入由正俸与养廉银两部分构成。其中,正俸为43两,养廉银为1400两,两者合计达1443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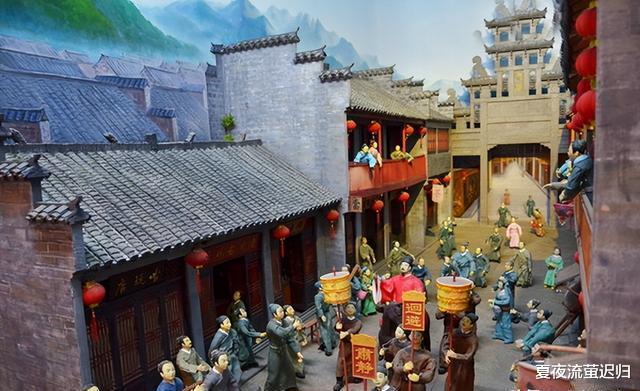
其二为法外所得。所谓法外所得,涵盖范畴极为宽泛,举凡处于合法与非法之模糊地带、性质未明之灰色收益,以及隐匿不宣之黑色收益,均能纳入此类范畴。
显而易见,董作栋对于法外收入中的这部分款项,并不会将其记录于公开账目之中,而是需依据鲁山县实际的财政收入状况进行估算。值得庆幸的是,在清代官场存在一项约定俗成的惯例,即每当有新官员履任,账房师爷依照惯例都要预先编制“须知册”。
“须知册”对鲁山县赋税收入有着详实记录:
每年额定征收地丁税银达二万四千余两,每两计征比率为一两六钱四分。于该税额中,扣除上缴部分后,每两留存三钱二分,据此核算,每年留存银约八千余两。
据相关记载,应征缴于民户的稻米数额约为二千余石。针对每石米,规定应征收白银四两六钱,而上缴入库的实际数额为四两二钱。
应征屯米数额达一千六百石有余,每石征收银两标准为三两五钱,而上缴数额规定为三两二钱。
税契方面,按年度计,应上缴银两数额约为四千余两。其征收标准为,以物产交易价格为基数,每一两产价需征缴白银八分,其中上缴至指定部门的额度为六分。
在鲁山县的财政收支体系中,以下四项构成其法外收入的一部分。以第一项为例,鲁山县实际征收的赋税数额较户部所规定的额定标准,多出15360两白银。依据相关惯例,此超出部分,一半需上缴至府、省等各级行政机构,而另一半,即7680两白银,则构成了鲁山县的法外收入。值得注意的是,户部对此部分额外收入持默认态度,其在实际财政操作中,与合法收入并无本质区别。

经综合统计,董作栋于鲁山任职期间,其每年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取的收入,涵盖灰色与黑色收入等,累计达32420余两。此数额相较法定俸禄,竟超出二十余倍。回溯乾、嘉时期,彼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全年收入尚不足50两。
【再来说支出。】
董作栋的收益状况表面上颇为可观,然而,其开支规模亦堪称庞大。
其一,为支付幕僚的酬金。
董作栋秉持勤勉理政之态度,凡事躬亲。其身旁设有首席幕友,此幕友身兼钱粮与刑名事务之管理职责,每年获酬八百八十两白银。与此同时,另有三位师爷辅佐。其中,一位司职账房相关事务,一位负责征比事宜,且这三位师爷亦承担着教育董氏子孙学业之重任,他们三人的薪酬共计六百两白银。

其二为胥吏相关费用支出。于鲁山县,设有“吏书十二名”,每位吏书支取工食银11.8两,另支取工银129两;差役人数达74人,每年支领工食银444两;县学斋夫、门子、膳夫共5人,每年支领工食银50.4两。不仅如此,招募团丁所需费用以及衙门日常办公开支,皆纳入此项核算范围。经统计,以上各项费用总计达12200余两。
其三为应酬费用。该费用数额难以精确界定,盖因其中相当比例是以应酬之名行“规费”之实。所谓“规费”,实则为向尊长上级馈送礼品所用之财资。
据鲁山《规费账簿》所载,于各个节庆之时,需向道员敬呈白银三百两,知府则为二百两。不仅如此,各级上司衙门中的师爷、门丁及长随等相关人员,亦均需予以周到的馈送。例如在端午节,董作栋便需支出白银八百余两。若以传统的三节两寿来计算,累计所需费用可达四千余两。

不仅如此,董作栋每年皆需前往省城履职,期间需谒见诸如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年所涉费用,保守估计亦达三千余两白银。
除此之外,行政体系中还存在上级摊派任务、京城权贵亲属以各种名义索求财物以及地方公共事业认捐等情况。尽管董作栋未对这些方面予以具体记录,然而,同治年间广东四会知县杜凤治所著笔记里,对上述事项却有着详尽阐释,据其所述,此几项每年总计不少于6000两白银。
上述各项支出皆纳入“公费”范畴。而在家庭用度方面,开支亦颇为可观。以董作栋为例,其家族人口共计十二人。尽管董作栋秉持生活简朴之原则,严格依据“人一岁食米三石六斗”这一平均标准进行消费,然其家庭一年之花销仍达四百两白银。
此外,尚存在部分零散开支,诸如向故乡寄递钱款、因人情世故产生的往来花销以及对亲属的经济援助等,此类费用总计约达两千两白银。

经分析可知,董作栋年度开支约达30000两(实际数额只会更高),而其收入为32200两,由此可见,年终结余颇为有限。鉴于此,若欲维持体面且奢华的生活水准,这般收支状况显然难以支撑。因此,“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之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客观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