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首批学员迅速集结。
那一届,被后人称作“将星的摇篮”。各党派的军事骨干,大多出自其中。
蒋介石初任校长,对这批学生格外看重。他亲自过问课程,严抓训练,却少有惩戒。
但偏有例外。
一位学生,仅入学三月,便被蒋介石亲手开除。他是黄埔一期中唯一被逐出学籍的人。
此后数年,此人始终是蒋介石最头疼的“旧部”,蒋介石视他为死敌。
顶撞蒋介石被开除1938年春,局势风雨欲来,西安暗流涌动。
一天清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收到了一份来自南昌的密电。
发信人是蒋介石,内容异常凶狠: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一名高级参谋,秘密处理,务必无声无息,不留痕迹。

命令下达,蒋鼎文心中五味杂陈。
一方面是解脱——此人长期令他头疼,是个麻烦制造者;但另一方面,又难免生出一丝遗憾——此人是他的同乡,是他在黄埔亲自带过的一期生,还是极少数具备卓越文才与胆识的人物。
任务不可推辞,情面也无法顾及。一场有预谋的“消除”,悄然启动。
时间来到1938年7月31日,西安。酷暑尚未散尽,夜色沉重压抑。
午夜一点,天水行营一间宅邸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子推着自行车走出。
他不紧不慢地前行,神情警觉,目光不时扫视两侧。
随后翻身上车,迅速穿行在寂静街头。
几乎在同一时刻,两名黑衣人从暗影中滑出,同样骑车紧随其后。
距离不远不近,始终吊在视线边缘。
前方骑车人似有所察,加快速度;后方紧咬不放,街巷间疾驰无声。

就在一处街口,局势骤变。一辆小汽车突兀冲出,斜停在路中央,拦住去路。
前车急刹,车轮划出刺耳声响。
周围黑影闪动,数人猛扑上前,将骑车人瞬间制服,强行拖入车内,车子掉头飞驰离去。
追踪者不慌不忙,迅速收拾现场,将倒地的自行车一并带走。
一切仅持续几分钟,动静不大,行动干净利索,连巡夜的警哨都未曾察觉。
那位被强行带走的男子,身份极为特殊。
他曾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中将主任,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宣侠父。
他是中共公开派驻国统区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更是蒋介石多年警惕的重点人物。

1924年初秋,黄埔军校刚开学两个月,一切都在探索中推进。
但就在这片看似秩序井然的操场背后,一场极为尖锐的冲突已悄然酝酿。
冲突的主角,是宣侠父。
作为黄埔一期第二大队学员,他年纪最大,资历最老,文才出众,说话风趣犀利,讲理有分寸。
他在同学中威望颇高,几乎人人佩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注定无法“安分守己”。
早在入学前,宣侠父已是共产党员。
他带着强烈的政治信仰走进军校,对党内事务自然格外敏感。
某天,黄埔将成立国民党党支部。校党部与队区党部的干部由投票选举产生,但最基层的党小组组长,却由“校长蒋中正”直接任命——而非选举。
消息一出,全校鸦雀无声。没人敢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决定。
没人,除了宣侠父。

他毫不犹豫地写了一份正式报告,递给蒋校长,开门见山指出:此举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请立即撤销命令,改为民主选举。
他言辞恳切,态度坚定,却在行政命令的铁板上,狠狠敲下了一记重锤。
蒋介石震怒。
他本以为自己一锤定音,不容质疑,却偏偏遇上这个“不识抬举”的学生。
蒋亲自召见宣侠父,劝他撤回报告,还口气颇为宽厚:“你要是愿意收回,我就既往不咎。”
宣侠父不卑不亢,缓缓作答:“提意见是我的责任,采不采纳是校长的权利。”
蒋介石当场翻脸,怒令将其关禁闭三日,限期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
三日过后,宣侠父再次被带去见蒋介石。
这次,他不但没写悔过书,反而直言道:“学生无过可悔。”
态度依旧从容。
蒋介石脸色铁青,怒不可遏,挥笔写下手令:“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屡教不改,开除学籍,即刻离校!”
不过,他还留了一道“台阶”:再给三天时间,只要悔过,仍可网开一面。

三天之内,全体教官联名请求通融,总教官何应钦亲自出面,被蒋当场驳回。眼见无望,众人只好求助于党代表廖仲恺。
廖从广州赶来,见到宣侠父,开门见山地劝他:“结束此事,对你来说,是委曲求全,但为革命受委屈,是不会使你受到伤害的。”
但宣侠父摇头。他说:“我个人的前途算不了什么,真正重要的是捍卫党内民主,防止专断成风。”
最后,他说出八个字,语气坚定如铁:“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
第四天,他没有妥协,没有低头。
宣侠父由此成了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挺直脊背,昂然离开了军校大门。
四处奔走宣扬抗日从黄埔军校被开除后,他带着满腹才学和一纸开除令,漂泊辗转,最终落脚西北,投奔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
在那里,他一干就是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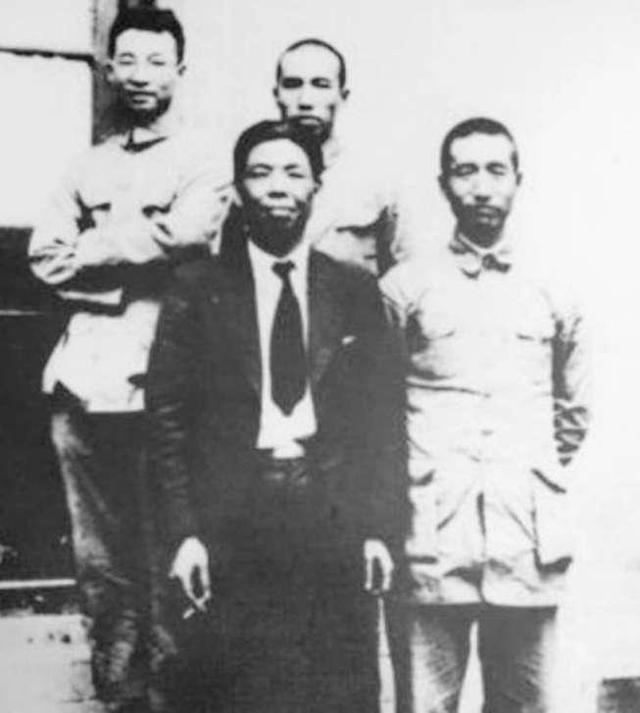
起初不过是谋个饭碗,但很快,他以政工专长脱颖而出,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刘郁芬部的军政治部主任。
职位不低,信任不浅,可惜他并非循规蹈矩之人。
就在任职期间,他完成了长达三十万字的《西北远征记》。
字里行间没有点名,却句句在点。
尤其对刘郁芬等人身上根深蒂固的军阀习气,他毫不留情。
结果不难预料,这本“说真话”的作品刚问世,他就被“礼送出境”。
1932年,他辗转来到镇江,临时投靠了黄埔一期的同学蒋超群。
靠老同学的照应,他才在生活上稍得安定。
不久,黄埔四期出身的妹夫胡醴泉将他安排到瓜洲三江营担任中队长,暂时摆脱了流浪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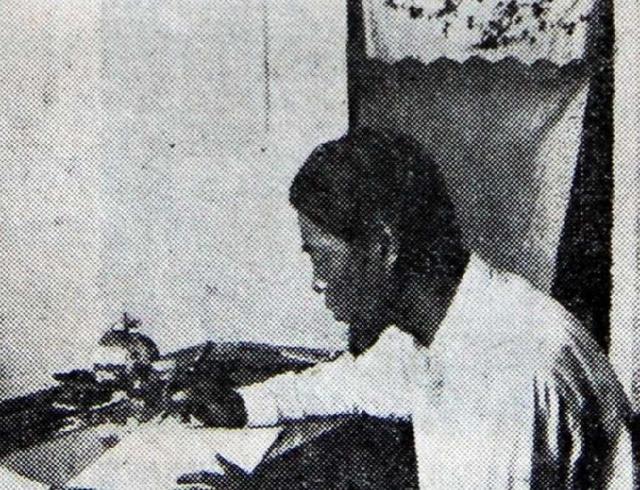
但宣侠父从不甘于只是“安稳”。在镇江期间,他又动笔写出小说《入伍前后》。
故事表面是虚构,骨子里却是批判现实。
整个故事清晰地传递出他对国民党内部的失望,以及对革命的认同。
小说出版不久,便遭封杀。
首印三千册还未上市,全部被查抄入库,书店被封,出版人周梦莲被捕。
警方全力追查“田雁”这一笔名背后的真身。压力直指作者本人。
此时,一批黄埔老同学又出现在这段历史中。
1933年,胡宗南与戴笠来镇江,与蒋超群寒暄之余,谈起了宣侠父。
蒋超群直言:“这样的人才,不该继续被放逐。”
几经权衡,蒋超群亲自赴南京求见蒋介石。

几番周折,蒋松口同意见面。
最终蒋介石点头同意重新安排工作,还“宽容”地表示可以一笔勾销往事。
宣侠父提出希望调往驻扎在淮阴的二十五路军。
原因也很清楚:军中总指挥梁冠英出身西北军,是他旧识,也较为开明。
1934年,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
宣侠父看得明白,也说得明白。
他直言不讳地劝梁冠英不要参与进去,还试图从中阻挠军令执行。
结果再度触怒蒋介石,调令随之而来:立即解除其职务,另行安排。

在此之后,宣侠父依然批评国民党抗战不力,到处发表演讲,写文章宣传抗日,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
蒋介石也无从下手,只好派出黄埔人士尝试再次拉拢宣侠父。
于是,老朋友胡宗南出场。他借着一次黄埔同学聚会,拉来了宣侠父。
觥筹交错,气氛热络,酒过三巡,胡宗南晃晃悠悠凑上来,话锋一转,说:“老兄,你在军校才高位卑,实在委屈。这样吧,我给校长说一声,让你出任政治工作厅厅长,如何?”
宣侠父听完,笑了。不是那种喜出望外的笑,而是冷冷一笑:“厅长?这官够大。但你忘了我怎么离开的黄埔?蒋校长会同意?”
胡宗南以为有戏,立马拍胸脯:“放心,全靠我安排。”
宣侠父还是淡淡一笑,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蒋校长再怎么大度,我恐怕也无福消受。要我去给国民党干活,做伤害共产党的事?那我可不来。但要是上前线打仗,不带条件,拿枪上阵,我绝对愿意。”
胡宗南当场哑火。从此,再没人试图劝宣侠父“弃暗投明”。
抗战英烈,永远铭记宣侠父的死,长久以来一直是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国民党高层对此讳莫如深,既无公开文件,也无官方说法。

多年来,传闻四起,版本众多。
直到1988年,一篇回忆文章悄然刊出,打破了沉默。
作者是原军统西北区负责人张严佛。
他披露:宣侠父的“失踪”,并非偶发,而是一场有计划、有执行、有指令的秘密暗杀。而下达命令的人,正是蒋介石本人。
张严佛的文章虽然交代清楚“怎么杀的”,却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杀”。
执行者知令,却不知其所以然。
外界的猜测不少,但多数观点指向一个核心:胡宗南。
胡宗南,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黄埔嫡系,是他在西北布下的反共主力。

胡部武器先进、兵力稳定,西北局势倚重于他。
而宣侠父,恰恰与胡宗南关系密切。
两人不仅同为黄埔出身,还有西北旧识背景。频繁往来,暗中谈话,令蒋极度不安。
蒋介石对军权的敏感,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时,他拒绝接受对方报送的干部名单,哪怕是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他坚持亲自点将,试图用任命权换取效忠。
这是他一贯的控制术:只要握住人事,就能掐住命脉。
更不用说自己的部队。
他对八路军尚且不放心,对嫡系将领更是寸步不离。胡宗南虽忠,但蒋从不真正放心。
美援武器照发,情报监控同步进行。他要掌握全局,不容模糊空间。

宣侠父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平衡。
他不属于体制,却频频出入胡宗南核心圈。
他不是主将,却能在军中影响思想。他不再是那个被开除的学生,而成了一个潜在的策反者。而且是极有能力的那种。
蒋介石想过拉拢。
他安排见面,试图重新收编这位“不听话的旧部”。
但宣侠父并不买账。他口头恭顺,行动依旧特立独行,甚至借机会反向渗透,扩大影响。
结果,蒋下了决心。
他知道,如果不能彻底清除宣侠父,就有可能失去胡宗南。
而“枪杆子”,是他最不能放手的东西。
他可以让步于统一战线,可以勉强接受共产党合法存在,但他绝不容忍有人动摇他手里的军权。
所以,他选择了最彻底的手段——密令军统,就地处理。

宣侠父,一个满怀热血、富有远见的青年将领,最终不是倒在抗日前线,也不是因战事牺牲,而是死于一场深夜袭击,死在特务枪口下。
西安,这座见证过无数王朝兴衰的古都,也收藏了他最后的踪影。
在那里,他曾为革命奔波,也在那片沉默中悄然陨落。
如今,人们已能以清醒的眼光审视历史,而那段被尘封的记忆,也终将在时间的河流中显影成形。
宣侠父是一个在黑暗中坚持信念的人,一个不愿低头的军人。
他的结局或许悲壮,但他的精神不朽。斯人已逝,英魂犹在。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中国,他所代表的,是一群人想要坚持做“对的事”的决心。
这永远值得铭记。
参考资料:蒋介石“密裁”宣侠父经过
辛叶

胡说八道
乱弹琴
蒋秃子真是地痞无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