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战火
1985年5月30日清晨,滇南的老山依然沉浸在那种典型的雨季气候中。整个山谷被浓重的雾气笼罩,潮湿的空气让人感到窒息,雨水细密而绵长。济南军区67军595团1营的战士们在这片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他们此行的目的很简单——接替南京军区第1军的驻防任务,守住那拉口子这一重要战区。

对这些刚到新阵地的战士们来说,天气的恶劣让本已沉重的行军任务更加艰难。路面上到处是泥水,每走一步,战士们的靴子都会被深深陷入泥浆中,仿佛每一步都在消耗他们的力气与耐性。雾气弥漫,视线极其有限,远处的山脊也似乎被雾霭吞没。
5月31日凌晨,整个老山地区的宁静突然被打破。凌晨5点10分,越南军队第二军区发起了名为“M-1”的作战计划,战火如同一把猛然点燃的火种,瞬间蔓延开来。位于227高地的越军炮群突然开火,猛烈的炮击向211高地倾泻而下。炮声如雷,密集的爆炸声不断震荡在山谷间,巨大的震撼让人几乎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67军595团1连的战士们此时刚刚从掩体里爬出,准备开始一天的巡逻与防守,他们却毫无准备地迎接了突如其来的攻击。刚爬出掩体的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任何防御准备,只见远处的越军已经如潮水般涌来。越军炮火的精准覆盖让211高地的防线瞬间崩溃。
那座曾经被他们精心布置的防御工事和坚守的阵地,在几分钟内彻底化为废墟。炮弹不断在高地上爆炸,泥土与石块飞溅,兵员被炸得四散飞扑。地面上的震动几乎让战士们无法站稳脚跟,四周的景象变得模糊不清,只有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与浓烟弥漫的空气。

而在这混乱的局面中,最让人痛心的是,1、2号哨位相继失守,防守的士兵几乎无一生还。战友们的身影被浓烟与灰尘吞噬,只有一名班长,鲍虎民,凭借着一股坚定的信念,最终凭借自己惊人的反应能力和不屈的意志,跳崖逃生,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战士,甚至连最后的逃生机会都没有。
粟戎生的强硬指挥
5月31日凌晨,211高地传来的战报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指挥部里,每个人的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时任199师师长的郑广臣少将坐在简陋的作战室里,盯着地图上标出的几处关键阵地,眉头紧锁。炮火刚停,他接到前线的紧急报告,越军的突袭让部队损失惨重,哨位接连失守。他建议部队先稳住阵脚,摸清敌情,等熟悉地形后再做打算。

67军参谋长粟戎生却完全听不进去这些劝告。他站在作战室另一头,声音洪亮地打断了郑广臣的话:“这时候犹豫就是畏战!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还等什么?”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在地图上重重地敲了几下,语气里满是急切和不容置疑的味道。
粟戎生是开国大将粟裕的儿子,身上带着一股天生的强硬劲儿。他认定,任何迟疑都是动摇军心的表现,必须立刻组织反击,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他的态度强硬,甚至直接给郑广臣扣上了“畏战动摇”的大帽子。作战室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参谋们低头不敢多说一句。

郑广臣还想再争取几句,可话还没出口,粟戎生已经转向军长,开始汇报自己的作战计划。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带着不容商量的气势,直接越过了师部的指挥链。军长听完,点了点头,显然被粟戎生的果断打动了。不一会儿,命令下来了:595团立刻反攻,郑广臣的指挥权被当场解除。
6月1日清晨,副营长王朝栋带着突击队,顶着风雨朝211高地冲了过去。他手里紧握着步枪,嘴里喊着“跟上我”,声音在风里显得有些模糊。战士们的军靴踩在泥水里,溅起一片片脏水,衣服早就湿透了,粘在身上又冷又重。可他们顾不上这些,只知道前面就是1号哨位,必须尽快夺回来。

刚靠近哨位,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尖利的呼啸声,越军的火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倾泻下来。炮弹炸开,泥土和碎石四处飞溅,突击队还没来得及找掩护,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10个战士几乎是瞬间倒下,他们的身体被炮火掀翻,鲜血顺着泥地流淌,和雨水混在一起,变成了一条条暗红色的细流。
好不容易,1连副连长贾柯带着残部杀到了哨位跟前。这家伙是个老兵,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打过硬仗,他带着人硬是把哨位抢了回来。可抬头一看,227高地的方向传来一阵刺眼的景象——越军竟然把阵亡战友的遗体挂在阵地上,像是在故意挑衅。

贾柯的眼睛一下子红了,那些牺牲的都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他攥紧了拳头,喉咙里发出一声怒吼:“跟我上!”他带着人又冲了出去,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泥水溅了他满脸,可他一点没退缩。冲到离哨位还有15米的地方,一发炮弹炸开,贾柯被掀进了一个弹坑,再也没爬起来。
冲锋与牺牲
从6月1日到接下来的十天里,67军的日子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噩梦里。前线的电话线几乎没断过,595团的战士们被派出去一次又一次,扛着枪,踩着满是泥水的山路,向211高地发起进攻。可每一次冲锋,越军的炮火就像是早早等着他们似的,炮弹从天而降,炸得山头满是烟尘和碎石。595团的队伍在这接连不断的攻势里被打得七零八落,伤员一批批抬下来,担架不够用的时候,就用破布和树枝临时凑合着往后送。

为了能撕开越军的防线,指挥部想了个办法,叫“添油战术”。这法子听着简单,就是把部队分成一小队一小队,按着党员、班长、团员的顺序轮番上阵。党员们先冲,喊着口号带着队伍往前跑,枪声一响,子弹和炮弹就跟长了眼睛一样追着他们打。
等这拨人倒下了,班长们再带着人补上去,端着步枪,猫着腰在炮火里找空隙。团员们排在最后,眼看着前面的队伍一个个倒下,才轮到他们扛着武器往前冲。3连的三个突击队就是这么被派出去的,第一队刚冲出去没多远,越军的机枪就扫了过来,十几个人没跑出几步就倒在了泥地里。

第二队接着上,炮弹炸得他们连掩体都找不到,地上满是弹坑和翻开的土。第三队的人还没冲到半路,炮火已经把前面的路封得死死的,最后只剩两个人踉踉跄跄地退了回来,身上满是泥和血,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211高地前面的通道完全被越军的炮火锁住了,火光和浓烟把整个山头裹得严严实实,想再往前挪一步都像是拿命去赌。
到了6月11日,枪声和炮声终于渐渐停了下来,211高地周围的山洞里挤满了67军的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着石壁,身上裹着被血染红的绷带,呻吟声和低语声混在一起。统计下来,120多名官兵就这么留在了这片被炮火翻得面目全非的土地上。

科技强军的转折
211高地的惨败虽然让67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场战斗的余波却意外地为中国陆军的未来点亮了一盏灯。仗打完没多久,到了1985年10月,事情开始有了新的动静。粟戎生,这位之前在指挥中吃了大亏的参谋长,带着一帮技术人员扎进了改装设备的工作中。他们盯上的是一堆原本用来当高炮靶子的靶-2靶机,这些家伙本来也就是在天上飞着让人打的靶子,外形简陋,功能单一。
可这回,粟戎生带着人硬是把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拆了又装,鼓捣出一套能遥控的侦察设备来。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响声没停过,技术员们围着这些机器忙活,手上满是油污,地上堆满了拆下来的零件和电线。他们给靶机装上无线电设备,又加了些简单的摄像头,折腾了好一阵子,第一代“土法无人机”就这么被弄出来了。

10月的时候,老山地区的上空开始出现这些小家伙的身影。它们晃晃悠悠地飞过山头,拍下了一张张模糊却有用的照片。那片397.5平方公里的战区,地形复杂,满是沟壑和密林,之前部队只能靠人踩着泥巴一步步去摸。现在有了这些照片,指挥部里的人拿着放大镜一张张看,把山脊的高度、敌人的炮位还有隐蔽的工事都标了出来。每次无人机飞回去,机身上都带着泥点子和树叶,地勤人员赶紧把胶卷卸下来,送到冲洗室去。一卷卷黑白照片铺在桌子上,成了接下来拔点作战的宝贝情报。
对粟戎生来说,这事儿不光是给部队添了个新家伙什,也把他自个儿的路给趟出来了。211高地的失利让他沉寂了好几年,军里的人提起他总有点嘀咕。可这回,他带着这套无人机搞出了名堂,风向慢慢变了。技术人员在靶场上测试的时候,他老站在旁边看,嘴里喊着调整参数,手上还拿个笔记本记数据。

后来,这套侦察系统的成果摆上了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奖状也送到了他手上。军里的会议上,他的名字又开始被人提起,桌子上的茶杯旁边多了几份文件,都是关于无人机改进的计划。几年下来,他靠着这股科技强军的劲头,硬是把自己的位置稳住了,还拿了好几项荣誉。
参考资料:[1]余果.粟戎生:将门虎子因戎而生[J].老同志之友(上半月),2009,0(1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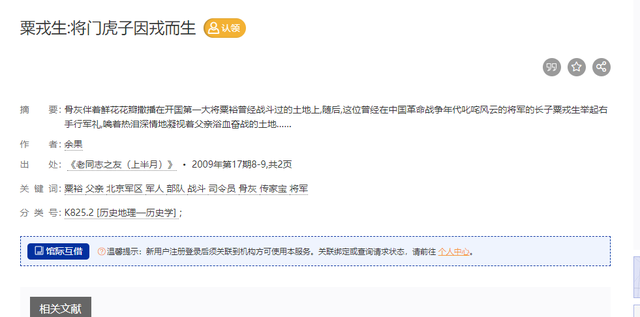

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