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腊月二十七,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我家低矮的土坯房里,我和母亲刚抱回一捆柴火,准备生火驱寒。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陌生而急促的呼喊声。一对衣着单薄的夫妇站在风雪中,脸上写满了疲惫和焦虑。他们恳求母亲:“大嫂,我们是从南边来的,去省城看亲戚,火车晚点错过了车。这大冷天的,能不能在您家借宿一晚?”
母亲看着他们冻得发紫的脸和瑟瑟发抖的身体,尽管家中并不宽裕,还是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院门,将他们迎了进去。这对夫妇,男的身材瘦高,裹着一件旧军大衣;女的则裹着满是补丁的棉袄,脚上的布鞋也已开线,看得出来一路的奔波。更让人揪心的是,她脸色苍白,不时捂着肚子咳嗽,似乎身体抱恙。

安顿好他们后,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她将原本堆放杂物的东屋收拾出来,铺上稻草和旧棉被,又去厨房做饭。我坐在火盆边,偷偷打量着这对陌生的夫妇,心里充满了好奇。他们虽然穿着破旧,但衣物干净整洁,男人的神情中透着几分焦急,而女人则一直捂着肚子,看起来十分虚弱。
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白菜炖粉条和红薯粥端上了桌。男人接过碗,低声告诉母亲,他的妻子怀孕四个月了,不能吃凉的。母亲听后,又赶紧煮了两个鸡蛋送过去。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轻轻叹了口气,"怀着孩子还跑这么远,真是造孽啊。"

夜里,风雪交加,呼啸的北风拍打着窗户,发出阵阵声响。母亲为了让他们睡得暖和些,特意拿出了珍藏的新被子。我有些不舍,那可是姨奶送来的好东西,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盖。可是看着女人蜷缩在炕上的虚弱模样,我又默默地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清晨,风雪停歇,男人执意要留下一些东西作为报答,却被母亲婉言谢绝了。“你们是有难处才来借宿的,东西我们不能收。”男人最终只留下了一小袋糖果,说是给我们的。临走时,男人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请求母亲帮忙寄给远方的亲戚。母亲接过信,答应等过了年就送到邮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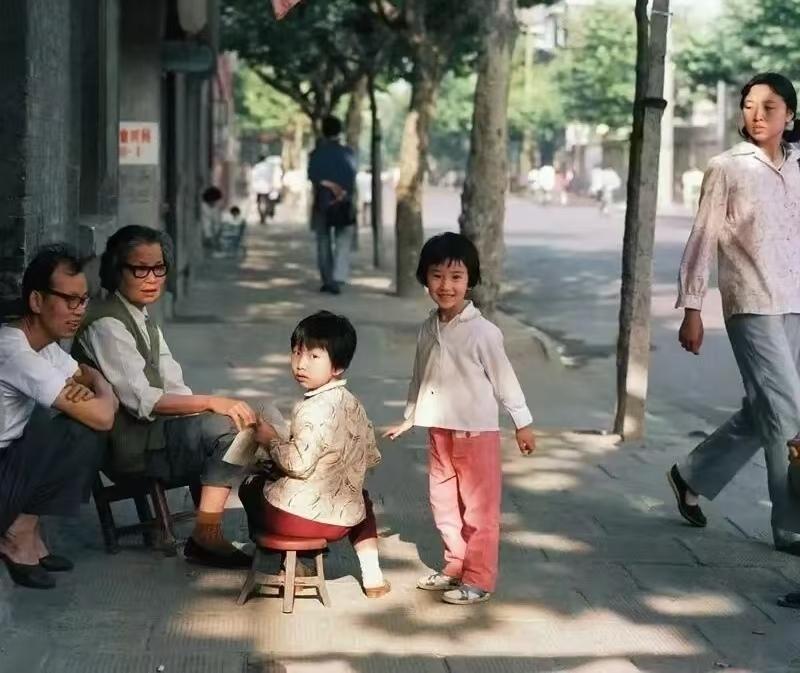
送他们到村口,看着他们渐渐消失在雪地里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丝莫名的感触。谁又能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会开启一段绵延数十年的情谊呢?
第二年的腊月二十五,天色渐暗,我和母亲正在包饺子,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突然,院子里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开门一看,竟然是去年借宿的那对夫妇!他们手里提着满满一篮子东西,脸上洋溢着笑容。“大嫂,去年多亏了您,我们这次特地来看看您,也当是给您拜个早年。”

母亲又惊又喜,连忙招呼他们进屋。篮子里装着活鸡、点心和酒,都是些过年用的好东西。母亲推辞着,"这怎么好意思,你们年年跑这么远路……"男人却认真地说起了那封信。原来,那封信并不是写给亲戚的,而是写给他的亲生母亲。他从小被送养到南方,多年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人。那封信,是他写给母亲的,希望能够通过这封信找到她。
母亲听后,眼圈红了。“那,后来呢?”男人抬起头,笑着说:“找到了!我娘在信里回复了我,说她也一直在找我。我们见面了,一家终于团圆了!”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紧紧握着男人的手,“好啊,好啊,团圆就好!”

男人接着说:“大嫂,我和媳妇商量过了,您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从今往后,每年春节,我们都要来看看您!”母亲摆摆手,笑着说:“说什么恩情,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从那以后,每年的腊月,这对夫妇都会带着礼物来看望母亲,就像走亲戚一样。而母亲也总是提前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热情地招待他们。
时光荏苒,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即将离开家乡。临行前,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记住,咱家虽然穷,但人穷志不穷。这世上,谁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母亲的这番话,我一直铭记于心。
去年腊月二十七,我回老家过年。刚进村,就听到有人喊我:“你快回家看看吧,有人来找你娘!”我心里一紧,连忙赶回家。推开院门,映入眼帘的,正是那对夫妇。他们站在风雪中,手里提着两大袋东西,头上落满了雪花也顾不得拍掉。男人红着眼眶说:“大嫂不在了,可咱们还是亲戚,一辈子的亲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中百感交集。
屋里的火盆烧得正旺,火光跳跃着,仿佛母亲的身影就在眼前,她看着我,笑得那么温暖。三十多年的光阴荏苒,这对夫妇的坚持,是否也映射出人世间最珍贵的真情?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这份承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