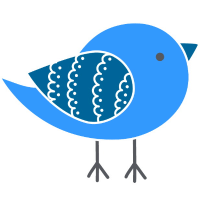进入二年级后,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南城各机关学校尤其是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学校的朝会上,留着齐耳短发,气质干练的李校长对全校师生作了大动员的报告。她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我们“以钢为纲”,15年内要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李校长号召我们全体师生都要投入“全民大办钢铁的运动中”,要掀起“以钢为纲,全面大跃进”的高潮,要创造一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办钢铁”的大好局面。因此,我们学校就全面停课,参与到街道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了。
一方面老师号召我们到处收集破铜烂铁,把家中闲置的和破烂的锅铁瓢盆凡是带有铁器的废旧物统统带来学校,学校称重计量,然后送去街道筑造的小高炉炼钢铁。而且上交得越多越好,谁交得多谁就是大炼钢铁的小英雄。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拾捡废品大军中的一员啦,家里的破铜烂铁毕竟有限,而且早被我们拿去与卖麦牙糖的货郎担交換麦牙糖吃掉了。我们翻垃圾桶,逡巡马路四方,只要检到了一点含铁的废品就高兴得跳起来。我们还把过去玩的铁环,铁丝扎的弹弓全都交了上去。每每学校收集了一箩筐的废铜烂铁就敲锣打鼓送往街道炼钢铁的小高炉处,看着我们努力收集上交的废铜烂铁被投进小高炉熊熊的烈火中,我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将要炼出的钢铁,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呀。
另一方面学校还应街道的要求,让我们为街道大炼钢铁的小高炉搓煤球,拾柴草。高年级的同学担运煤和黄泥并组织搅拌煤泥。我们低年级的同学就搓晒煤球。那段时日我们跟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卖力地搓晒煤球,常常搞得一身的泥巴,满脸的煤灰。我们一边搓煤球,一边又翻晒煤球,还不忘咧着嘴嘻嘻取笑别人是黑包公,大花脸。殊不知自己更像泥猴子,煤鬼子。然而取笑归取笑,我们都奋力地争取多搓煤球,因为学校要现场评比,看谁搓的煤球多,谁就能得到表扬。争强好胜的我,搓煤球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出色,我似乎天生就缺少运动细胞,动手的能力一向较差。在班上劳动课和美术课的手工制作方面,我都是弱者。搓煤球总是比别的同学搓得慢,而且搓出的煤球又小又难看,圆不圆扁不扁方不方正不正,有的还团不拢,一晒就散了。非但如此,我的花脸总是被大家取笑最多,都说我:“难怪蒋老师让齐红润扮小花猫,人家天生就长着一张猫脸吗,你们看黑胡须都长到了额头上,脸蛋上啦。真是笑死人啦,哈哈哈!”搓煤球、检废铜烂铁,拾柴伙帮助街道小高炉炼钢铁的活动持续了近两个月,随着小高炉炼出的几不像,我们学校停课参与“全民大炼钢铁”的活动就结束啦。
那是一个说不上是喜剧还是闹剧的下午,全校千多名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顶着十月的艳阳,敲着队鼓,打着腰鼓,举着迎风招展的队旗,和写有:“欢呼小高炉炼出高质量的钢铁,15年定要赶超英美帝国主义!”的横幅集合在小高炉正前方宽敞的晒煤坪上。左边是工人叔叔的队伍,他们擂起震天的大圆鼓,敲打大铜锣,每人摇着一面小红旗,高呼着大炼钢铁的口号,万分激动地迎候着小高炉的开炉。右边是农民伯伯的队伍,他们个个扮上了相,头系着白毛巾,身穿白短袿,腰里扎着大红绸缎,群情激奋,口号震天。除了喊着有关大炼钢铁的口号外,还高呼着:“人民公社好,幸福万万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高昂的口号。
口号刚一停就听见农民队伍里一声嘹亮的锁呐声响起,即刻从队伍中走出十多个妇女,个个红花衣,绿裤子,她们扭着十字步,唱着花鼓戏。戏文唱道:“人民公社好,全民大跃进。圈养千斤猪,亩产万担粮。食堂无限好,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鼓干劲呀,共产主义在眼前!”大家都鼓掌并齐声喝采。
这时只见有几个工人模样的大汉,打开小高炉冷却的炉灶,使出万钧的力量,用铁棍钢撬撬出一团还在冉冉升腾着热气的黑呼呼的东西。在众人震天的欢呼声中,大家看到炼出的这团巨型东西,既不像铁碴又不像是燋炭,更不像是什么钢,完全就是块锤不烂,敲不碎黑呼呼的大怪物。万众欢呼声,倾刻间变成了一片噫呀的惊叹声和惋惜声。
大家尽兴而来,扫兴而归,各自的队伍涣散着悻悻向四周散去。望着那一堆凝结在小高炉中的黑色怪物,大人们议论纷纷。他们愤愤地说,只可惜我们家的伢妹崽子从家中交上来的锅铁瓢盆了,只可惜他们辛辛苦苦顶着烈日在垃圾场翻检的破铜烂铁了,如今竟然是变成了这样一堆废物。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没有来庆贺小高炉出钢时的兴奋神情,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全焉头巴脑,唉声叹气的。这时,从西北天际迅急翻滚涌上一团团浓墨似的云彩,大地倾刻间变得灰暗,劲厉的秋风也乘势怒吼而来,把人吹得东摇西晃站不稳脚跟。
“不好啦,要下雨了,小同学们快跑吧,不然等下会被淋得七荤八素,像只落汤鸡。”那位吹锁纳的农民伯伯笑着呼唤我们。他的话音刚一落,突然天空“咔嚓”一声雷响,豆大的雨点便从天而降。一位工人师傅边跑边抱怨道,还真是邪门了,秋天竟然打起雷来啦,怪事!同学们一下子懵了,各班带队老师吹着哨子,慌忙指挥着让同学们四处避雨。蒋老师指挥着我们跟着队伍也朝小高炉边的工棚跑去,那处工棚是街道大炼钢的指挥部。我正往前拼命跑时,不跟脚的一只鞋掉啦,我连忙回头去检。这时高年级一个较高大的男同学正从我身后跑过来,他一手检起我跑掉的已被雨水打湿的鞋,一边抱起已淋成落汤鸡的矮小的我说:“噫,这不是小花猫吗,快跑吧!”说着他将我抱着跑到人挤人的工棚里。“小花猫,你这鞋大了不跟脚,怎么能跑快呢?”那个也淋成落汤鸡的男同学笑着抹去脸上的水,他弯下腰跟我穿上鞋,系上鞋绊。
“妈妈特意做大的,说我长得慢,鞋子还可以明年穿!”我一脸的雨水,抬起头感激地朝那个同学说。
“齐红润,齐红润,你在这里呀!”蒋老师从里面穿过人群,挤到我身边。
“蒋老师,我鞋子掉啦,是这个大哥哥跟我捡的,还是他抱我进来的。”我连忙对一脸焦急的蒋老师说。
“这位同学,你是高年级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谢谢你啦!”
“蒋老师,不用谢,我6年级甲班的,我叫汤德明。”那个哥哥笑着对蒋老师说。
“哦,汤德明,真是谢谢你!”蒋老师牵着我再次感谢那位大哥哥。我看见那位大哥哥不好意思地望着蒋老师笑得一脸灿烂。我记住了,他微黑的脸厐,浓眉大眼,露出白生生一口好看的牙齿。他的笑容和汤德明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中,一晃过去了六十年。

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我们全家几乎都上了炼钢铁的工地。照看三弟就是二弟分内的事和责任,好在我们家搬到电力学院快三年啦,二弟带着三弟在学院里可以满世界疯玩,只要不出学院的大门。正像过去我领着他们在学院里玩一样,但三弟较顽皮,二弟管不住他。一次他们在大礼堂学着电影《狼崖山五壮士》电影中跳崖的情节从大礼堂的舞台往下跳,三弟往下跳时,摔断了右腿。三弟的右腿夹了夹板,打了石膏绷带,只能卧在床上不能动弹。这下可要了三弟的命,平日里动如脱兔的他,哪里愿意被固定在床上呢。于是他变着法使喚着二弟,二弟稍有怠慢,他就山呼海叫地折磨二弟,又是掐又是咬,又是锤又是打的。老实的二弟无可奈何,只能任他打闹,只要能看住他不让他下床。好在是小孩子恢复得快,个把月三弟就拆除了石膏绷带,可以下床慢走了。个把月的时间,我们一家都在外面大炼钢铁,忙了个不亦乐乎,三弟却在床上将一铺竹板凉席磨得面目全非,完全散烂了。
随着街道小高炉炼钢的失败,我们也不用再去炼钢铁的工地,捡拾柴草,和煤搓晒煤球了。我们回到学校,李校长又在早会上动员我们要发奋努力,争取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学习的氛围紧张了,而且每天下午要增加一节课,还要在学校自习一节课。这样由原来每天下午三点多放学的时间,现在要推迟到临近下午五点钟。时令已是初冬季节,下午五点天已昏暗,夜幕垂临,初冬的寒风瑟瑟地吹来,扬起一片黄尘。学校附近的山山岭岭因大炼钢铁,树木全都砍光了,濯濯童山在寒彻的冷风中显得无依无靠,分外萧条。即便是我们抄近回家的那条山路,原来路两旁的树楂野草也都被砍了个精光,显露出路两旁狰狞可怖的嶙峋怪石。不久便是一场又一场的凄风苦雨漫天袭来,它将彻骨的寒意和弯弯山路的泥泞裹挟而来,行走在这条山路便有了些许惆怅和惶恐。于是我们再也不敢独自行走在这条山路了,即便是两人走也要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壮着胆子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前行。从学校往家里的路,似乎遥远了许多。根据天气的恶劣,学校决定还是减去下午那节自习课,让我们早点放学回家。
这天我回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推开家门,只看见母亲哭得昏天地暗,悲痛欲绝的。我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抽泣告诉我,父亲接到了广州大舅妈的来信,她告诉我们大舅已在韶关的硫磺矿死去了。母亲伤心地说,想不到前年春节与大舅的一别竟成了永别。后来,母亲告诉我,前年春节大舅就是从广州来长沙躲罪的。但后来回广州后大舅就被抓去韶关坐牢了,罪责是私自偷渡买卖黄金。大舅虽生得高大,但身体并不太健康,听母亲说大舅是外婆用药罐子喂养大的。大舅在韶关的劳改任务主要是挑硫磺,他身单力薄,本就耐不住艰难。后来他又被抽到韶关硫磺矿上的小高炉去大炼钢铁,没日没夜的在工地奋战,因此染上了风寒。终日咳嗽不止,以至成了肺痨病,咳血而死。及至大舅妈接到大舅死讯的通知去往韶关认领尸首时,大舅妈说,她也很难辨认大舅的尸首了,整个人变了形,佝偻弯曲成了一只干瘪的虾公。
大舅坐牢后,大舅妈也失去了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工作。后来在街道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很小的妇科诊所,带着三个表弟艰难的生活着。这篇记事写到这,笔触似有些沉重,大炼钢铁也好,大舅病死了也罢,好在那段岁月已经翻篇了。何况大舅的遭际也是他不识时务而一时贪念使之然,如果当初他不偷渡去香港,干些私自贩卖黄金之类违法的事,而是热切地参加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建设,想必也会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前程吧。
大舅的死更给道湖外公的一家,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这年的春节,二舅把外公送来了我们家,外公的到来为家里增添了几分节日的喜庆。七十多岁的外公早些年已不再在外为别家的婚庆喜嫁打喜奁了,他比外婆洒脱自在,也不操儿女家的心,而是安心乐意享度晚年。虽然这次大舅的死,对外公打击很大,但是外公表面似乎还较平静。外公虽清瘦,但身子骨还算硬朗,而且味口不错,每餐饭尤喜啖鱼肉。母亲即使节俭惯了,也要孝敬外公一日三餐鱼肉不断。餐桌上一个小小的蒸菜碗始终是外公的独有,碗中或几片扣肉,这是外公的最爱;或几坨腊鱼,外公稍有些嫌弃,他喜欢吃豆豉辣椒蒸鲜鱼块;或几块香肠腊肉,外公勉强接受,说是牙不好了,嚼起来有些费劲。当然外公不喜欢吃的鱼肉类,我们三兄弟都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可以在外公擦擦嘴离餐桌后,让母亲把外公剩在碗中的,我们巴巴看着的鱼肉虾 蟹分夹到我们只扒了两筷子的饭碗中。母亲笑着说:“快扒饭吧,小鬼头,巴巴地就等外公蒸菜碗中的剩菜吧。”于是我们仨便一阵风卷残云,只差没像母亲躲在厨房舔碗啦。

不知为何,外公也喜欢去技工学校对面的火葬场。每次他都要拄着拐杖,用那只戴着玉手镯子,青筋暴突的手牵着我去火葬场的尸骨骨灰陈列室观赏好半天。火葬场尸骨陈列室很大,窗明几净,一排排红漆的柜子上,陈放有许多的尸骨和骨灰样品。人体各个部件的骨头都有,都装在硕大的陶瓷盆里,并标志着各个部件骨头的名称或焚烧的程度过程等等。我那时不懂也不害怕,因曾和学院食堂的李叔叔早就去看过。而且上学后又和班上的同学去看过,春天我们还在公墓的山上采摘映山红,挖野笋,结结巴巴地读墓碑墓刻,所以很熟悉那里。那时,火葬场似乎从来就不限制人们参观,而且每次去骨灰陈列室,里边都有好几拨人,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品评,没看到有人神情紧张害怕的样子。外公也一样,他饶有兴趣地用拐杖对各部件的骨头指指点点,还把骨灰抓在手中,轻捏细扬,看看焚烧的粗细。但外公却笑看对我说,他死后不火葬,他要土葬,住在棺材里好歹是个家。外公死后虽是住进了棺材,在地下有一个家,但这个家外公并没住上几年。因为外公死后不到十年,埋葬它的山岗搞建筑,坟都被挖掘铲平了。我二舅去认领尸骨,还是凭外公手上带的那个青色的玉镯才找到装殓外公尸骨那口陶瓷罈子的。外公要地下有知,他是否会改变他在火葬场尸骨陈列室的初衷,不土葬而是火葬后留下尸骨或骨灰也陈列起来,让后人观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