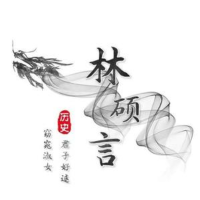68年,鲁迅的爱人许广平病逝,却留下遗言:坚决不与鲁迅合葬! - 今日头条
1968年,许广平突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在她快不行的时候,拉着儿子周海婴的手,泪流满面的说着遗言:“千万不能把我和先生葬在一起。”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回忆鲁迅文字中写的最感人的,远比许广平写的好,这不仅是因为萧红的才华,也是因为他更理解鲁迅,更深入他的内心。
虽然一度有鲁迅暗恋萧红说,比如那日萧红赴宴,许广平便给她找一条布条梳头发,最后在米色,绿色,桃红色中,唯独选中了桃红色,将它放在萧红的头上,对一旁的鲁迅说道“好看吧。”
当时鲁迅很严肃用的皱起了眉,脸色大变,说道“不要这样妆她……”,许广平瞬间不说话了,萧红也安静了下来。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一句话是老师你要和谁比呢?张爱玲和胡兰成。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

在鲁迅所有犀利作品中,唯独不同的便是他跟爱人许广平的《两地书》,“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却因平淡而显出可爱的真趣。
有着防蚂蚁的小窍门,有着对新对某种新鲜水果的见闻,有着满满的稚子琐事,“广平兄: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广平兄: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再谈。迅。”
“广平兄: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真实而动人。鲁迅也曾总结自己和许广平的感情,“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后来鲁迅在逝世前写给许广平的遗嘱是“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没有朱安,没有萧红,没有许羡苏,唯有二人。
两人最初的结识源于1925年。
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收到了北师大,大学生许广平的一封信,信的开头说道
“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吧,所以向先生陈诉……”
当时鲁迅不仅在北京大学任课,在1920,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学讲师,1923年也受聘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的教师。
这日,他收到了许广平的一封来信,信中所介绍的事项便是女师大风潮,原本女师大的校长是许寿裳,但是她在24年1924年的时候辞职了,由杨荫榆担任。

她因为是江苏无锡人,曾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过5年,又在美国哥伦比大学获得了教学学士学位,故而在接任校长后也曾一度将外国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工作中,却不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因此引起了反对大风潮。
后来在日本强迫中国签订21条的10周年纪念日,杨荫榆又组织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名人前来演讲,却被学生的嘘声轰了下来,后来她因此便要开除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学生。
风潮便逐步升级,后来也因此事许广平跟鲁迅的书信来往逐渐频繁,许广平三天两头就写一封信。
信中的称呼也极为有意思,鲁迅称其为广平兄,鲁迅据此解说,这是自己特定的用例,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
也能让收信人从这意外的称谓中感到一份亲切,而许广平自己的注写,则逐步从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改做小学生,改做鲁迅先生的学生,再到学生,后来改为(鲁迅师所赐许成立之名)小鬼许广平”了。

而在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便有幸去往拜访了鲁迅运家,当时她是跟同学林卓凤一同去的,称其为风窝探险,后来在《两地书》公开出版后又将其改为尊府。
在1926年左右,鲁迅跟包办之妻朱安道别,而后跟许广平一同坐上了南下的火车,彼时朱安曾一度对此事心怀忧虑,后来也曾据此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一个小男孩儿回家,母亲听后责怪她不识大体,净说胡话。
其实也算一语成谶。1935年7月16日,鲁迅曾给萧军写去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我们是相识十多年,同居七八年了,但何年何月何日是开始同居的呢,我可已经忘记了,只记得确是已经同居了而已。”
其中的我们,便是只他跟许广平了,二人同居了。
两人同居的消息最初并没有向外透露,故而不仅朱安对此事不知情,许羡苏也对此事不知情。

许羡苏也是跟女性跟鲁迅纠葛较深的一位女性,她是浙江绍兴人,曾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指的都是她。在1920年,她便跟兄长许钦文(青年作家)赶到北京。
当时刚刚20岁的许羡苏想要留在北京,想要报考北京大学,故而去找到周建人,因此住进了周宅。当时受到了鲁迅母亲的热烈欢迎。
不仅因为许羡苏算是老乡了,能讲地道的绍兴话,而且知识面积广,深得鲁迅母亲的喜爱,成了老太太的知音。
后来她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每逢周末和假日都要去找鲁迅的母亲聊天。
后来还见到了鲁迅,许羡苏后来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记叙了两人初见的情形。

在文中她表示,“只记得他给了我一个很严肃的印象,不多谈,进来转一转,看见有客就出去了。因为我是建人先生的学生,不是他的客人,叫老太太作太师母是从建人先生的关系而来的”。
第一次见面如此仓促,但许羡苏也曾一度早在许广平之前,被认为最有可能跟鲁迅结合的女子。
鲁迅跟最初跟许广平同居,许羡苏并不知道,她因为考虑到彼时天冷了,就寄去了围巾,随后又寄过去了自己亲手编的背心,后来此事也被鲁迅记录了日记中。
当时鲁迅和许广平已然开始同居了,自1927年10月开始,二人就住在同一栋住宅里,虽然鲁迅住2楼,许广平住3楼,鲁迅的住处放的也是单人床,对外也是宣称许广平是鲁迅的助手,但是亲朋好友早有察觉,每次宴请鲁迅时都要邀请上许广平,鲁迅的一些学生,甚至已经开始叫许广平为师母了。

关系至此悄然发生变化。后来在1929年,鲁迅跟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了,海婴的出生最初算是个意外。
后来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便介绍了此事,上面写到:“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
许广平怀孕时已经30岁了,生育时要到31岁,在当时的年代也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两个人最初都在考虑,纠结是否要留下这个孩子。
后来在生产时许广平难产,在医院病床上整整躺了20多个小时,仍然没有生下来。
当时鲁迅就在床边陪了一夜,一度对医生说要先保大人,但后来母子均安后,鲁迅兴奋得像个孩子。
后来,某日,弟弟周建人过来看海婴,鲁迅特意将孩子抱起来,让他看。

亲朋好友来也总是如此,将抱起孩子来,就像展示自己的作品一样。
彼时年少的海婴,每每据此表示反对,毕竟有时自己睡着了,父亲还要抱,还非得要抱起自己来,便哭天喊地的吵闹一番才算罢休。
虽然海婴是阴差阳错诞生的,但鲁迅也极为疼爱这个儿子。父子二人的生日极为相近,以阴历来算只差两天,故而鲁迅的生日还往往成为海婴生日的附属品。
后来在1931年九月二十五,本是鲁迅生日,但是“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主角却变成了海婴。
直到后来萧红的出现,萧红在与鲁迅和许广平熟识后,便经常到周府做客。而且每次相谈甚欢,总是不知不觉忘了时间。
鲁迅是萧红的恩师,对其作品的指点其中所花费的心血,都是众所周知的,故而也曾一度有两人的种种绯闻。

某次,因聊的高兴,忘了时间,萧红离开时已经是午夜一点了,当时还是许广平将萧红送出来。
因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天黑通通一片,故而鲁迅也极为担忧,一再叮嘱许广平,一定要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而且为了确保此事,还叮嘱许广平要先付车费。
此后萧红住到了北平四路,就离鲁迅家更近了,自此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隔三差五,萧红总是给鲁迅家做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喜欢吃北方饭的鲁迅,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儿。
在1936年,萧红只身东渡要去日本,他们分别那一天正好是7月15日,彼时的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宴为萧红践行,由许广平亲自下厨做菜。
彼时的鲁迅也是“已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一日不如一日,但仍然坚持着送萧红。
后来在分别前,鲁迅还叮嘱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

在三个月后,鲁迅便去世了,这三个月间他跟萧红没有任何联系,虽然萧军也觉得蹊跷,但很多年后,他也曾据此对别人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至于许广平,后来曾这样评叙自己与鲁迅的关系“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这一段文字发表后,也曾引起极大的争议,有人据此猜测许广平是否曾有过独立谋生的打算。
但不管几人关系如何,鲁迅都是那一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传奇斗士。

是在那个世界创造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作者,是曾经在战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自己也上了暗杀名单后,却坚定的选择去好友葬礼的人。
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者,是曾一度厉斥谣言,指出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的人。
抛弃他所有的谣言,且去敬仰这一位伟大的斗士,毕竟他曾以洞若观火眼睛,审视世间的一切丑恶,他曾用匕首一样的文字,将社会的不公,毫不留情的展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