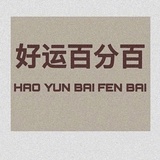在挑战他国国家豁免实践、维护自身权益上,伊朗是认真的
众所周知的就是,因为伊朗革命卫队在1979年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工作人员扣为人质,以及在1983年策划了系列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军营的爆炸袭击、造成超过250人的美国维和军队人员的死亡,自1984年开始,美国就将伊朗界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对伊朗的此定性一直维持到现在。
在前述背景下,美国于1996年修改了其《外国主权豁免法》,修改的内容主要是:一旦某国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如果该国在美国被指控涉嫌酷刑、法外处决、劫持人质,或为这些犯罪行为提供物质支持的类似诉讼案件中,该国将不再享受相应豁免。不仅如此,此类国家同样还不能享受执行豁免。在美国修改了《外国主权豁免法》之后,部分受害者或其家属即在美国提起了针对伊朗的诉讼。由于伊朗在此类案件中既不能享受诉讼豁免,也不能享受执行豁免,伊朗一直寻求通过不同途径来挑战美国的前述相关国内立法。可惜的是,在美国国内的挑战没有任何效果。而通过国际法院进行挑战,由于缺乏直接的管辖权基础和依据,伊朗也只能寻求“曲线救国”。这主要体现在伊朗诉美国“某些伊朗资产案”中。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伊朗虽然有挑战美国国内立法的想法,要实现此想法却殊为不易。原因很简单。国际法院基于“某些伊朗资产案”的管辖权是建立在1955年《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的基础之上的。由于管辖权受限于此条约,伊朗的相关诉求都必须基于此条约的相关条款来主张,只能指控美国的相关措施和实践构成了对此条约相关规定的违背。在这个意义上,伊朗在本案中只能打“擦边球”,间接地提出美国前述国内立法所引发的问题。国际法院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在3月30日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并没有对美国反恐立法是否侵犯伊朗基于国际法所享有的豁免问题作出裁决。伊朗想通过本案挑战美国前述立法的尝试未能实现。
在前述尝试未能成功之后,伊朗是否就此放弃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是这次,伊朗采取的还是“曲线救国”方式:伊朗直接挑战加拿大的相关国内立法与实践,认为其构成了对伊朗基于国际法所享有豁免的侵犯。
6月27日,伊朗在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加拿大的诉讼。在请求书中,伊朗指称:加拿大于2012年修改了本国的《国家豁免法》,随着此修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加拿大将不再享有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此修改具有溯及力。由于伊朗被加拿大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在加拿大遭到了相关诉讼,其部分国家财产也被执行。伊朗认为,加拿大的前述立法和实践构成了对伊朗基于国际法所享有豁免的侵犯。
由于加拿大的前述立法和实践完全是步美国的“后尘”,是在美国立法与实践后面“亦步亦趋”,在挑战美国相关立法和实践“投诉无门”的背景下,伊朗直接挑战加拿大的前述立法和实践,其目的和用意自然“不言自明”。
而在伊朗在国际法院起诉加拿大之前,为了解决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伊朗专门在6月25日发表了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在声明中,伊朗明确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局限于:(1)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2)对国家及其财产的限制措施的豁免。同时,伊朗还声明,其有权随时修改或撤回自己所发表的声明。由于加拿大此前早就发表了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伊朗在正式起诉的前一天发表此声明的目的和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了。
一旦伊朗能在诉加拿大的案件中获得突破,对于美国而言,伊朗的诉讼,是不是有“敲山震虎”之效?而从伊朗所采取的步骤及策略来看,在通过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伊朗显然展示了其过人之处,也显示了其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上的信心与娴熟。再联系到伊朗此前在国际法院所发起的针对美国的其他诉讼,伊朗的国际法实践无疑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
但对于伊朗的观察和跟进,我们显然不能仅停留在前述两个案件上,而应看到伊朗诉讼行为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7月4日,加拿大、瑞典、英国和乌克兰联合,在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伊朗的诉讼,指称后者于2020年1月8日击落一架乌克兰民航客机的行为及后续的作为违背了其基于《关于制止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第6条、第7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等所承担的义务。
那么,本案同前述伊朗诉美国、伊朗诉加拿大案有何“关联”?
在某种程度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前述三个案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看待:将这三个案件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要素就是:伊朗被美国、加拿大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蓄意毁坏航空器等行为被视为是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之一,一旦国家涉嫌从事此类行为,会被作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重要证据之一。
根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有八种不得援引豁免的情形;而在这八种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情形中,并没有包括“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此类情形。伊朗诉加拿大案和诉美国案的重要动因,正是伊朗试图挑战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内立法及其实践,阻止此类国家实践的进一步“漫延”。原因很简单:一旦此种实践进一步漫延,更多国家跟进美国和加拿大,“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极有可能发展成为第九种不得援引豁免的情形。
在此背景下,英国、加拿大等四国诉伊朗案的意义就一下子“凸显”了出来:一旦这四个原告国胜诉,以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为由,将其界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不就名正言顺了?在这个意义上,伊朗诉美国、伊朗诉加拿大这两个案件的作用力方向,与加拿大、英国等四国联合诉伊朗案的作用力方向,不是正好相反?伊朗与美国等国,正通过在国际法院的诉讼进行相关博弈。此种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当然值得关注和研究。
与此同时,联系到乌克兰诉俄罗斯案中32个国家宣布参加、从而在国际法院形成“群殴”俄罗斯的现象,由于加拿大等四国诉伊朗案涉及到对《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是否也会出现相关国家或站营加拿大等四国、或站营伊朗的“群体性”参加现象?这无疑同样值得关注。
作者最新文章
- 1 上合组织正式扩员,印度东道主却闹小情绪,左呛中国右批巴基斯坦
- 2 马克龙不在中美间站队?愿接纳中国融入全球秩序,却把台海当筹码
- 3 耶伦访华不止为推销美债?美国想向中国“要钱”,逼中国减免外债
- 4 美国大选将至,中美将迎来惊涛骇浪?崔天凯喊话美方:别光说不做
- 5 耶伦访华不止为推销美债?美国想向中国“要钱”,逼中国减免外债
- 6 台湾证实:俄军舰接近己方“应变区”,台军全程戒备,密切监视
- 7 中美互相反制,中国限制半导体原料出口,拜登限制中企使用云计算
- 8 想白拿美国大礼?莫迪被逼上贼船,白宫高官:印度在南海有大用处
- 9 中美互相反制,中国限制半导体原料出口,拜登限制中企使用云计算
- 10 德媒:中国在多方面有求于德国,柏林不需要对北京“卑躬屈膝”
国际TOP
- 1 197比102!韩国法案判决结果出炉
- 2 中国就是不给台阶,特朗普摊牌了,美国玩不下去了,向中国摇白旗
- 3 反水,因印度反对金砖国家未致成一致;巴西外长会罕见未发表公报
- 4 特朗普大仇得报!扎克伯格被罚款300亿美元,美国商界瞠目结舌
- 5 王毅外长董军防长首次配合,中方的安排有深意,对邻国极为重视
- 6 美国拒付会费,世卫组织宣布因预算缺口裁员重组
- 7 泰国殡葬业者捡死者金牙,10多颗熔成重21.31克的金条,赚6万泰铢
- 8 不到24小时,东盟欧盟集体让步,中国换了打法,对美文化霸权动刀
- 9 激烈交锋,中乌粮食交易清零,基辅提高召见等级,中方回了2句话
- 10 华盛顿大门已敞开,只等中方登门,特朗普以总统名义,立下保证书
国际最新文章
- 1 韩国最高法院宣布李在明“违反选举法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引发热议!
- 2 特朗普认怂了?承认"都是我的错"
- 3 中国海警展示五星红旗后,4月28日,菲强登铁线礁6人被当场扣下
- 4 朝鲜功利心极重,突然把事抖出来,让中国很为难,这绝非好消息
- 5 国民力量党:李在明选举法案最高法院判决日真相战胜谎言之时
- 6 韩国最大在野党表示:“韩德洙立即停止与美方谈判,否则将严肃追究韩德洙等人的责任!”引发热议!
- 7 英法等国退缩了
- 8 泰国殡葬业者捡死者金牙,10多颗熔成重21.31克的金条,赚6万泰铢
- 9 停止对华加税,特朗普四大金主下通牒,20多家美企来华,转机出现
- 10 反水,因印度反对金砖国家未致成一致;巴西外长会罕见未发表公报
热门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