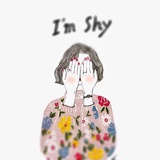公元621年,李世民率领唐军,进攻洛阳。王世充抵挡不住,最终兵败投降,其手下大将单雄信也成了俘虏。
最终,李世民赦免了王世充,但坚决下令要将单雄信处死。
就在这个时候,李世勣站了出来,为单雄信求情。
李世勣,是单雄信的同乡兼好友,又曾一同在瓦岗军效力,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李世勣对李世民说:“秦王殿下,单雄信骁勇善战,乃是一员虎将,我愿意用我的官爵换取他的性命。”
可是,李世民却不为所动。
他看着李世勣,冷冷地说:“单雄信这个人,反复无常,不可信任,绝不可留。”
说完,李世民拂袖而去,留下李世勣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李世民素以仁义著称,连王世充都能赦免,为何却执意要处死单雄信呢?
李世民素以仁义著称,连王世充都能赦免,为何却执意要处死单雄信呢?提起单雄信,很多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个“义薄云天”的绿林好汉形象。他手持金钉枣阳槊,胯下闪电乌龙驹,纵横沙场,快意恩仇。在《隋唐演义》等小说和评书中,单雄信更是被塑造成了瓦岗寨的“五虎上将”之一,是“二贤庄”的庄主,是江湖上人人敬仰的“总瓢把子”。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并非如此“光鲜亮丽”。真实的单雄信,虽然也是一位勇猛的将领,但他与演义中的形象,却有着很大的出入。他并非什么“绿林总瓢把子”,更不是什么“义薄云天”的英雄。
单雄信,是山东曹州人。他出身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他后来能够成为瓦岗军的“创始元老”来看,他家境应该还算不错,至少不是那种“赤贫”的农民。
单雄信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擅长使用马槊,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型的骑兵武器。单雄信能够熟练地使用马槊,可见他的力气和武艺,都非同一般。
单雄信有个同乡兼好友,他就是徐世勣(李世勣)。
徐世勣,也是曹州人,比单雄信小几岁。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就读过书,很有见识。他跟单雄信的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谈论天下大事。
在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徐世勣和单雄信,也动了“造反”的心思。但是,他们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公元611年,东郡法曹翟让,因为犯了法,被判了死刑。他偷偷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跑到瓦岗寨,聚众起义。
瓦岗寨,位于今天的河南滑县一带,是一片沼泽地。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是“落草为寇”的好地方。
翟让在瓦岗寨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单雄信和徐世勣的耳朵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就带着一帮人,去投奔了翟让。
翟让见到单雄信和徐世勣,非常高兴。他知道,这两人都是当地的“豪杰”,有了他们的加入,自己的队伍就能壮大起来。
就这样,单雄信和徐世勣,成了瓦岗军的“创始元老”。
但是,翟让虽然是瓦岗军的首领,但他却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为人仗义,喜欢结交朋友,但是在军事上,却没什么才能。
在翟让的领导下,瓦岗军只能算是一支“流寇”,根本无法与隋朝的正规军抗衡,这种情况直到李密的加入,才得到根本的改变。

李密,是隋朝末年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熟读兵书,善于出谋划策,很有才华。他本来是在隋朝宫廷担任左亲侍,可隋炀帝杨广却不信任他,执意把他调走。
李密一气之下,辞去了官职,专心致志读书,后来结识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
杨玄感起兵的时候,李密就是其身边的重要谋士。杨失败后,李密四处逃亡,最后来到了瓦岗寨,加入了瓦岗军。
李密的到来,给瓦岗军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不仅有才华,有谋略,而且还很会笼络人心。在他的带领下,瓦岗军迅速壮大,成为了一支能够与隋朝正规军抗衡的力量。
公元616年,李密指挥瓦岗军,打了一个大胜仗,击败并斩杀隋朝名将张须陀。
这一仗,让李密名声大噪,也让他在瓦岗军中的威望达到了顶峰。
不久,翟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把瓦岗军的“头把交椅”,让给李密。
翟让的这个决定,让很多人都感到不理解。有人说,他是“高风亮节”,主动让贤;也有人说,他是“迫不得已”,形势所逼。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李密是当上了瓦岗军的“新老大”。他被封为“魏公”,成了瓦岗军的最高统帅。而翟让呢,则退居二线,当起了“司徒”。
李密当上“老大”后,瓦岗军的“势头”更猛了。打了不少胜仗,地盘也越来越大。
看到瓦岗军形势一片大好,翟让的一些亲信,开始坐不住了。
翟让的哥哥翟弘,就对翟让说:“兄弟啊,这瓦岗军,是你一手创建起来的。现在,眼看着就要‘功成名就’了,你怎么能把‘天子’的位子,让给别人呢?”
翟让听了,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可是,李密却不能不把这话放在心上。他知道,翟让虽然已经“让贤”,但在瓦岗军中,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李密的亲信左长史房彦藻,因为曾经受到过翟让的斥责,添油加醋地在李密面前说了翟让不少坏话。

房彦藻对李密说:“魏公,翟让这个人,贪财好色,刚愎自用,而且还有‘不臣之心’,您可得早做打算啊!”
他还故意捏造了一些事情,说翟让曾经抱怨过,说李密把打仗得来的金银财宝,都给了自己的亲信,一点儿也不分给翟让的手下。
李密听了,更是怒火中烧。
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除掉翟让这个“心腹大患”。
公元617年11月11日,李密派人去请翟让,说到自己府上赴宴。
翟让呢,对李密还抱有一丝幻想。他觉得,李密毕竟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应该不会对自己下毒手。
于是,翟让就带着自己的哥哥翟弘、侄子翟摩侯,还有单雄信、徐世勣几个亲信,一起去赴宴了。
李密也做了一些“准备”,表面上对翟让“热情款待”,暗地里却安排了刀斧手,准备在宴会上动手。
宴会开始后,李密和翟让、翟弘等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
不一会,李密让人拿出一张好弓,递给翟让,说:“翟司徒,您看看这张弓怎么样?”

翟让接过弓,刚要拉开,突然,站在他身后的蔡建德,挥刀向他砍去。
翟让猝不及防,被砍倒在地,当场毙命。
翟弘、翟摩侯等人,也被李密的亲信给杀了。
徐世勣反应快,想跑,结果被守门的士兵砍伤了脖子,当场昏死过去。
士兵刚想补刀结果,王伯当大喝道:“这是徐世勣,不要杀他。”
一旁的单雄信看到这种情形,吓得当场“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密面前,连连求饶。
房彦藻见单雄信膝盖这么软,对李密劝说道:“魏公,单雄信这人,反复无常,不可留。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一起杀了,以绝后患!”
可是,李密却摇了摇头。
他觉得,单雄信虽然人品不怎么样,但毕竟是一员猛将,杀了可惜。而且,单雄信在军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能把他收为己用,对自己也有好处。
于是,李密就饶了单雄信一命,还把他给“安抚”了一番。

单雄信也识时务,立马就向李密表示效忠,并按照李密的吩咐,前去安抚翟让的部下,让他们服从李密的号令。
就这样,一场“鸿门宴”,结束了瓦岗军的“二元政治”。李密,成了瓦岗军唯一的“老大”。
后来,房彦藻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反复无常的单雄信再一次选择倒戈。在决定瓦岗军命运的邙山之战中,单雄信的表现,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当时,李密率领瓦岗军,与王世充的军队激战。由于李密的轻敌,瓦岗军中了王世充的埋伏,损失惨重。
就在这危急关头,单雄信拥兵自重,不听李密的调度,见死不救,直接投降了王世充。
单雄信的这一倒戈,直接导致了瓦岗军的全线崩溃,让李密再无翻盘的机会。
李密最后带着残部和王伯当合并一处,投靠关中的李渊。
单雄信投降王世充后,受到王世充的重用,被封为大将军。

公元619年,王世充废掉了隋朝的傀儡皇帝,自己当上了皇帝。
可是,他这个“皇帝”,也没当多久。
公元620年,李渊派遣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进攻洛阳。
王世充抵挡不住,只好向李世民投降,单雄信也成为了李世民的俘虏。
在决定如何处置单雄信之前,李世民曾私下里向瓦岗寨的旧将们打听过单雄信的为人。
他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
第一,单雄信这个人,贪生怕死。当初,翟让对他有恩,可是,他却眼睁睁地看着翟让被李密杀死,自己却为了活命,向李密屈膝投降。这种行为,可谓是“骨头软”。
第二,单雄信这个人,不忠不义。他跟随李密,本应忠心耿耿。可是,在邙山之战中,他却背叛了李密,投降了王世充,导致瓦岗军大败。这种行为,可谓是“不忠不义”。
第三,单雄信这个人,不识时务。他看不清天下大势,竟然与王世充这种“乱臣贼子”狼狈为奸,公开与大唐为敌。这种行为,可谓是“不识时务”。
综合这些信息,李世民得出了一个结论:单雄信这个人,绝不可留。
 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的是,单雄信曾经两次差点要了他的命。
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的是,单雄信曾经两次差点要了他的命。第一次,是在李世民围攻洛阳的时候。
当时,李世民带着一队骑兵,去侦察敌情。结果,遇到了单雄信的骑兵。
单雄信一马当先,挥舞着长枪,直奔李世民而来。
李世民的卫队,拼死抵抗,才勉强挡住了单雄信的进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世勣赶到了。
他大声喊道:“住手,这是秦王殿下!”
单雄信一听,愣了一下,这才收住了长枪,主动退兵而去。
李世民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第二次,是在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去榆窠打猎的时候。
当时,王世充带着几万步骑兵,跟李世民撞上了。
单雄信又一次冲在了最前面,挥舞着长枪,直取李世民。
李世民的弓箭,在近战中发挥不了作用,眼看就要被单雄信给刺中。
就在这“危急时刻”,尉迟敬德从斜刺里杀了出来,一枪把单雄信给挑下了马。
李世民又一次死里逃生。
这两次“险情”,让李世民心有余悸,再加上瓦岗军旧将对单雄信的评价,李世民最终做出了处决单雄行的决定。

李世勣得知李世民要处决单雄信后,赶紧跑去求情,希望看在单雄信勇猛善战的份上,用自己的官爵换他一条命,但李世民不为所动,铁了心要杀单雄信。
求情未果的李世勣,只好将情况告知单雄信,但单雄信居然埋怨起了好友:“我就知道你办不成事。”
李世勣对单雄信说:“我并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不想与兄长一同赴死。我既为唐朝效力,忠义与私情两难全。况且,如果我死了,又有谁来照顾你的妻子儿女呢?”
临刑前,李世勣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递给单雄信吃,说:“就让这块肉随兄长化为尘土,也许可以不负当年我们结义的誓言吧。”

单雄信死后,李世勣收养了他的儿子,并一直照顾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