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这找夏禹都城遗址啊,那可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考古大比拼”!
先瞧瞧这山西安邑遗址,那可真是“穿越能手”,主要都是东周至汉代的遗存,像是什么魏国都城安邑之类的。嘿,说是要找夏禹都城呢,它可好,尽拿战国到汉代的东西出来,出土的篆字方砖、滴水瓦当啥的,跟夏禹时期那是八竿子打不着,就像一个走错片场的演员。虽说《史记》等文献硬说禹都安邑,可考古证据却无情地表明,它更像是战国时期魏都的“忠实粉丝”,跟夏代的关系啊,就像两条平行线,几乎没啥交集。那所谓的禹王台,估计也就是后世为了纪念啥的建的祭祀建筑,硬要把它说成夏禹都城核心,这不是硬拉郎配嘛!而且这考古成果,也没拿出啥夏代的直接证据,全靠后世文献牵强附会,就像没地基硬盖楼,摇摇欲坠啊!
再看看登封王城岗遗址,时间上属龙山文化中晚期,可能比夏禹建政还早,部分遗存倒是延续到了夏初。可这早期发掘的城址,面积小得可怜,才1万平方米,这哪能配得上都城的高大上规格呀,简直就像个“小矮人”站在都城的舞台上。后来虽说发现了外围城墙,可文化单一得就像一碗没放盐的白粥,寡淡无味。出土文物呢,也没啥高规格礼器,玉器、卜骨这些象征权力的遗物少得可怜,就像一个穷酸秀才,哪有都城该有的霸气。虽说部分学者硬推测它是禹都阳城,可就这出土文物等级和单一的文化,实在难以服众,这争议啊,就像野草一样,怎么都除不尽。
最后看看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那可真是这场“比拼”中的“潜力股”。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00年到前1800年,完美覆盖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早期,跟夏禹时代那是严丝合缝,就像量身定制的一样。下限还接近二里头文化的上限,形成了完整的时间链。地理位置更是没得说,《竹书纪年》《史记》这些文献都来“站台”,跟“禹都阳翟”的记载高度吻合,邻近南阳,跟禹征三苗的传说地理也相符,就像自带导航找到了历史的正确位置。考古发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800平方米的“回”字形夯土建筑基址,还有那奠基坑里的数十具人牲与动物牺牲,这祭祀礼仪规格,妥妥的国家范儿。出土的山东龙山文化陶鬶、湖北石家河文化玉鸟等,就像各国使者来朝贡,彰显了它“大都会”的跨区域影响力。五谷四畜的遗存,也符合夏代早期农业社会特征。而且人家还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的核心项目,这就像被官方盖章认证了一样,学界普遍认可它夏代早期都邑的性质。
这场“考古大比拼”下来,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在时间、地理、考古发现和文献契合度上全面开花,展现出早期夏王朝都邑的“王者气象”。登封王城岗遗址呢,顶多算个区域性中心“小角色”。山西安邑遗址,那就只能在战国时期的历史记忆里“自娱自乐”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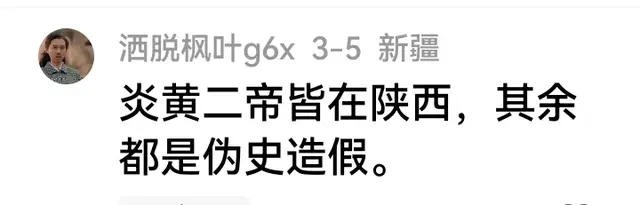

史记“昔三代居于河洛之间”意思是夏商周三个朝代国都在洛阳一带的河洛地区。夏商经常迁都,史记有明确记载且已挖掘到遗址的夏都有且不局限于以下这些:夏禹定都颍川阳翟(见史记夏本纪),阳翟为今河南禹州,对应有禹州瓦店遗址,后迁都至阳城(见史记夏本纪),阳城为今河南登封,对应有登封王城岗遗址,夏禹的孙子太康迁都斟鄩(见史记夏本纪),之后夏又迁都数次,最后夏桀又迁回斟鄩(见史记夏本纪)。史记等史书认为斟鄩在伊洛河地区(洛河与伊河交汇后也称伊洛河),唐朝学者认为斟鄩在伊洛河所在的巩义西南,巩义尚未发现遗址,但巩义西南的洛阳偃师县对应有二里头遗址,C14测年代相符合。登封、巩义古代也属洛阳。巩义发现的有距今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应该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国都。偃师县除了夏都斟鄩遗址(二里头),还有个商都遗址,偃师商都遗址为商都西毫,商汤灭夏定都毫,汉书记载商汤的毫都位于偃师。史记记载商汤以毫为国都是因其先祖帝喾(五帝之一)也以毫为国都。西安地区在秦之前都属于边远地区,比如秦国被中原各国称作西戎(西方蛮夷),周灭商类似清军入关,正式迁都前的丰、镐相当于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前的东北老家,三皇五帝夏商周长达三千年
石峁可是二里头的祖宗
世遗的好东西,都是韩国的,如果不是韩国的,绝对是河南的!!!
石峁遗址就是夏朝首都,已经得到国家考古界的一致认可!
中心论的人才是沉浸在自己的梦里,他们谈文化遗址就是自说自话,讲的全是学术霸权,不管你考古遗址的逻辑通不通?二里头就是石峁龙形雕刻齐家文化七孔玉刀,三星堆宝墩陶盉、高柄豆整个西边羌人人群的传承都能找到和商族开始接触的前哨站,国家文物局新闻发布会也说了二里头是人口具有比较持续稳定输入的结果,这些人群在山西就是胡说八道,二里头墓里出土的青铜器都是外来高等级人群出土,不是本地河南龙山文化人群的墓里出的,本地人就是低等级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