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忧心忡忡 朱由检)
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
对于明朝来说,这一年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份。
二月份,清军攻克了松山,三月份张献忠攻克了舒城,四月份清军又攻克了塔山,五月份张献忠又攻陷了庐州,七月份开封告急,八月份安庆发生兵变,十月开封失陷,十二月李自成拿下了襄阳。
可以说,哪个皇帝摊上这样的世道,那都得着急上火。
尤其是崇祯,他更加的着急,因为就在张献忠于当年五月攻陷了庐州之后,张献忠就兴师动众的在巢湖上搞起了一场声势震天的水军拉练。
巢湖,距离明朝的第二都城南京还不到数百里,那距离凤阳皇陵自然也很近,张献忠今天敢公然演习,明天他就敢带兵把明孝陵给刨个大坑。
崇祯很愤怒,皇帝心说你们南直隶的这帮官员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丢城失地还不算,现在祖坟也要守不住了,皇帝的愤怒简直无以言表,于是凤阳总督高斗光当即被免职。
高斗光下台之后,继任凤阳总督的,是大臣马士英。
马士英走马上任之后,压力也很大,崇祯年间的总督不会好干,那是纯玩命的工作,要么被起义军捉住杀掉,要么短时间内你干不出成绩,天威降下,也得被崇祯给砍了,总督的名头听着威风,可是凤阳毕竟只是小城,城防薄弱,城内都是老弱残兵,他马士英也是血肉之躯,农民军来了他也挡不住,所以马士英立刻就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抓紧募兵,增强凤阳的兵力,于是他很快派出了麾下一个叫做李章玉的将领,从凤阳出发,南下贵州,要求李章玉在贵州积极募兵,招揽人手,组成军队,然后再带兵回凤阳。

(思量对策 马士英)
而至于为什么要去贵州,原因很简单,贵州是马士英的老家,他对当地比较熟悉,他知道相较于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贵州的人口基数还是有的,募起兵来也比较方便。
李章玉领了命令,很快出发,抵达贵州之后他广泛招募乡勇,号召百姓入伍,很快就拉起了一支至少七千人的队伍。
这个过程,李章玉花了半年时间,等到他募兵结束,要从贵州返回凤阳的时候,可就已经到了年底了。
那么就在即将返程之际,李章玉突然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想回,反而回不去了。
从贵州到安徽凤阳,原本最便捷,最快的路线,是从沅江出发。
沅江,是长江流域中洞庭湖的支流,从沅江走水路,就可以连通长江,一直到长江的荆州流域,经过池州再往北,很快就能抵达凤阳。
这条原本可以走得通的返回之路,有两个必经点,一个是荆州,一个是池州。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李章玉走的时候,荆州还在朝廷的控制下,李章玉要回来的时候,荆州已经被李自成给拿下了。
荆州成了敌占区,那么就说明很大一段的长江水路,李章玉就都不能走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李章玉只能绕路江西,绕过整个鄱阳湖,到江西的九江之后,再走水路渡江。
不过坏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九江这条路,很快也走不通了,因为九江对面的黄梅县,早就被张献忠给占领了,也是敌占区。
那没办法了,只能是接着绕,从九江走陆路,到乐平,走祁门,经徽州,到绩溪,最后从绩溪转芜湖,从芜湖渡过长江,然后再步行返回凤阳。
可以说,这是兜了一个大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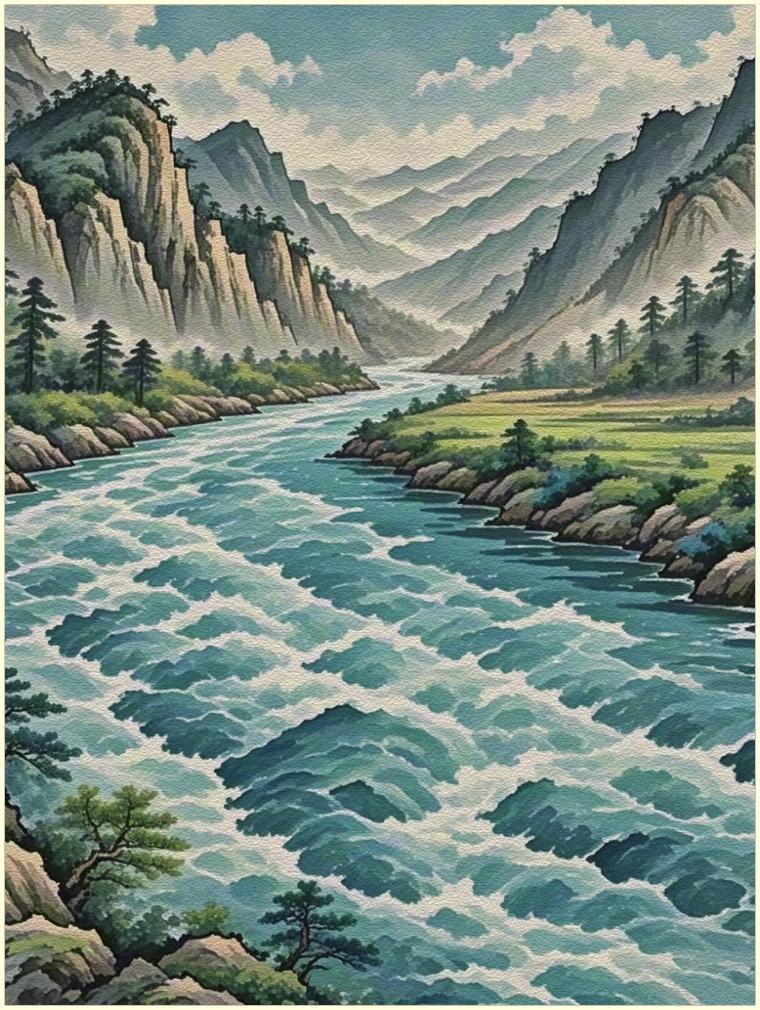
(江水滔滔 阻隔去路)
如果说只是兜圈子那也就算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就走呗,可是问题是,绕路绕的越多,这麻烦就越多。
本朝军队行军,每到一地,都要提前通知,要给行军路线上的州府县乡提前送交书信,你得告诉人家你是谁,你什么时候来,你来了干嘛,什么时候走,要到哪里去,反正事无巨细,你都得老老实实的写明白了,你不提前告知,你不证明身份,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你是正规军还是闯军假扮的?
所以,就算是麻烦,李章玉所部也得照办。
这一天,他们绕路绕了挺老长时间,就要进入徽州府,所以李章玉按照规矩,就提前给徽州府送去书信,提供了完备的信息和资料,说自己这支军队要从徽州过,麻烦徽州府接待一下,住的地方,吃的东西,要更换的马匹,反正总要提前给我准备好了。
如果是在以前,那也就是走个流程的事儿,李章玉的军队来了,徽州府派几个工作人员接待一下,劳军犒军,消停的送走了就算完事儿。
可是,此时毕竟是天下大乱之际,这人心不古,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军队,他们时常cosplay成明军,也给地方衙门发送信件,通过这种方式来诓骗地方守军打开城门,实在是不得不提防啊。
所以,当李章玉的信件送到徽州府的时候,徽州府就严重怀疑,李章玉所部是不是也是农民军假扮的。
这倒不是徽州府太过敏感,也不是他们过于疑神疑鬼,而是李章玉信件中提供的这个行军路线,在徽州府的官员来看,那简直是太过吊诡了。
李章玉的军队既然已经到了九江,那么在正常人看来,他就应该往上走,经过池州到芜湖,再从池州方向返回凤阳,怎么可能放着池州不走,反而绕大老远的路往咱们这徽州山区里钻呢?
荆州被占领了,黄梅被占领了,可池州仍然在明军手里啊,还有大将左良玉驻防,但凡智力没有问题,肯定都会走池州。
所以,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此行迹可疑的一支队伍,那肯定不是官军,而是农民军。
在认定了李章玉所部是反贼乱匪之后,徽州府可以说是如临大敌,整个徽州府全面戒严,专门张贴告示,让乡里,村镇都号召乡勇,拿起武器,时刻准备对来犯的贼人迎头痛击。
李章玉那边,他是毫不知情,很快带兵抵达了徽州府。

(带兵回凤 李章玉)
我们知道,这古代的军队啊,结构上往往分成前军,中军,后军,有在前头探路的先锋部队,有中间的精锐力量,还有负责殿后的,那么这一次率先进入徽州府的,就是李章玉的先锋部队,共计七百人。
这七百人到了哪里呢,到了徽州府的祁门县。
祁门县老早就得到了上头派发下来的警戒消息,所以这七百明军到了祁门县,祁门县对他们十分警惕,生怕是农民军乔装打扮的,所以压根就没让他们进城,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了城外的一个祠堂里。
如果说这七百人在祠堂里休整完毕,离开祁门奔下一站,那也就没事了,但是偏偏,这支临时拉起来的队伍,那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军风败坏,他们非但不肯老老实实的待在祠堂里,反而四处烧杀抢掠,骚扰百姓,抢了不少东西还不算,还动手格杀了数十个无辜平民。
百姓嘛,在军士们看来命如草芥,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们早晚都要死,不是战死就是饿死,可是这帮军士们忘记了,他们行凶作恶的地方不是别处,而是徽州府。
徽州,这个地方的宗族凝聚力很强,而且百姓普遍尚武,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聚族而居,可以说自古这里就是民风彪悍之地,本朝开国到如今,小三百年的时间里,在徽州这片土地上,那发生过的奇闻轶事简直太多了,你到人家地界上惹是生非,杀人作恶,人家能惯着你么?
所以,祁门县的乡勇们立刻拿出徽州府发过来的布告,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官军,而是乔装打扮的反贼,既然是反贼,那还等什么?灭了他们丫的。
祁门县的乡勇们一哄而上,将这七百多明军打杀了个精光,竟然一个活口也没留,随军的几百匹战马,也全被杀死。
消息传到李章玉的耳朵里,他当场就破防了,自己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走来走去,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筹措了这么点兵力,结果还没等上战场呢,先被老百姓消灭了十分之一,这像话吗?这合理吗?
李章玉二话不说,立刻一纸奏疏,就告到了朝廷,原原本本的把事情陈述了一遍,要求朝廷为他做主。

(徽州兵变)
这朝廷吧,也不是好糊弄的,朝廷说李章玉啊,这事儿的起因,在于你手底下的兵不老实啊,骚扰劫掠,还杀害百姓,所以这根本不能说是官军单方面被百姓杀掉,这属于是官军和百姓互殴,你有损失,人家老百姓也有损失,所以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人死了你也别追究了,我让徽州府祁门县赔偿你那几百匹战马就算完事儿了。
等于说,朝廷给了徽州府一个台阶下,因为不管怎么说,乡民暴起,杀害官兵,真要追究起来,你们徽州府也不好弄,所以让你赔点马息事宁人,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徽州府根本就不领朝廷的情,反而立刻驳斥,说哪儿有官军啊,没看见啊,我们杀掉的人都是反贼流寇,杀死的马也都是反贼流寇的马,我们干嘛要赔偿?不赔!
给你台阶你不下,朝廷也怒了,说你们这不是无理取闹么?于是这回也不和稀泥了,而是打算要重重处罚徽州府,要将当地官员连降三级,还要罚钱,还要赔偿人家李章玉的军资器械。
徽州府一听那更不干了,说就算这七百人真的是官军,可是他们也有问题啊,放着好道池州不走,非要往徽州跑,谁遇上谁都会认为是反贼。
徽州府抛出这个问题之后,朝廷也觉得很纳闷。
是啊,池州有友军驻防,虽然算不上一马平川,但肯定要比徽州的山地丘陵好走啊,李章玉舍近求远,舍安取危,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于是朝廷就问李章玉,说小李,你是怎么想的,放着好道你不走,你怎么偏偏走徽州呢?
李章玉也很纳闷,他说我不知道,反正走荆州有李自成,走黄梅有张献忠,我只能走徽州。
朝廷说不对不对,你怎么不从九江改道池州呢?
李章玉双手一摊,表示这就不是我说的算了,因为行军路线都是我的上司,凤阳总督马士英指定的,他就让我走徽州,不让我走池州,我也没有办法。
于是,问题又抛到了马士英的身上,朝廷又问马士英,说老马啊,你有什么战略决策,有什么战术思维,你不走池州一定是另有精妙安排啊对不对?
朝廷的思路是,总督级别的官员,制定出这样不合理的行军路线,其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合理性,说不定马士英让李章玉走徽州,是在憋个能拯救明朝的大活儿。

(驻兵池州 左良玉)
事实证明,朝廷想多了。
马士英脸一红,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故,这池州呐,是左良玉带兵驻防,我和左良玉一直政见不和,关系闹的很僵,我就不愿意让我的部队跟他有什么接触...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下文,徽州府受到处罚,但是处罚很轻,约等于无,李章玉也好,马士英也好,对这个处理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那个时候的大明,千疮百孔,事儿太多了,祁门县这一桩公案,已经没有人在乎了,何况一年之后,明朝就灭亡了。
想来,这些仓促招募的士兵其实既无家国信念,也无严格训练,他们劫掠成性,终于反噬了自己。
而徽州府乡勇们的反抗,难道不是基层社会在长期动荡中形成的暴力自卫本能吗?
当朝廷的正规军与民间武装互为猎手与猎物而极端寇雠时,王朝早已在自我消耗中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一个丧失制度弹性,信任基础与价值共识的政权,终究难逃在猜忌算计与内耗中自我瓦解的命运。
只是,马士英和左良玉的矛盾,却并没有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就此结束,两个人将会成为南明时代“内斗就要灭亡,灭亡也要内斗”的典型写照,恩恩怨怨,伴随余生...
参考资料:
《只麈谭》
《豫变纪略》
《明史·左良玉传》
《明季北略·卷十九》
吴行健.明清之际徽州士人的政治参与.安徽大学,2023
袁垣.武将选择与明末政局——以明末名将左良玉为例.西部学刊,2021


欧洲风车磨坊的风车,在没有风的时候,就不能转动和磨面粉,使用这种永磁电力,就能保证风车磨坊的风车,在没有风的情况下,也能转动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