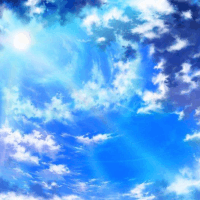从《望春风》到《风恋秋》(代序)
文/庄马炮

在《望春风》一书自序中,我写到了业余创作是个人情感倾诉、宣泄的园地,还激发了对生活的热爱与顿悟;同时,工作水准的提高也得益于文学素养的提升,可以让更多人感受到法律的温度。
《望春风》是我十余年大部分随笔杂文的一次总回顾,就像别人帮我总结的一句“从风月写出风云,从‘小事’论出‘大理’,饱含着作者正义之声、呼唤道德回归的杂文集”;而《夏季风》风骨依旧,却更多地表现在不仅管中窥豹,还“小题大做”一番,延续着一种“愤青”的情结。到了《风恋秋》,似乎成了秋收的季节,但并没有出现“却道天凉好个秋”,冬风已悄然尾随而至。

不知从何时起,杂文变得名声不佳,还被一些人称为负能量的“发牢骚”等。我也曾因文惹祸,但始终执笔直抒胸臆没有退却,还自认为“打是疼,骂是爱”,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良好方式,也是在社会上传递一股正能量。
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寻找失落的尊严,才能发出更多富有理性生命力的声音,这是一股特别神奇的力量,如果汇集起来则可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望春风》里阐述的大多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生活小事,而《夏季风》的重要篇什则放在关注大千世界上,其共同点都是点点滴滴带着血与泪,字里行间表达爱与恨,只是尚缺文字功力,还没有达到“骂人有学问”的理想境界。《风恋秋》秉持着一颗炽热的心,从“法律边角料”中裁剪拼接出一个多刺的法苑。
俗话说,别人的老公最好,别人的老婆更顺眼漂亮,自己的孩子才是聪明伶俐可爱的。在狠抓落实“二胎”政策之际,《夏季风》是我的“第二胎”,它比《望春风》更添机灵好动,敢于打破某些禁区,也像制造绯闻一样,总想吸引更多人的眼球,不再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历经磨难“超生”的《风恋秋》,给人一种老年得子般的喜悦。其聪慧程度难下结论,倒是仍然不失童真。不同年代的“三兄弟姐妹”让人感觉都带有某些时代的印迹,脸孔有几分酷似。

扩大了“雷区”的侦探范围。《望春风》里对社会上司空见惯的“热点”问题进行春风向晚般的梳理,但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无奈。《夏季风》响应了中央的号召,敢于聚焦社会痼疾,对不符合人性的行为进行无情的鞭挞,同时也从宣泄不满到提醒如何建章立制“出谋划策”。《风恋秋》沿袭了《夏季风》的风向标,虽然“针砭时弊”的想法用于“降虎”乏力,但找一找“苍蝇”的藏身之处还是有迹可寻的。
多方位深层次阐释法律。本职工作已长期停留在重复机械的状态,内心已缺乏一股求进闯劲,但热爱生活一刻也没改变。在《望春风》中的“法眼茶话”像茶余饭后的消遣,已远远不能满足自己与周边人对法律的敬畏与信仰。于是,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在《夏季风》中重点论述“执法如山”与“执法如水”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风恋秋》既有风情万种的情感滴达,又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竭力撕开各种伪装的面孔,指出蔑视法律的要害,并对误入歧途的行为作出了温馨的法律提示。
表达手法力求多样化。《夏季风》汲取了《望春风》里的一些营养,减少作报告似的空洞说教,更多地体现在寓庄于谐,能有一种悦读的快感。亲近了《风恋秋》,感受到了时令的变迁,叙述角度适当调整,以冷幽默阐述硬道理,以轻描淡写探索生与死的哲学问题,看淡人生的终局意义,或许还带有点命运的禅意。
“文字因缘”曾令人自我陶醉,“与文共舞”又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局限性,体验不失自我的成长阵痛,拓宽写作的时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虽然业余创作仍不被看好,所谓的“疗效”也相当有限,但路还在脚下,我自愿继续做一个不厌其烦、不怕流泪的剥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