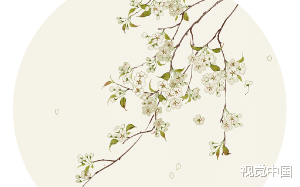我在方应珣忙得连日不着家的时候,亲自去县衙提了和离。
他头埋在卷宗里,眼皮都没抬一下:“越儿要归我方家,你别后悔就行。”
仿佛算准这只是我哭闹威胁的手段。
我牵起嘴角,长长的单子落在他案上:“这是当年郎君的聘礼,仲漪尽数归还,八十万两嫁妆我不要,越儿此生吃穿用度若是不够,我再给就是。”
“方大人,你我一别两宽。”
1
小小商家女竟然舍得同方家嫡长子和离。
消息一经传出,整个长安都物议如沸。
宴会上,相熟的女眷好奇询问,我笑脸嫣然,语气却讽刺:
“大抵方大人也没想到,旁人两年都办不到的事,轮到自己半盏茶的工夫就成了。”
也有看我不惯的:
“旁人都说方大人雷厉风行,如今看来倒不是,到底对人用的心思不一样,办起事来当快则快,当慢则慢。”
姜元容大抵是觉得方家少夫人的位置给她腾出来了,春风得意:“应珣待我一向亲厚,总是小心谨慎生怕我受委屈。”
我同方应珣成亲八年,八年前商家女一朝嫁入国公府,也是轰动一时的谈资。
婚后,我们也过了几年夫妻恩爱,举案齐眉好辰光。
不想短短两年时间,就走到今天这样分道扬镳的地步。
个中原因,还要从方应珣从前的未婚妻姜元容说起。
姜元容既是他的表妹,又是他的青梅。青梅要和离,可夫家势大不讲理,咬准了要休妻。
兴华坊本属长安县管辖,姜元容却一纸诉状投到了万年县令方应珣处。
方应珣若是有尾巴,大约早就高高摇起来了,日日帮忙理卷宗,查地契。
连姜元容嫁妆里的夜壶缺个油边儿都要论一论,生怕青梅受一丝委屈。
姜元容也是个妙人,今儿个说夫家薄待大张旗鼓要和离,明儿个又换成夫君同她也算情长颇有不舍。
要我看,无非是想多捞几个钱罢了。
姜家是方应珣的外家,自是簪缨满门。
可姜元容不知是哪个旁枝末节的孤女,当年从方家出嫁,还是我在前婆母授意下给她凑了嫁妆。
武皇在位数年,女子地位颇高,可扮柔弱从来都是激起怜悯的利器。
姜元容靠着自己和离的最新消息,倒也俘获了几位热衷八卦且同情心泛滥的贵女的芳心,落第失意的酸举子里也不乏她的拥趸。
我却有意扒一扒这位青梅的面皮。
探春宴上,我摇着扇子同旁人调笑:“如今女子也自强,和离不是甚么难事,只要肯舍钱财,总能得一个称心合意。”
话传出去,那些怜悯她的贵女和酸儒纷纷不满。
贵女们抵制我参加宴会,不同我下帖子,酸儒们则是口诛笔伐,用词颇是狠辣无情。
或许,再酝酿一些时日,便有人往我年府门楣扔烂菜叶了。
我倒是不甚在意,反正年家富庶,宅子多。
我只是想看看,若越儿也因此受影响,方应珣是选择青梅,还是儿子。
2
很快,方应珣便找上了我。
我正在铺子里盘账册,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大人竟十分罕见地贵步临贱地。
我本以为他会开口责备,拿越儿要挟我不要再拈酸吃醋。
意外地,他没有。
他揉了揉眉心,语气疲惫:
“仲漪,你知道的,我做事从不虎头蛇尾。府衙既接了元容的状纸,我便得负责到底。”
拨着算盘珠子,我头也不抬:“所以呢?”
他沉吟半晌,到底是拉不下世家贵子的脸,态度也渐渐倨傲冷硬起来:
“我和她从未逾矩,若你是因为旁人同我和离,实在是多此一举。”
这是警告,让我懂事省心些。
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一停,我也带了几分恼怒:
“大丈夫说话做事凭良心,你对着满天神明功曹想一想,这两年,你到底是为了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个父母官,还是为了你那点见不得人的不甘心。”
他或许自己都深信不疑,闻言便脱口而出:“我是万年县令。”
“你也知你是万年县令,长安县的姜云容你倒是着意得紧。”我冷笑一声,“这两年,有多少次,越儿生辰、病痛、拜师、骑射诸如此类需要父亲陪伴,可姜云容一张帖子你便招之即去。”
“而我,还要费尽心思为你圆谎,说你是万年县的父母官,自是万事缠身,要越儿好好读书,长大后也要像你一样功名在身,心怀天下。”
“去岁秋日里,越儿和顾国公、齐国公家几位公子去京郊打马球,你说要去县衙公干,半路便抛了我俩一走了之。那两家的世子都亲自下场教子侄,越儿要强,不肯示弱,不慎摔下马扭了胳膊。”
“那日我带着越儿匆匆回城找大夫,却看到禾丰楼里你同姜云容搂在一起,美人梨花带雨,郎君心焦难耐。你猜,越儿是什么心情?”
“你教教我,该当如何替你掩饰?”
方应珣沉默不言,或许是此刻惊觉对越儿的忽视,唤起了这人心中的一丝惭愧。
我不介意让他更惭愧一些,清了清嗓子继续道:
“方应珣,两年了,越儿从五岁长到了七岁,可他再不像从前一样缠着你练字习武,再不会去府门迎你下值,再不会喊你‘爹爹’而是换成了父亲,你以为是他长大了,懂事了,对吗?”
这两年来,我承受着方应珣的冷漠,负担着越儿的心事,扮演好方家的孝媳贤妻良母,还要时常面对姜元容直接或者间接给我的嘲讽难堪。
受够了。
端了杯中茶,我冷笑送客。
“方应珣,你已经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丈夫了,我是可以一走了之,可越儿既然还在你家,就还请方大人别再做一个令人作呕的父亲。”
3
我同方应珣说好,一旬里越儿可同我住两日。
这日,我如期套了马车亲自去方府接越儿,没想到方应珣也在。
他看起来不大修边幅,眼中血丝凌乱,眼底乌青缭绕,鬓边的青茬冒了头,素日里平整的袍衫皱皱巴巴。
剩下的几个通房和丫鬟是干什么吃的?
我之前预想的烂菜叶、臭鸡蛋都没有出现,交际也恢复如常,振聋发聩的话本子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大约是方应珣为着越儿使了些手段,让那群贵女酸儒闭了嘴。
我问他,他却说不是。
方应珣支开越儿,让他回房取衣衫,眼皮子撩着,状似随意地试探:“为什么不带越儿回年家?”
我愣了一愣,才意识到他所说的“回年家”是什么意思,心头不禁染了几分怒气:
“方应珣,你为了个外头的女人,连自己儿子都嫌累赘了?怎么,要我越儿为她姜元容的孩子腾地方吗?”
夫妻八年,他虽在姜元容一人身上拎不清,但总归也算端方君子,肩上也抗得起世家名门的责任。
他或许会为了一个尚未和离的女子抛妻,但到底不至于弃子。
果然,他皱了眉:“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怒气消散了一些,若他当真敢让旁人欺负越儿,我势必会让满长安大街小巷都传唱这对狗男女的故事。
“权衡利弊罢了,方家少夫人如今于我不过是枷锁,是笑话。”
我淡淡道,“可越儿不是,你百年世家,根基深厚,前程光明。就算你舍了一切同姜云容成婚也好,私奔也罢,你方家总不会轻易舍弃越儿。”
“我不愿他做商家子。”
英国公方家祖上有从龙之功,公爵之位世袭罔替,方应珣之父方道广官至殿中监,嫡支旁支十数儿郎都在官场里摸爬滚打。
他自己也争气,若无意外,方应珣也会同他祖父一样,从万年县令,到京兆尹,再到六部。运气好的话,还能拜中书侍郎,宰辅也尚未可知。
他靠山稳重,前途坦荡,而我不过是富商之女,家里纵使堆满了金山银山,也绝比不上他家族的荣光。
不说别的,若越儿是商家子,哪怕我年家家财能盖百座学堂,他也不能入弘文馆读书,这便是门槛。
方应珣或许没想到我会实话实说,闻言便有些失落地收起了玩味的表情。
我却调笑着弯了嘴角,一脸无辜:“我常劝你离姜元容远着些,你只会不耐烦,是不是笃定我舍不得越儿,只能被迫忍气吞声?”
“若你觉得我年仲漪是这样瞻前顾后,做小伏低之人,便心安理得地将所有时间和耐心奉送给姜元容,那你,真是够下贱。”
他额头青筋跳了又跳,到底是世家子的修养在身:“你一定要这么粗鄙吗?”
“奴奴不敢,奴家贺郎君千岁,佳人百年,贺你二人恩爱长久,举案齐眉。”
讽刺地行了个福礼,我甩着手绢要带越儿离开这晦气的地方。
他犹豫了半晌,在我身影即将在月门消失时叫住了我:“我本意并非如此。既然你不愿,元容的案宗我已移交给县丞。”
我的心中毫无波澜。
早干什么去了。
若在我头一次同他谈及姜元容时他如此答复,兴许越儿早就多了个妹妹。
若在我提出和离时他肯这样说,我说不准还真的会为了越儿再忍一忍。
只可惜,覆水难收。
商人重利,不管眼下还是今后,和离是我最好的出路。商人也果断,买定离手,再不回头。
“和离了才知道该怎样做,方应珣,你该招个太医来看看是否有头疾。”
4
纵使世风开放,女子位尊,谁又愿意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和离呢?
方应珣即便一直对姜元容念念不忘,但他身后是如日中天的方家,纵使他不在乎旁人如何看待自己,总要尽力维护家族的荣光。
故而我始终明白,方应珣同姜元容清清白白,仅限于借着和离的状子眉目传情。
虽然恶心,但也能忍,这便是我此前同方应珣得过且过的缘由。
可无论如何,姜元容不该放肆到越儿面前。
方应珣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为了这个幼时青梅,将越儿排在第二位。
两月前,方应珣答应带越儿学蹴鞠,半路却被姜元容的婢女当街拦了下来,也不知怎么想的,他急匆匆带着越儿一同去了姜元容处。
姜元容的婢女趁无人注意,捏着越儿的脸蛋同他讲,姜元容将会是他的母亲。
回家后越儿独自思忖了一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鼓起勇气向方应珣询问此事,却被方应珣认为是我利用越儿,逼迫他同姜元容断了关系。
他连点卯都不顾,当着下人的面在我房中摔摔打打。
等到越儿被吓哭,在院中说出前后因果,方应珣瞬间羞愧得无地自容,一句话没说就出了门。
晚间下了衙他对此事只字不提,只给我带了一支金步摇,给越儿带了一方昂贵的端砚,想要就此轻轻揭过去。
真好笑。
在外谦和有礼,到我这便是做错了也不敢认,这让我看他不起。
另则年家若想再进一步,得个皇商身份,照我和方应珣的关系,再过十年八年也够呛。
不论是理性上还是情感上,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不可取代之处了,干脆和离,也求个海阔天空。
但他的家世对越儿有用,我得把孩子留在这。
因此,为保越儿的荣华富贵,我决不能让姜元容有登堂入室的一丝可能。
索性就让她身败名裂,哪能让她一直恶心我,风水轮流转,如今也轮到我恶心恶心她了。
哪怕,这手段有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嫌疑。
但我不怕,我家底厚。
我花了重金,让城中最大的几个茶楼将姜元容过去做的那些下三滥的事儿全写了话本子,女主角的名字潦草地换了个“江远蓉”,又安排上最火的说书先生、戏班唱将来造势。
这些下九流只认钱,不认人,有钱就能使鬼推磨。
然而,这次好像失了效用。
茶楼管事客客气气退了我的银钱,只说对方给的数更多,不管我给多少,对方给三倍。
方应珣和姜元容没我钱多,我打着算盘合计了下,就算这俩人都加起来,在撒钱这方面也不能抗衡我年家。
帮姜元容的会是谁呢?
方家不喜她,姜家她没助力。
她夫家更是小官清流,若知道了这种事只会更理直气壮地休妻,绝不会砸钱。
我便只能在我的交际圈中,往上看一看。
给远在神都的好姐妹许如霜去了信,她只提了一个名字,李世镜。
尘封的记忆像狂风席卷而来,呼啸不已。
4
我同李世镜,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年家基业起于并州,十六那年,爹爹病重,我初掌年家,族中几位叔伯虎视眈眈,说我一女子掌不好偌大家业。
我不服,一路将铺子开到长安。
年家在并州也算富户,到了长安我才知山外有山。
杯盏不停,笙歌不息,灯火流星,当真是富贵迷人眼。
我想留在长安。
若我老实做个商贩,按时开门,迎客,送往,打烊,顶多是堪堪维持体面。
可我想要的太多了,我想要在长安扎根,要这万盏灯火里也有属于我的安身立命之处,我还想亲手抚一抚盛唐下的繁花似锦。
我拼命地研究门路,香料、布匹、酒楼、车马、奴仆……凡是年家能经营的营生,我用簪花小楷密密记了无数本账册。
半年后,从西域进来的密罗香一时名声大噪,一两香料抵一两黄金,我知道,我的门路来了。
我去佛前还愿,一身密罗香味在木质的檀香中张牙舞爪,李世镜便在此刻跪在我身侧的蒲团上。
他忽然靠近我:“娘子身上的密罗香花香气过重,若以青茶缓缓焙上几日,更合娘子气韵。”
说罢,他又递给我一张名帖,烫金宣纸,漆黑歙墨,铁画银钩绘着三个大字:李世镜。
我不着痕迹地在各大商行打听了这个名字,查无此人,便将这名帖塞到了角落里。
不过他的主意倒是提醒了我,密罗香花香怡人,清气中和,若以此为基调,加上不同辅料调和,想来又是大赚一笔。
我重金聘了位调香师,不出一月,我赚得盆满钵满。
曲江池畔,宴饮中场,我又见到了李世镜。
这次他不再是居士装扮,一席华服,琳琅满身,面上儒雅随和,映着粼粼江水的桃花眼笑意潋滟,倒让人失神一瞬。
这次,我主动同李世镜兜搭。
我想着,或许他能成为我在长安的人脉,很重要的人脉。
他贪图我美色也好,想要同我一起捞金也罢,价值交换,这是追名逐利的路上无可避免的事。
顶顶低的打算,跟这样顶级的富家公子周旋,最起码也能学学察言观色的分寸。
惊喜的是,他随意的一句指点,我的金库便越滚越多。
他并非不学无术的长安纨绔,相反,不论家世还是能力,他都能站在金字塔尖俯瞰芸芸众生。
我只待我的财神爷一日比一日用心。
5
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用心了呢?
或者说,是在我确认他的皇亲身份后,才不得不收了心。
天潢贵胄,怎能娶一位并州小城来的商家女。
我同许如霜因成衣铺子结识。
她是我店中的老客,一次闲聊中从掌柜那知道她喜欢的衣裙泰半出自我手,便下了帖子要见我。
户部尚书家的女儿,意外地同我投契。
我想着,她或许知道李世镜这个人,便隐晦地问了一句。
许如霜收起调笑的神色,端了茶饮了一口,眉目凝重:“你来往的人,叫李世镜?”
见我点头。
她神色怪异地打量我一番,岔开了话题,临别时她送我上马车,低低地提醒了一句:“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她怕我受伤,但也怕因此得罪李世镜。
金尊玉贵放在手心里长大,走到哪都是众星捧月的大小姐,竟然也有不敢惹的人。
许如霜知道李世镜这层关系后,有意抬举我,她带我熟悉长安贵女的交际,繁杂的礼仪,时兴的妆容,还让她的母亲收我为义女。
我明白,总有些许如霜的身份不合适做的事情,那由我来做便可,这也是一种交换。
但归根结底,总是为我抬身份,加筹码罢了。
我很是感激,但依旧选择同李世镜切断关系。
原因倒也简单,我在他身上学到的本事,够多了。
两年间,我的铺子涉及各行各业,用日进斗金形容我的赚钱速度,还是慢了许多。
可是,他不可能一辈子不成婚,我也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他。
能做李世镜妻子的人,绝不容许他身旁有我的存在。
就在我从并州收拢老宅回到长安的那一天,在李世镜为我接风的小宴上,我主动提出从今往后莫要再见面。
他低垂着头,修长精致的手认真把玩着琉璃盏,心绪不露分毫。
“为何?”他问。
“你会娶我吗?”
他定住动作,抬眸深深看了我一眼,却未再说话。
我们一言不发地吃了这顿饭,再也没交集。
对李世镜来说,我能做徒弟,能做情人,却独独不可能做他的妻子,做不了大唐皇室的夔王妃。
门当户对,齐大非偶,确实有几分道理。
可他,为何要帮姜元容,或者说,为何要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