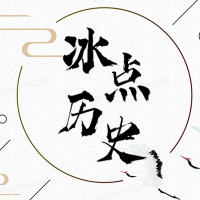在红军军史里,西路军的经历满是悲壮色彩,它宛如一个哀伤的 “符号”,饱含着诸多难以言说的复杂记忆。彼时,西路军被敌人围困,局势岌岌可危,几乎到了全军覆灭的边缘。而李先念带领的部队,同样深陷险境,随时都有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从自己的队伍中抽调出一个营的兵力,前去支援准备突围的程世才。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李先念为何会这样做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质朴而又坚定:“我们是同志”。

1937 年 1 月,酷寒肃杀的河西走廊,倪家营子内,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三十军陷入绝境。国民党西北 “剿匪” 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率数倍兵力将三十军团团围住。一路遭敌人围追堵截,三十军损失惨重,仅余 268 和 265 两个主力团,由代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指挥。
九昼夜的血战,倪家营子成了血与火的炼狱。屯庄围墙被炸成残垣,白匪和红军战士的尸体层层叠叠,鲜血在大地上蜿蜒。程世才的 268 团和李先念的 265 团,被七万多敌人隔开,敌人企图分割消灭红军。此时红军每团仅几百人,在敌人强攻之下,随时可能全军覆没。

生死关头,程世才接到李先念电话,得知西路军总部已令九军两个团分两路来援。268 团一面坚守,击退敌人一次次进攻,一面盼着援军。程世才站在寒风中的围墙上,紧盯总部方向,战士们也做好出击准备。夜里十点,枪声传来,战士们以为援军到了,可因敌人防御坚固、兵力悬殊,解围失败。
程世才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打电话给李先念决定突围。李先念表示派一个营接应,程世才担心 265 团本就艰难,再抽兵力更加危险。李先念却坚定回应,困难虽有,但 268 团情况更危急。程世才感动不已,声音颤抖。
很快,接应部队在敌后打响战斗。程世才握紧驳壳枪和手榴弹,大喊:“同志们,冲啊!为了胜利,为了生存,冲!” 战士们呐喊着冲出围子,一场壮烈的突围战就此展开......
李先念率部脱险2 月 27 日,西路军撤离倪家营子。后续的战斗更为激烈,但西路军将士没有退缩。红三十军和红九军战士带伤继续战斗,在三道柳沟、梨园口、马场滩、康隆寺等地与敌人厮杀,一次次击退敌人,掩护西路军总部转移到祁连山深处的石窝山。

部队到达石窝山时,兵力大减,加上伤员、妇女和孩子,总数不足三千人。曾经精神饱满的队伍,如今伤痕累累,但战士们眼神里透着不屈。3 月 14 日黄昏,石窝山上气氛压抑,陈昌浩主持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
会上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现有人员分成三个支队开展游击。李先念率 1500 余人组成左支队去西面大山;王树声带 700 余人组成右支队去南面大山;毕占云率部分兵力及伤员、妇女、儿童在当地转移。
石窝会议后,李先念知道责任重大。西越祁连山,既要面对恶劣环境,又要防备敌人追击。但他没有被困难吓倒,冷静分析局势后,带领西路军左支队向祁连山深处进发,寻找胜利的希望。

西路军成功脱险后,有人满怀好奇地问李先念:“先念同志,接下来你是打算去苏联,还是去延安呀?” 李先念不假思索,语气坚定地回应:“去延安!” 那时,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苏联的路程比去延安近不少,而且一路上的安全系数也要高得多。可李先念心意已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奔赴延安。
要是李先念当初选择了去苏联,他的人生或许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有几个西路军将领选择了前往苏联,却遭遇了不测,被暗中处决。即便李先念坚定地迈向了延安,命运对他依旧没有丝毫的偏袒。
回到延安后,他遭受了连降六级的处分,从原本高高在上的军政委,一下子被降为营教导员。许多西路军的干部战士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李先念自己又何尝不觉得委屈呢?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抱怨,他始终坚信,组织一定会将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因为他明白,自己投身革命的信念是正义的,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管它呢,就算把我降成普通士兵,我也要在红军里继续干下去!”

后来,毛泽东听闻了这件事,便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专门接见了李先念。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再次相见,李先念心中五味杂陈。
那是在 1935 年 6 月 15 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在一座天主教堂的东厢房里,李先念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而这一次,曾经被寄予厚望、“前途无量” 的战将,如今却被连降六级。毛泽东见到李先念后,第一句话便说道:“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
听到这句话,李先念的鼻子一酸,眼眶瞬间湿润,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一句话,对他来说,胜过千言万语。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公正评判,更是对两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深切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