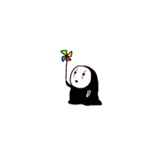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日常有记录文字的习惯。
一方面,整理数据可以帮助自己记忆;另一方面,总结成文字发布也更有利于成果的查找和阅读。
因此,我绝大多数的文字,强调的是方法学层面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
因为,从他身上,我看到了肺癌诊疗的真实轮廓。
虽然坎坷,但总有希望。

病例分享

影像描述:右肺上叶(227)见团片状高密度灶,周围见毛刺及血管集束征,径约2.5 cm×1.1 cm,胸膜牵拉。两肺散在磨玻璃灶,大者位于左肺上叶(215),径约1.9 cm;双肺多发透亮影及索条影,双侧胸膜增厚。两肺门区未见异常。所示气管支气管通畅。纵隔内未见异常增大的淋巴结。两胸腔无积流征象。
这是一名61岁男性,在2021.9检查时发现右上肺肿物,病灶呈实性、合并毛刺、胸膜牵拉、血管穿行表现,考虑肺癌。
病灶最大径2.5 cm,检查未见其他转移病灶,纵隔淋巴结也比较干净,cT1cN0M0 IA3期。
虽然年龄不大,却合并糖尿病、冠心病、COPD;肺功能尤其差,恐怕耐受不了手术。
于是,在2021.9.17,在CT引导下行经皮肺病灶热消融术,为防止反复穿刺造成气胸等不良影响,未行穿刺活检。
从下面三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消融后的肺部改变。
在2021.9.18这张CT中,我们可以看到胸膜皱缩改变(绿色箭头),然后病灶的实性区域明显比治疗前的更大,说明穿刺、消融给肺部带来了明显的创伤,实变的背后可能是淤血,可能是炎症,也可能两者都有。

在2021.10.21这张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消融后一个月,肺部实变区域较前缩小,说明局部的炎症在吸收和消退。与此同时,肺部病灶内部出现明显的空腔(绿色箭头),说明热消融治疗确实洞穿了肿瘤区域,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而在2022.6.15,也就是消融后9个月,可以看到原先的空洞已经消失,肺部病灶挛缩成一个类似三角的长条形改变,并有长毛刺牵拉胸膜,这是炎症病灶的典型影像特点。

后续,患者继续随访,各方面情况稳定。
但是,在2024年1月,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胸痛、胸闷改变,完善CT检查,发现肺部病灶较前明显增大,呈浑圆改变,并重新出现细毛刺等恶性征象。

与此同时,出现心包积液:
如下图所示,红色箭头是心脏边缘,而黄色箭头是心包膜,蓝色箭头就是充满在心脏和心包之间的心包积液。

于是,引流心包积液,送检细胞学回报肺腺癌,送检基因检测回报KRAS G12C突变。


为了控制心包积液,予以心包引流,同时,于2024.2予以心包灌注化疗,方案是卡铂+贝伐单抗。
2024.2.8,卡铂300mg+贝伐单抗200mg;
2024.2.12,卡铂250mg+贝伐单抗100mg。
在控制全身疾病方面,患者因为身体情况较差,没有选择KRAS突变患者常用的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方案,而是使用了最新的靶向治疗。
从2024.2.13开始,患者开始口服索托拉西布(Sotorasib)(960mg/天),一种针对KRAS G12C突变设计的靶向药。
并在2024.3.1、2024.4.16及2024.7.22复查,发现病灶稳定,持续至今。


一些思考
今天,之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病例,是因为一路以来,他的诊疗过程,正是反映了现阶段肺癌治疗的大抵轮廓,即:尽管坎坷,但总有希望。
首先,是心肺功能不佳,排除在手术指征之外。
但是,接受了妥协性射频消融。
随后,是病情进展,出现KRAS G12C突变。
尽管不能耐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但仍然有索托拉西布(AMG510)在等着他。
一路过来,磕磕绊绊,也已经3年有余,目前情况良好,心包积液消失、肺部病灶稳定。
其实,看着这个患友,让我想起之前自己接诊的一位病友。
老林82岁了,和其他老年人一样,有不少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但是,说话中气仍然比较足,爬楼梯一次可以上3楼。
2018.11,他家人带他来找我,因为肺里长了个肿瘤。可我惊讶地发现,这个病变从2017.7开始就有了,只不过一直没有处理。
2017.7,胸部CT已经看到右上肺的病变了,那时候大小17×15mm,没有处理。
2018.6,复查CT,提示病灶增大,大小为45×34mm,还是没有处理。
而到了2018.11复查CT,提示病灶已经进一步扩大为50×34mm。


这是纵隔窗的比较,在2017.7到2018.6期间,肺部病灶增大,而纵隔淋巴结并无显著差异;在2018.6到2018.11期间,伴随着肺部病灶的增大,出现了多发、多站的纵隔淋巴结肿大。
说明什么?除了肿瘤本身在进展,纵隔淋巴结也出现转移了!
2017.7,临床分期 cT1bN0M0 IA2期
2018.6,临床分期 cT2bN0M0 IIA期
2018.11,临床分期 cT2bN2M0 IIIA期
我很好奇这种对肿瘤进行放养的决策背后的原因,因为在我看来,其家庭经济条件还不错,子女非常孝顺,这种处置方案很不合理。
在与其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是当地观念认为:“超过70岁就不需要进行积极的治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超过70岁的肺癌就别治了,顺其自然最好?》关于这点,我在这篇文章中早就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但毫无疑问,伴发多站纵隔淋巴结转移的老林,已经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写在最后

多年临床工作中,见过不少患者,一诊断肺癌,就放弃治疗,我在尊重患者乃至家属意愿的前提下,也只能自觉可惜。
没错,肺癌诊疗这条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即便早期如原位/微浸润的患友,他们在获得病理治愈的同时,也要警惕未来第二原发癌的高风险。
清华北大尚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群体了。
但,尽管前路漫漫,肺癌总有希望。
我是2010年进入胸外科读研究生,读研之前,放疗、化疗、手术,是肺癌缩仰仗的三驾马车。
那时候的肺癌,效果是真差呀。
再看看今天,在手术赛道,微创手术日益成熟、机器人辅助也应运而生。
微创的同时,还有精准,得了肺癌不用全切肺叶了,对付早早癌,部分切除也是OK的,效果和肺叶切除相当。
而在放疗赛道,日益成熟的放疗技术,有了更多的迭代,三维体力定向放疗技术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准的杀伤肿瘤细胞,而重离子放疗技术则可以更好地降低放疗的毒副作用。
消融技术也在传统热消融基础上、出现了电消融、冷消融等不同派系,适用不同应用场景。
靶向治疗的出现,更是让治疗选择冰彩纷呈,基因观点的引入让我们可以再更加微观的层面探索肺癌,分析他们发生发展乃至耐药的规律。
即便针对同一个靶点,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打个比方,前文提到的KRAS G12C突变中,2023年在柳叶刀曾经发表了Code BreaK200研究,发现在二线患者中,索托拉西布(Sotorasib)可以实现比传统化疗更好的效果,实现5.6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

但在今年刚发表的<胸部肿瘤杂志>就首次证明,另一个针对KRAS G12C的靶向抑制药物IBI351,可以在二线患者中,实现9.7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
就连KRAS G12C的竞争都如此激烈,那就更不用提EGFR、ALK这样的成熟赛道了。
免疫治疗的出现,则为那些无法接受有效靶向治疗的患者,进一步带去希望。
现在,在免疫治疗,我们不再需要像过去一样,只能仰望国外的洋产品,即便面对诸如帕博利珠单抗这样的顶级单品,国产的PD-1抑制剂一样可以用数据证明自己的疗效可靠,不输过它。
抗癌药的纠结,一场无声的硝烟,选国产还是进口?
而与此同时,新药开发还在继续、新方案的探索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不能成药的TP53,现在也可以被结合上了。
KRAS G12D的靶向药,也已经在路上了。
……
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
我进入胸外科领域、学习开展肺癌诊疗,已经有十几年。
我感觉,这些年的时光,我就像一个跑者一样,一路爬坡。
在早些日子,或许由于太阳没出来、或许由于角度不对,山路确实崎岖难行,困难重重。
但现在,这条路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阳光照进来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会有更多。
所以,我常常说,我们确实要相信临床研究的结果,但千万不要用这些数据限制自己。我们肯定活得比他们更长久。
为什么?
因为,临床试验,从开展到入组到随访结束发表最终生存结局,一不留神,5年就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漂亮的数据,其实只是5年前就跑出来的结果。
而我们自己,用着已经不断研发出来的新药、新方法,享受着种种胜利的果实,一定可以实现比过去更加辉煌的成绩。
肺癌治疗的太阳已经冉冉升起。而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向阳而生,踏光而行。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心若有所向往,何俱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