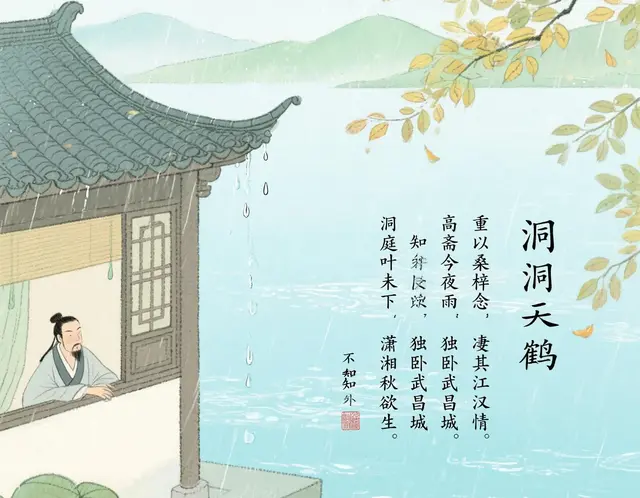作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钱币之一,得壹元宝以其诡谲的铸造背景、精湛的工艺水准与极端的存世稀缺性,成为安史之乱时期特殊金融政策的实物见证。这枚直径约3.6厘米、重达16克的青铜钱币,诞生于唐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割据洛阳的特殊历史节点,既是藩镇势力挑战中央货币体系的铁证,也因“旋铸旋毁”的命运,在当代收藏界享有“古泉五十名珍”的盛誉。本文将从历史经纬、铸造技艺、文化隐喻及市场表现等维度,解读这枚承载着战争密码的货币遗珍。
一、历史背景:河朔铁骑的金融突围安禄山起兵反唐的第四年(758年),其部将史思明在范阳再度叛变,次年攻占洛阳,自立“大圣周王”。为筹措军费、彰显政权合法性,史思明于乾元二年(759年)废止唐廷发行的乾元重宝,改铸“得壹元宝”。其命名暗含《道德经》“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的深意,既隐喻“首义”正当性,又寄托“天下归一”的政治野心。
据《河洛遗编》记载,得壹元宝初铸时规定“每千文兑绢十匹”,强制与实物挂钩以稳定币值。但军事形势的恶化迫使史思明次年改铸“顺天元宝”,并大规模回收熔毁得壹钱。这种“旋铸旋废”的政策,导致得壹元宝实际流通不足一年,后世估算总铸量不超过10万枚,历经千年损耗,如今存世真品不足百枚。
 二、铸造工艺:战火淬炼的技术巅峰
二、铸造工艺:战火淬炼的技术巅峰得壹元宝虽为割据政权所铸,其制作工艺却达到唐代铸币的巅峰水准,其技术特征深刻体现军事政权对货币信用的极致追求:
材质管控:采用“铜七锡二铅一”的高铜合金配方,钱体呈青白色泽,经光谱检测铜含量达69.8%,超过开元通宝的62%。部分试样钱含微量银元素(0.3%),推测为防范私铸的特殊防伪手段。雕模技艺:钱文由幕僚梁悦然以魏碑体书写,“得壹元宝”四字雄浑峻拔,“寳”字“貝”部作开口状,暗喻“广纳天下财富”;背月纹采用“单刀直刻”技法,锋芒凌厉如剑戟。钱郭采用“三圈九层”精修工艺,外轮宽达1.2毫米,地章平整如镜,铸造时需五次修模方能成型。版式特征:早期试样钱直径可达37毫米,重18克,字口深度达0.5毫米;后期减重钱缩至35毫米,重14克,出现“得”字双人旁断笔现象。背纹分“上月”“下月”“双月”三大体系,其中背四月纹者传为祭祀天地所铸,存世仅3枚。洛阳考古发现的铸钱遗址显示,得壹钱范采用“阴文反刻”技术,每范仅铸钱两枚,这种低效工艺虽保障了质量,却难以为继大规模战争消耗。
三、文化隐喻:非正统政权的符号建构得壹元宝的设计暗藏多重政治密码,堪称古代僭主货币美学的典范:
文字游戏:钱文“得壹”既可解读为“首得天命”,又与“得一”谐音,呼应《周易·系辞》“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的哲学命题。纹饰政治:背月纹并非简单装饰,据《洛阳兵燹录》载,史思明令工匠“以戟尖刻月”,象征“弯弓逐日”,即推翻李唐“日纹钱”(开元通宝背月)的政权隐喻。短命钱谶:民间迅速流传“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谶语,既暗示得壹钱将成绝响,又暗讽史氏政权“得壹而终”的命运,这种舆论反噬加速了钱币的废止。 四、收藏市场:千年遗珍的价值神话
四、收藏市场:千年遗珍的价值神话在近二十年全球钱币拍卖市场中,得壹元宝始终占据唐钱板块的至尊地位,其市场规律呈现三大特征:
存世分级:普通版美品存世约40枚,背单月纹者25枚,双月纹不足10枚,背四月纹为孤品级存在。直径超过36毫米的初铸试样钱,目前仅见日本东京货币博物馆藏1枚。价格体系:2011年嘉德春拍,一枚背单月纹得壹元宝以89.7万元成交,创当时唐钱纪录;2020年北京保利秋拍,背双月纹极美品以287万元落槌,每克单价达2.05万元;2017年德国昆克拍卖行出现直径37.1毫米的试样钱,虽经修补仍以52万欧元成交。鉴定门槛:因存世量少,真品均经数百年藏家递传,新出土品几乎绝迹。PCGS评级入盒者仅6枚,其中最高分AU58分者估值超400万元;市场常见仿品分“清末翻铸”“民国改刻”“现代电火花”三类,高级仿品价格甚至超过普通开元通宝真品。据行业分析,顶级品相得壹元宝近五年年均增值率达25%-30%,其文化稀缺性远超材质价值,未来仍将保持“藏一件少一件”的升值惯性。
五、结语得壹元宝如同一枚穿越时空的烽火令箭,既凝固了河朔铁骑冲击大唐金融体系的瞬间,也见证了古代军事政权在货币信用建构上的天才与局限。在收藏领域,它不仅是检验藏家眼力的试金石,更是研究唐代地方铸币工艺的活化石。当这枚泛着青冷幽光的钱币置于放大镜下,那些凌厉的笔划、精密的花纹,都在诉说着一个悖论:最完美的技术杰作,往往诞生于最混乱的历史时期。或许正是这种毁灭与创造的交织,让得壹元宝超越了货币的实用范畴,成为承载人类政治欲望与艺术追求的永恒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