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贱”按其属性可分为官有贱民和私有贱民。官有贱民包括陵户、官户和公奴掉。私有贱民包括家人和私奴裨。“五色贱”虽同属于“贱”身份但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也不是完全等同的,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复杂的身份差异。

在《养老律令》中,关于“五色贱”的规定占有不小的比例,其中陵户所占的比例最小,奴婢所占比例最大。
根据神野清一的统计,在日本律令条文中,有关贱民的令条文有58 条,律条文有 48 条(包括逸文),共 106 条。这106条分布的范围很广。
 陵户的含义
陵户的含义陵户是“五色贱”中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附属于中央官僚机构诸陵司后改为诸陵寮。律令制下的陵户与杂户具有共同特点即都可以单独立户但又和普通百姓在制作户籍时总共只需制作三份不同必须制定四份。
同时陵户同杂户都可以免除课役。并且当陵户人数不够时还会挑选良民充任以十年为交替为天皇及其皇族守卫陵墓。前已述及笔者赞同陵户沦为贱民是在《养老律令》颁布以后这一观点。

在大化改新之前日本存在着职业与陵户相类似的墓守、陵守等“陵户”这一名称是从唐朝中国传入日本的。那么日本何时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呢陵户被划归为贱民的原因又是什么?
陵户和贱民的关系有关“陵户”这一名称,在现存史料中,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显宗纪元年(458年)五月条中。但是,此条史料中提到的“陵户”与日本律令制下的“陵户”(ryouko)涵义不同。
泷川政次郎曾指出,上文出现的“陵户”以及“籍帐”等名称,都应当理解为,是用后世的名称来代指前代的事物。

在中国的“陵户”这一名称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存在着“墓守”、“陵守”等名称。慕守、陵守的职业与陵户的职业相类似。显宗天皇纪记事中的“陵户”指的便是充当守墓,兼守山,隶属于山部连的墓守或陵守。
根据仁德天皇纪六十年(373年)冬十月条记载。"在皇极天皇纪元年(642年)是岁条中亦有相关记载:“又尽发举国之民,并百八十部曲,预造双墓于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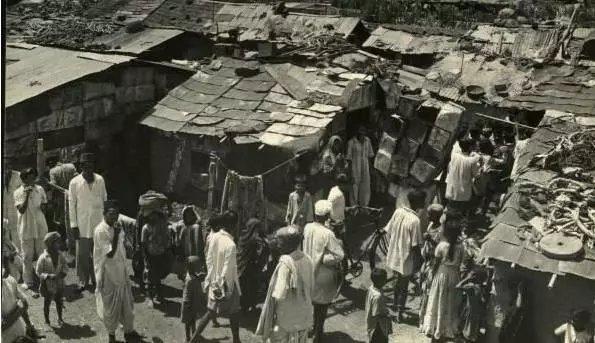
一曰大陵,为大臣慕,一曰小陵,为入鹿臣墓。望死之后勿使劳人,更悉聚上宫乳部之民。”"总之,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前出现的“陵户”并非律令制下的“陵户”,而是“慕守”或“陵守”等。“陵户”并非律令制下的“陵户”而是“墓守”或“陵守”等。
在这一过程中也汲取许多中国的法律术语而唐代的“陵户”这一名称也便是在此后不久传入了日本。在孝德天皇纪大化二年年三月甲申条中有记载。该段史料说明,当时日本可能已经开始参酌唐代的制度,加强了对日本的陵墓的管制。

但对日本此时是否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还不能下明确的结论。在律令制下,关于“陵户”一词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持统五年(691年)十月乙巳条:“诏曰,凡先皇陵户者置五户以上。
自余王等有功者置三户。若陵户不足,以百姓充。免其徭役。三年一替。”神野清一认为日本律令中首次使用“陵户”这一名称是在《养老律令》中,在《净御原令》与《大宝律令》中不存在“陵户”一词。

认为上述史料中的“陵户”是后世之人润色的结果,实际上指的还是“陵守”或“墓守”。笔者以为,持统五年的史料并非“后世之人润色”的结果。一般认为,该诏以《净御原令》丧葬令为前提。
陵户的特性《净御原令》是在参照唐代《永徽令》的基础上编篡成的。该诏作为律令国家形成时期的一条重要史料,十分清楚的说明了律令制下陵户的特性。
即第一、天皇的陵慕的配置以陵户“五户”作为一个基准单位,皇族功臣陵墓的守陵人的配置则以陵户“三户”作为一个基准单位;第二、陵户的数量是很有限的,当时存在陵户不足的情况;第三、为了弥补陵户的不足,常以“百姓”来补充;

第四、作为陵户不足的补充者,“百姓”可免徭役,且三年一更替。如前所述,早在大化二年(646年),日本已经开始参酌唐代的制度,加强了对日本的陵慕的管制,日本此时可能已经接触到“陵户”这一名称。
第五、在此后律令制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陵户”这一名称无疑传入了日本。在制定《净御原令》时(681 年),对陵户的特性已经做了十分清楚的说明,与律令制之前的慕守或陵守等有所区别。
第六、但必须承认,此时“陵户”并没有完全取代“墓守”与“陵守”等名称,而是存在“陵户”与“墓守”、“陵守”相混用的情况。即一部分人可能仍然使用日本所固有的名称“墓守”、“陵守”等。

第七、另一部分人则开始使用从唐朝传入的名称“陵户”。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日本当时向中国唐朝学习的必然结果。
关于日本律令制国家陵户沦为贱民的原因,日本史学界大致有以下三种看法。以唐代良贱制为样板;对死秽的忌讳;陵户是不负担课役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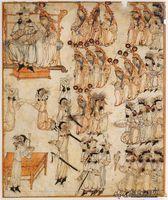
如果对唐代陵户的变化加以考虑,日本律令制下陵户身份变化与唐代陵户身份的变化正好相反,这一点很耐人寻味。养老二年(718年)修订而成的《养老令》中首次将陵户视为贱身份之一,这一年是唐朝开元六年(718年)。
在唐朝开元十七年(729年)以前,唐代的陵户是贱民,但是在开元十七年(729年)十一月,唐玄宗在五帝陵举行亲谒仪。下达大赦令,陵户才放贱从良。

日本的陵户制模仿了唐朝的陵户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将日本的陵户被划归为贱民的原因归结于仿照唐代的结果这一说法存在难以解释的地方。
如上所述,日本最迟在制定《净御原令》时(681年)已经开始使用“陵户”这一名称,而陵户被划归为贱民则是在养老二年(718年)《养老律令》颁布之后。唐代的陵户在开元十七年(729 年)十一月,唐玄宗在五帝陵举行亲谒仪,下达大赦令之前是贱民。

也就是说,唐代的陵户制度在传入日本的时候,陵户属于贱民,如果日本以唐代陵户制度为样板,日本的陵户也应当属于贱民。而此时日本的陵户却是良民,直到《养老律令》中才被确定为贱民,这是为什么呢?
陵户成为贱民的缘由古代中日两国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贱民制到唐代已经经过长期发展并走向成熟,而日本的贱民制则是在大化改新后模仿唐代贱民制的基础上建立的。
日本在模仿唐代贱民制时未必完全同唐代一样,而是在模仿中进行了变通,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杂户在唐代是贱民,但在日本却是良民。因此,不能将陵户被划归为贱民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对唐代的模仿。

由于对死秽的忌讳而将陵户划归为贱民的说法在日本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泷川政次郎指出陵户沦为贱民与它的职业是丧葬、陵墓有关。
他认为,伴随着日本与大陆、朝鲜半岛的频繁交往,嫌弃死尸、忌惮陵墓的死秽思想传入日本,并且在日本十分盛行,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从事丧葬、守墓的陵户必然遭到社会的嫌弃、排斥、贱视。"
升井正元也认为陵户被划归为贱民与当时将坟慕守卫民视为卑贱的趋势日益增强有关。但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这一说法。神野清一认为将慕地视为“秽地”的观念在奈良时代初期尚未产生。

墓地在当时作为“圣所”是拒绝俗界之秽的地方。八世纪末的贱民,只是统治阶级通过观念上的罪秽或者是宗教的思想将其与不净相联结。
贱民虽被贱视,但尚不是社会的一般看法,与死秽之间的联结还未显现化。笔者以为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即陵户沦为贱民与当时人们对死秽的忌讳是不无关系的,因为对死秽的忌讳是所有民族所共通的感情与观念。

但是,只将这种一般性的感情作为理由,不能解决为何只有律令制下的日本将陵户视为贱身份这一问题的。笔者以为,陵户从良民被划归为贱民,有着更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首先提出陵户被划归为贱民的原因在于贱民不负担课役的是升井正元。神野清一对升井正元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在律令制下,杂户、品部等杂色人"同样也不负担课役。

据此,神野清一认为升井正元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何同样是不负担课役之民,杂户、品部没有被视为贱身份,而唯独陵户被视为贱身份这一问题。
在日本律令制国家“公地公民”制下,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课役是国家财政的基础。作为公民身份的标志之一便是必须从事从业生产,负担课役,不负担课役就意味着得不到国家的承认。
在律令制下,公民与良民是不同的。公民主要是指在国有土地即“公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主要包括百官人以下,除奴婢、杂色人、寺社的封户之外的社会成员;良民则指除天皇与贱民之外,包括了百官人以上、公民、以及杂色人、寺社的封户民等。

杂户和品部既不属于贱民阶层,同时也不属于公民阶层。这主要是因为杂户和品部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不必负担课役。
不过,杂户、品部虽然同陵户一样,都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由于品部、杂户主要从事官司的劳役,担负着供给官司特殊物质的重担,是有特殊技能的手工艺人,因而仍然被保留在“良人共同体”成为其中的一员。
而陵户则从事守护陵墓这一被视为污秽的低下职业,进而被排除出“良人共同体”,被排除出社会秩序之外,成为“五色贱”之一。
 总结
总结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往往对人民采取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策略。陵户被划归为贱民共经历了两个步骤。即陵户首先由于不用负担课役,因而将其与必须负担课役的公民区别对待,其次由于当时人们对死秽的忌讳,因而进一步将其与同样不必负担课役的杂色人区别对待,从而陵户逐渐从“良民”被划归为“贱民”。
参考文献神野清一:《律令国家と賎民》,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年
【日本】滨口重国:《唐の陵、墓戸の良賎にっいて》,《史学雜誌》43-8,1932年
【日本】升井正元:《陵戸制成立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流》21,198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