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一次,我们很可能在经历气候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夏天:
也许你清晨从贵州镇远的民宿标间里醒来,发现窗外河水已经漫到三楼,连沙发也漂浮起来;也许在你山东东明6楼的家中,忽然天色骤暗来了一阵龙卷风,把厨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许你去了川西跟团游,结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变成极限逃生……
官方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勾勒着灾难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来,国家多次向灾区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并调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前线。7月4日,中国气象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正在趋多趋强。7月14日,水利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流域连续发生20次编号洪水;预计“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发生洪水。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大家开始感到无力和疲惫,这会让人们把头转向一边。”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说。
“今年上半年确实重了一些,是我们做气象灾害这十年里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说。
“今年整个基金会的募款项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了,(只有)三位数。”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说。
在这个大江大河洪水并发、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凤凰网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环保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

一向快人快语的王刚,此刻就像“像素游戏”里的小人回到现实世界,吐词磕磕绊绊,语速极慢。
王刚是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接通凤凰网电话时,他刚结束在湖南华容洞庭湖决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后,王刚已经头脑发昏,记不清行动路线。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时间和地点。对讲机中队友同样浑浊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滥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状态。6月17日起,救援队一连参与了7场水灾救援: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乐平、永修,湖南平江、华容。最多时有113名曙光队员顶在前线。

◎ 2024年6月26日,曙光救援在江西浯口镇救灾
最难的一天是7月2号,王刚用“全线告急”这样的词语形容彼时——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不得不发出“家书”,号召当地人回乡抗洪;洪水倒灌进入湖南平江,淹没了近一半县城;湖南汨罗更是出现了约30米的溃堤(那时距洞庭湖溃堤还有3天),当地人不得已将装满石头的卡车驶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点50分,正在高速公路庐山服务区休息的队伍收到求援消息,紧急会议后,他们决定兵分两路:2车4艇继续前往江西永修县;主力团队30人10车12艇携带水陆两栖车连夜赶往湖南平江和汨罗地区;此外还调动了山东的志愿者。
如果熟悉好莱坞的灾难电影,你会知道难题总是接踵而至。现实也是如此。对于王刚来说,更麻烦的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季还没到来,钱却快花完了——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动资金支出超过40万,而这个民间救援团体全年的备灾资金也就50万。
到处都是钱窟窿——补充救援装备,队员训练经费,日常开支,救灾行动。为了省钱,一个月前,队伍从厦门出发时自备了50箱面包、21箱自热米饭和50张行军床;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们只开三四间酒店房间供四五十名队员轮流洗澡;休息时,女队员住酒店,男队员搭帐篷住行军床。去年一年,厦门曙光积攒的矿泉水瓶和纸箱卖了3321块钱。

◎ 救援人员在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决堤救灾现场
7月13号零点18分,王刚和队友终于回到厦门。与此同时,重庆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发出“特大暴雨”预警,部分区县救灾指挥部开始引导居民转移避险。一天后,河南省南阳社旗县出现了“超级暴雨”,三天降下了当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个月这里还处于极度干旱中——重旱瞬间急转成了重涝,一夜之间,当地人努力浇了三轮水才抢救过来的玉米苗,被彻底淹死了。
16日,王刚一边休整,一边在朋友圈开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灾的求助登记表。

“今年的气象灾害比较频繁,发生时间也比较早,已经有好几个国家三级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了。”爱德基金会社区发展与灾害管理团队主任谭花说。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 2024年7月2日,江西永修县,车主在抛锚的汽车中求助
可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对话氛围立刻变得谨慎。
一则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舆论事件是,7月5日,企业霸王茶姬向湖南华容县捐赠500万元,却引来反对质疑声。有人问,这些善款真的能帮到灾民吗?还有网友评论,灾难频发后,人们对苦难麻木了,“现在社会缺少联结感及共通感,大家都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之下……对遥远的他人有着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灾时,老百姓对救援队伍很尊敬,是吧?”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他是国内最早做急流、舟艇、绳索、冰面等综合救援技术培训的人士之一,“以前我们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围是)这又不关我事,我凭什么支援?”
2018年寿光水灾时,800*800平米的仓库几乎装满了各地驰援的物资。而今年,据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观察,“各个基金会的捐赠都挺惨淡的”(谭花形容,是“断崖式的下降”)。不仅如此,“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灾害事件,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大量的捐赠”。
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应急救援项目部负责人王涵介绍,今年基金会收到的公众捐款占比80%-90%,其余是企业捐款——称得上“寥寥无几”,而在过去两年,企业捐款平均占比总筹集善款的20%左右。“我们往年合作的一些企业今年甚至都婉拒了。”截至7月15日,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南方水灾项目筹款45万,而去年京津冀水灾项目时,它筹得了700多万。
谭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灾和京津冀水灾的募集款项达到“几千万”,今年的南方水灾目前只募到“几百万”。
往年,矿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紧缺物资——灾害发生一两天后,应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了,基金会采购时务必谨慎,不然就会过剩。今年却有不同:“好几个地方提出来的需求是应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谭花在爱德基金会工作了20年,这让她感到意外。

◎ 方便面是救灾时重要的应急战略物资
应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灾后所需的水枪(用于冲扫淤泥)、发电机、雨鞋、铁锹、手推车、电动三轮车、消毒药具、水泥等等了——即便是社会援助充分的年份,这些灾区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关注到。
变化势必影响救灾救援工作。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共支持100多支民间救援队,并和30多家社会组织长期合作。“如果没有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救援行动,大规模灾害的救灾有运营成本。如果没有快速的筹款能力,资金怎么能到一线也是一个问题。”王涵说,他刚从湖南救灾前线回到北京。他们今年响应了广东韶关和梅州、广西桂林、湖南华容和汨罗、河南南阳、重庆的救灾与救援。
谭花所在的爱德基金会的情况是,“哪里发生灾害还是会响应,但是响应规模明显比较小。用有限的资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据郝南观察统计,近几年达到需要公众募捐程度的水灾大约是每年20次,而真正引起全国范围内踊跃援助的水灾只有2021年“7·20”河南暴雨和去年的京津冀水灾。甚至,有的灾情信息都没能走出当地——今年6月,黑龙江倭肯河、广西崇左和百色都发生了严重水灾,都没能在舆论场留下什么痕迹。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灾中,华容县因为洞庭湖决堤多次登上热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上平江县的灾情远超华容县——郝南估算,平江、汨罗救灾需求折算成货币价值的话,大概是华容的十几倍。

◎ 2024年7月2日,湖南平江县,救援队运送被困民众
目前国内缺少对水灾严重情况的定级,类似地震震级——“这能让公众更容易理解灾情到底有多严重。”郝南说。
现实之二是,社会捐助却和公众关注度成正比。这意味着,灾情严重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被“看见”,从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今年6月中旬,广东梅州和福建龙岩水灾时,当地通讯中断,消息传不出来,“一开始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过了大约两天,我们才发现还有很多村庄在失联中。”谭花说。郝南提到,广东梅州、福建龙岩受灾之深之广,其所需的救灾赈济资源是平江的好多倍——平远、蕉岭、武平、上杭,这四个重灾县的受灾程度都比平江要严重。
灾情聚焦,这看起来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话题——比起事后才能被量化的灾害,它更取决于在受灾第一现场,是否有可以几何倍扩散的新闻点出现。“郑州地铁的情况出来之后,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当时还有一个在线求助文档,每个求助信息都很紧急,大家就意识到原来水灾特别严重。”谭花说。

◎ 2021年7月27日,郑州沙口路地铁口纪念遇难者的鲜花
但这远不止一个传播问题。受访者们试图梳理“灾情失焦”背后的原因:经济环境、企业效益、灾害麻木、信任危机……又都默契地点到为止。
郝南强调道,捐赠遇冷不是今年的偶发现象——2015、16年之后,公众对灾害捐赠的意愿就下降了。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来辞去牙医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义援助中。
郝南的语速不快,善于掌握谈话的主导权。在这个极端灾害日渐频发、而大众捐助愈加疲软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说的气势反问道:“公益组织要先做到,有没有说清楚捐赠的必要性?公众有那么多的质疑,有没有人回应、解释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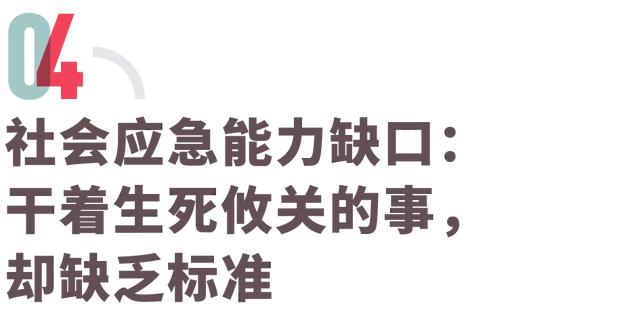
早年间,谭花和同事向企业、资助人寻求资金支持民间救援队,总是吃到闭门羹——人们更希望善款直接用在灾区百姓的身上。当时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不断提升,也更倾向于独立完成救援工作。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于地区缺乏应急响应机制,有的地方甚至连备灾的救援艇都不够用。谭花说,民间救援队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和态度发生了转变。
今年的情况更不一样了。“灾害发生那么多,大家都有点顾不过来了,希望能够有社会力量帮助他们。”谭花说。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镇人民政府在官微上号召“全镇父老乡亲和在外奋斗的乡亲们”,“立即集结、迅速行动”,投入抗洪抢险中。
某种意义上,极端天气的高发,推动了民间救援的发展。“(民间)水域救援是从2016、17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原因是水灾越来越多。”郝南说,河南水灾后,民间救援队的数量翻番,从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队伍几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鲜有地震、山地领域的队伍。
“民间救援队的优势是灵活机动,信息来源也更迅速。”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河南水灾时,他的队伍到了新乡牧野区寺庄顶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从一间厂房里游出来。一番询问,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离此地三公里外的村子已经被洪水围困了好几天,信号中断,外部无人知晓。救援队赶到后,看到房顶上站满了村民,他们拿棍子敲击铝盆,喊着救人。队员们花了两天时间才将村里数千人顺利转移。

◎ 2021年7月24日,河南新乡牧野区,被淹没的房屋
但是,极端天气带来更加频发的多种灾难,我们成长中的民间救援队真的足以应对吗?
郝南对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来,培养一个专业合格的救援人员需要3-5年。“我估计现在干救援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做救援的基本素质,”他毫不含蓄地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不少队伍和个人确实很积极,但是他完全不具备救援的能力,他就不应该出现在现场。”
“这么多队伍干着生死攸关的事情,却没有操作的标准,没有技能的标准,也没有现场指挥协调的标准。”他继续说,这会危及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的生命安全。
一些队伍练了很久的技能,但并不知道这些技能在灾害现场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郝南说。气象灾害救援的时机非常重要,“怎么在水涨之前赶到现场”——“你不能等到水退了才去救人,这不成作秀了吗?”
圈子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冒进的英雄主义。“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线就会去,这叫有组织无纪律,那不就乱成一片了吗?”李延照说。近些年,无论是训练还是救援现场,都发生过民间救援队员遇难事故。
与凤凰网通话那天,山东东明出现了强对流龙卷风,风力掀翻了板房的房顶,造成5死83伤。如果是十年前,李延照听说有险情,一定立刻带队出发。如今的他知道,等他做好准备带队从青岛奔赴500公里抵达东明,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谁距离近谁优先,谁能力大谁优先。”李延照说,如果没有相应能力,就要给专业的救援队让路,“不然社会应急力量会被诟病”。
这不完全是技术和态度问题,也跟资金有关。“兜里没钱,他怎么提升装备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没钱,越想干点活引起别人的注意。干活越多,危险越多,伤亡越大。”李延照总结。
民间救援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基金会、企业和公众,不同队伍的情况大有不同。李延照队伍的资金来源包括10%的政府支持、3-5%的社会捐赠,剩下的缺口靠他每年在全国做六七百场救援培训等补齐。一年几百场培训做下来大概有200来万。

◎ 李延照在救援培训中
此外,政府也会购买社会应急力量的服务。服务期通常为一年,民间救援队负责相应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突发事件、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等任务。尽管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过《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但政策落地情况地域差异。李延照观察,北京、深圳的政策落地最好,“有的地方是抵触的”。
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做保障,资源注定会分配不均。就像救灾时,越靠近路边的灾民得到的物资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岛”越得不到帮助——民间救援队同样旱涝不均。“没资源的,仰着脑袋只能看天。”
尽管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李延照还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们从事这个事的时候,你别看他累成什么样,但他是享受的。”

过去几年里,周楚涵所在的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一直努力让公众理解,极端天气出现的背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大背景:气候变化。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包括高温和强降水。”周楚涵说,这意味着过去没有处理过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和人群需要应对灾害;即便有过应灾经验,很可能应付不了新的灾害强度了。
现实却是,大多数民众,就连一些救援人员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和气候危机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当时觉得吃惊,”周楚涵说,“又可以理解,他们觉得救援是一项技能,背后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当你对(气候变化)趋势有所了解,会做出预判指导救援工作。”
绿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导预防灾害的重要性。“把资金投入到(灾害)事件发生之前,投入到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响应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事后再去救济、修复,卷入到恶性的循环中,那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周楚涵说。
这在业内已是共识。湖南洞庭湖救援抢险时,郝南在线上跟了全程。他认为当地的应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时,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在傍晚6点30就开到即将发生溃坝的村子,村民也有应灾经验,配合有序。准备到位的快速反应,“减少了救援的工作量,也减少了人员伤亡”。

◎ 2024年7月7日,湖南岳阳,卡车正排队堵住决口
“预防(灾害)具体要做什么?是要真正的减少伤亡,”郝南说,“这不是靠救援队,是靠一整套预警监测逃生演练体系。”
然而,基金会筹到的用于防灾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将善款实实在在地送到灾民手里。
“我们都知道防灾、减灾比单纯救灾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钱能用到这上面,”谭花说,“大家更关心救灾工作有没有做到位,东西有没有发到老百姓的手上。”
灾害总是和无情、肆虐相关,但救援现场最不缺的是人们的互相守望。梅州龙岩水灾时,政府部门投入几架直升机运输物资、转运人员,可一些“孤岛”村落并不具备起降条件。一开始,是周边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时给孤岛里的老人们送吃的。志愿者们听说后,每人每天背着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资,像蚂蚁搬家一样人力运输。
“这就是社会力量,”郝南说,“当灾后的需求和刚性的投入之间存在缺口时,这部分社会的韧性补上了。”
在许多救援人的心里,绕不开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情结——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说,那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志愿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区支援。

◎ 汶川地震发生的2008年,成为中国志愿者元年
那年也是谭花加入爱德基金会的第四年,她在当年7月去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一位村支书告诉他们,地震后,路断了,他们村由于位置偏远也成了孤岛。一开始,村民们相互接济,勉强度日。随着食物逐渐消耗,整个村子快坚持不下去了。
村支书终于拨通了乡镇书记的电话。对方回他,先撑着。但撑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在绝望日渐加重的煎熬中,村支书在废墟里找到一只收音机。他打开调试了一会儿,呲啦的声波里传来总理的声音:“大家坚持下去,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你们。”
几个月后,在建起的临时板房里,村支书对谭花他们讲起那个时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们村子没有被放弃,”谭花回忆着,强调道,“社会公众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