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一个隆冬,天空下着鹅毛大雪。

就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瘦削佝偻的老人,缓缓向前走着。
天色渐暗,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终于在接近部队营地时,一头栽倒在厚厚的雪地里。
当部队的官兵发现并将老人救回营房时,他已经几近虚脱。
当他缓缓睁开双眼的那一刻,却挣扎着立正,颤巍巍地向团长敬了一个军礼,接着,他用尽全身力气,用嘶哑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报告首长,任务已完成,请指示!”

这短短的十二个字,让在场的所有人瞬间呆住了,年逾七旬的老人是谁?他为何跋涉千里来到这里?他口中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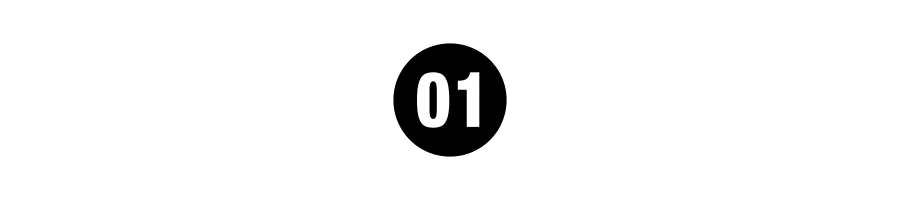
当时晋察冀军区某部队正向关外转移,在这片山地,部队前锋意外发现了敌军的踪迹,而后方的追兵也紧紧逼近。
前有堵截,后有追击。
经过短暂的分析,团长迅速作出了决定:大部队趁夜撤离,务必保存有生力量。

要想让几百人安全撤退,就必须有人留下来断后,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为大部队争取宝贵的时间。
“谁来断后?”这是战场上最危险的任务,一句问话让空气瞬间凝固。
一旁的连长几乎是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部下,他深吸了一口气,“交给我们连吧。”
断后的命令迅速在连队中传达,而此时,连长又将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指派给了他的排长常孟兰。
常孟兰没有任何犹豫,只是敬了个礼,“我带人去。”

这个“去”,很可能意味着永别,但在当时的战场上,没有时间留给士兵们去思考其他。
连长最后的叮嘱,是那句让常孟兰记了一辈子的话:“只要号角声没响,绝不能撤退!”
夜幕渐渐降临,长城脚下寒风刺骨,常孟兰挑选了五班的7名战士,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带着轻机枪和手榴弹,潜伏在敌人可能经过的山路上。
此时,整座山谷寂静无声,只有北风在耳边呜咽,一名年轻的战士趴在隐蔽处,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枪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低声问常孟兰:“排长,能坚持多久?”

常孟兰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坚持到天完全黑下来,等部队安全撤离,我们再撤。”
敌人的脚步声打破了夜晚的沉寂,首先出现的是探路的士兵,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前方摸索前进,不时停下来观察周围的动静。
常孟兰示意队员们按兵不动,直到敌人离得更近。
终于,当敌人的主力出现在射程内时,常孟兰果断下令开火。
一时间,枪声炸裂山谷,手榴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敌人显然没料到这里有埋伏,常孟兰带领的几名士兵迅速转移位置,利用山地复杂的地形,再次发动猛烈的射击。
敌人很快反应过来,调整了战术,开始反击。
他们用重机枪扫射,用照明弹刺破夜空,试图找出隐蔽的阻击点。
常孟兰迅速判断局势,立即命令队员分散作战,各自寻找掩体,尽可能延缓敌军的推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
常孟兰和他的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逼退,弹药也在逐渐消耗殆尽,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但那声令他们撤退的军号,却迟迟没有响起。

“排长,我们是不是该撤了?”负责监听军号的小战士忍不住跑过来询问。
他的脸上满是焦急,常孟兰明白他的担忧,却依旧冷静地回答:“没有命令,我们不能撤。”
话音刚落,又是一波猛烈的炮火袭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名战士倒下了,他们的身体再也没有动弹。
常孟兰咬紧牙关,抬起已经被冻得僵硬的手,将轻机枪架在石头上继续开火,他的眼睛被浓烟呛得模糊,但他的枪口始终没有偏离敌人的方向。
最终,当敌人的照明弹再次升起时,常孟兰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寥寥几人。

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周围的土地,而敌人的脚步却越来越近。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常孟兰在心里默念。
这一刻,他们已经成为了死神面前最后的一道防线,而此时,战斗才刚刚进入最激烈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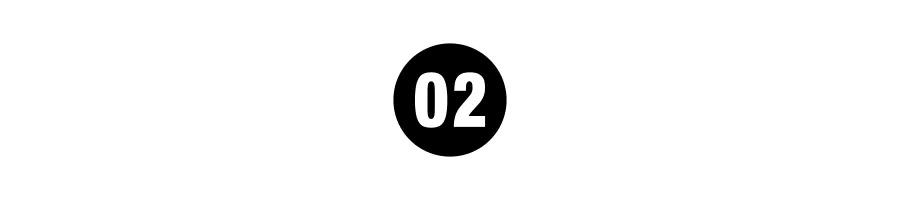
当最后一颗子弹从枪膛中射出,常孟兰的手紧紧攥着空了的弹夹,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疲惫。
他们已经弹尽粮绝,而敌人的脚步却愈发逼近。
周围的战友,早已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冰冷的土地上,只有几名幸存者还在拼尽全力抵抗。

但此刻,常孟兰的耳边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呼喊声,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胸膛里剧烈地震动。
天彻底黑了下来,风雪渐渐加重,敌军的炮火依旧不曾停歇,照明弹刺破夜空,将他们的位置暴露得一清二楚。
常孟兰的双腿早已麻木,身上的伤口也因严寒,冻得失去了知觉。
他紧贴着一块巨石,那些他熟悉的面孔,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们,如今已倒在尘土里。
他们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想喊却喊不出,只有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就在这时,敌人的攻势再次升级,他们发起了最后的总攻,重炮猛烈轰击,地面震动得如同翻滚的浪潮。
常孟兰迅速低下头,贴着地面滑入一片阴影处,避免暴露自己的身影,他瞥了一眼四周,发现自己身边再也没有一个活着的战友。
“兄弟们,都没了……”
常孟兰下定了决心,他抓起仅剩的一颗手榴弹,用牙齿咬开引线,奋力朝敌人扔了出去,伴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吞没了敌军的前排士兵。

他趁着爆炸引起的混乱,迅速从地面跃起,借着黑暗和地形的掩护,朝着山后跑去。
风雪扑面而来,夹杂着敌军混乱的吼叫声,常孟兰不敢回头,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去,向大部队报告情况。
不知跑了多久,常孟兰的双腿像是灌了铅一般沉重,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他的体力渐渐耗尽,耳边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天色已蒙蒙亮,敌人的追兵似乎还在远处。
常孟兰闭上眼睛,脑海中那一声声爆炸,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仿佛都在眼前闪回。

他想起了出发前连长的叮嘱:“军号声不响,绝不能撤。”
深深的自责在心头涌起,他咬紧牙关,不让眼泪流出来,作为排长,他的职责是带领队伍完成任务,可如今,他却是唯一活着的那个人。
他躲藏了几个小时,等敌人的搜索部队彻底散去后,才踉跄着站起来,继续朝着安全的方向行进。
可想找到大部队,谈何容易。
在艰难地走了数天之后,他穿过了敌军的封锁线,回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带。

当他试图寻找大部队时,却发现他们早已转移。
无奈之下,他只能暂时回到自己的家乡——河北赞皇县,回到老家的他,四处打听部队的下落。
可是,那个年代的通讯并不发达,部队的调动信息更是机密,他几乎找不到任何线索。
他去县城的政府部门登记自己的信息,希望通过军队的档案寻找到自己的连队,但得到的回复却让他失望:“战争结束后,部队编制重组,你的连队可能已经撤销,建议你等待通知。”
等待是一种折磨,常孟兰每次梦到当年的战场,梦到战友们的牺牲,都会从梦中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他害怕,害怕那些牺牲的兄弟被遗忘,更害怕那些兄弟被污名化,他们不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孬种。
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不行,我必须找到部队,把这一切都说清楚。”
于是,他背起行囊,踏上了漫长的寻找之路。
常孟兰的第一站,是北京,当时,北京是新中国的政治中心,或许那里有自己需要的答案。
1950年,他省吃俭用,带着积攒下来的几块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抵达北京后,他一路打听,找到了解放军接待复员军人的部门。

随着常孟兰的叙述越多,工作人员的表情也渐渐变得凝重,他们翻阅了大量档案,却始终没有找到与常孟兰所在连队相关的记录。
“你的部队可能已经解散,或者改编到了其他番号中,具体情况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调查。”工作人员安慰他。
常孟兰在北京足足待了半个月,每天来回于接待室与街巷之间,和工作人员交流、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
最终的结果却让他倍感失望——档案中的信息有限,他的连队的记录大多已经被时间湮灭。

抱着遗憾,他只能离开北京。
常孟兰的寻找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败而停下,他先后去了石家庄、太原、沈阳,甚至长春等多个城市。
他从军区的接待站,到地方的退伍老兵协会,几乎跑遍了所有与军队有关的单位,他不止一次地说:“我要找到部队,报告任务完成的情况,也要问清楚那场战斗的结果。”
有时候,他会在当地的街头遇到一些同样带着军帽或穿着旧军装的老人,他总是主动上前攀谈,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每一次,他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部队的番号早已改动,或者战友们早已天各一方。
到了六十年代末,常孟兰的头发已经花白,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
他曾对妻子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找到部队,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对不起那些跟我一起牺牲的兄弟。”
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常孟兰已是古稀之年。
1995年,常孟兰在街头偶然遇到了一位老军人,这位老军人正是解放军某军事学院的副院长王定庆。

得知常孟兰的经历后,王定庆深受感动,他表示愿意帮助常孟兰寻找部队的下落。
这一次,事情似乎迎来了转机,王定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多方联系老部队的负责人,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终于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沈阳军区某集团军的前身,正是常孟兰当年的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而驻扎在辽宁本溪的地炮团,便是三十团的后续编制!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常孟兰几乎落下了眼泪。
他的家人纷纷劝他:“你年纪这么大了,路途那么远,等有机会再去吧。”

常孟兰没有丝毫犹豫:“等不了,这么多年我都找过来了,这一次,我必须亲自去一趟。”
1996年初,常孟兰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辽宁的路。
他的身体早已大不如前,家人为了让他安心出行,给他准备了足够的干粮和御寒衣物,长途跋涉的艰难依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河北到辽宁,常孟兰几经转车,坐火车、换汽车,又步行了十几公里。
他的体力渐渐透支,到了桥头镇时,已经是大年三十的前夜,由于路途遥远,汽车停运,他只能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步行前往十公里外的部队驻地。

漫天飞雪中,常孟兰的双腿早已僵硬,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每当他想停下来休息时,耳边仿佛会响起连长的叮嘱:“军号没响,任务未完。”他告诉自己:“我还没完成我的任务,不能停下!”
终于,当他看到部队营地的灯光时,他的身体已几近虚脱,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一步步爬到营地门口,最终倒在了厚厚的雪地里。
经过几十年的奔波,常孟兰终于接近了自己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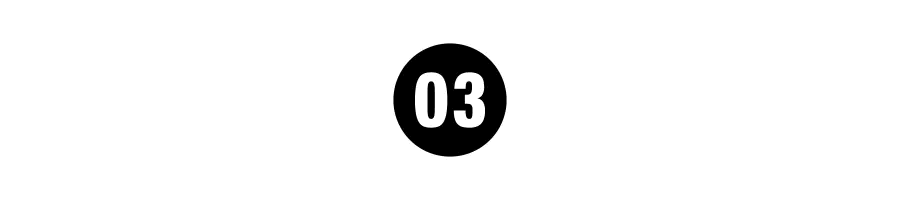
当常孟兰醒来时,周围是一片温暖的光亮。

他的身体被盖在厚厚的棉被下,脸颊和手脚已经渐渐暖了过来。
他用力地眨了眨眼睛,意识逐渐恢复,耳边传来低声的交谈,是几个年轻的战士站在旁边,正小声讨论着他的身份。
“你说,他是谁啊?怎么大年三十的夜里,还跑到我们营地来?”
“我听说,这老爷子是来找部队的,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团长报告。”
常孟兰吃力地撑起身体,声音嘶哑:“我……我要见团长!”
周围的战士立刻围了过来,扶住他摇晃的身体,“大爷,您别急,团长很快就会过来。”

不久,一名身着军装的年轻团长推门而入。
他步伐稳健,目光沉稳,但当看到面前这个满头银发、满脸风霜的老人时,却不由得愣住了。
他忙走上前,弯下腰,问道:“老人家,您找我有什么事?”
常孟兰深吸一口气,用颤抖的手扶着床沿站起身。
他艰难地立正,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无比标准的军礼。
“报告团长!原晋察冀军区四纵十旅三十团三营八连二排排长常孟兰,奉命带五班七名战士,为掩护部队安全撤离执行阻击战。

在战斗中两名战士牺牲,其余人员下落不明,我不幸与部队失去联系……请首长指示!”
屋子里的战士们顿时安静下来,空气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年轻的团长站在那里,眉头紧锁,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复命”搞得不知所措,他目光复杂地看着眼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像是在消化他的每一句话。
“您说,您是咱们三十团的老战士?”团长试探着问道。
常孟兰点了点头,慢慢放下右手。

他的眼中闪着泪光,他开始向团长讲述那场发生在1948年的阻击战,讲述自己和战友们如何在古长城脚下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如何为掩护大部队撤离而坚守阵地。
“那一天,连长说,军号响了我们才能撤。但我一直没听到军号声……”常孟兰的声音低了下来,带着掩不住的哽咽。
他握紧双拳,双手青筋暴起,“我的战友们,全都牺牲了。我一个人突围出来,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听到军号,才导致了他们的牺牲……”

团长的脸色越来越沉,他听得异常专注,听到这里,他终于忍不住问:“老首长,这么多年,您都在找部队?”
常孟兰抬起头,用力点了点头:“是!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安心?”
年轻的团长转过头,对身边的战士说道:“去,把荣誉室的资料取来!”
不一会儿,战士们拿来了一本发黄的档案,团长翻开后,很快在其中一页停住了。
他的目光锁定在一张黑白照片上,那是几十年前一支连队的合影,照片的右下角写着“八连”两个字。

而在合影的中央,一个年轻的身影正对着镜头,神情坚定,那是属于常孟兰的面孔。
“是您!”团长有些激动地说道,将照片递到常孟兰面前。
常孟兰接过照片,眼睛死死盯着那张泛黄的合影。
他的手微微颤抖,指尖轻轻划过每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团长站直身体,郑重地向常孟兰敬了一个军礼:“常孟兰同志,我代表部队,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您和战友们当年的英勇付出,部队从未忘记!”

听到这句话,常孟兰的身体轻微地晃了一下,他闭上眼睛,任泪水无声地滑落。
他等了四十多年,自己和兄弟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句认可。
他慢慢抬起手,回了一个军礼,声音哽咽:“谢谢首长,谢谢部队。”
常孟兰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或许,连长他们也遇到了突发情况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听到,才害死了我的战友……”

团长拍了拍常孟兰的肩膀,低声说道:“无论号角有没有吹响,您和战友们的牺牲都是值得铭记的,是你们的坚持,换来了大部队的安全,无论结果如何,您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
这句话,像是一剂安慰的良药,却又无法抚平常孟兰心中的遗憾,那一声未曾听见的号角,成为了他一生的心结,也成了他内心无法填补的空白。
他的兄弟,他的战友,已经永远留在了1948年的那片山岭上。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这片土地不再有硝烟弥漫,也不再需要断后者的牺牲。

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份和平,是像常孟兰这样的英雄,用血肉之躯换来的,他们的故事,值得被书写、铭记,代代相传。
正如那句话所说:“国泰民安的背后,是一代代军人负重前行。”
【免责声明】:本文创作宗旨是传播正能量,杜绝任何低俗或违规内容。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私信及时联系我们(评论区有时看不到),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