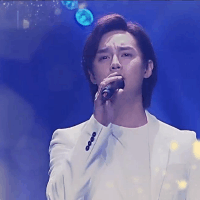亦舒是香港都市文化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在女性文学小说中占据半壁江山,她的看法改变许多中国现代女青年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中国有大量的女性作家,但亦舒只有一个。
电影《喜宝》10月16日正式公映,观影之前,又读了一遍小说,这样在观影的时候会更有感觉。

电影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亦舒传播度最高的经典名句:“我想要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有很多很多钱,也是好的”,这句直到今天仍是十丈红尘中最具洞察性的金句。
不光是小资界,亦舒的作品影响了各个角落的独立女性们 ,包括千亿儿媳徐子淇妈妈也奉行小说《喜宝》中的经典台词:“学历是女人最好的嫁妆”。

对于一部拥有众多读者的成功小说来说,粉丝都希望《喜宝》的影视化能忠于原著。
我觉得如果影视改编能基本忠于原著就可以,当然基于篇幅、载体、实际拍摄、审查等诸多方面的考量,说不定上映时还会有一些情节线索的调整。毕竟即使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观众出于不同的文化经历、人生经历、家庭经历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
在《喜宝》观影过程中,它展现了重点剧情线——喜宝命运和性格的轨迹,即:她为什么想要有很多很多爱,她为什么想要有很多很钱?

命运是一个特别大的主题,它看似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却早已渗透在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许思考明白这个问题,就是掌握了人生,所以喜宝搬到勖存姿的别墅中后才敢真正考虑命运的问题。喜宝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下女性最常遇到的问题:生存与自主意识。“很多很多爱”是女性生存的基础;没有爱,钱就失去了诱惑。
在小说《喜宝》中,她面临的是一个逆向选择,如果没能很多很多爱,那么要有很多很多钱。她走投无路,她别无选择,她没有生存基础,她是脚不沾地式人物形象,这是女性最矛盾的一面。
喜宝下意识的抗拒勖存姿拿过来的投资,但她不知道在抗拒什么?她既不抗拒钱,也不抗拒爱,她对抗的是自尊。
当二流子爸爸得知她过上好日子,不远万里搭飞机过来揩油时,她对他说:“如果有人用钞票扔你,跪下来,一张张拾起,不要紧,与温饱有关的时候,一点点自尊不算什么。”你看,她从头到尾就是清醒的。一个人清醒的越早,她脱离无奈与艰辛的挣扎就越早。
今年疫情初期,不光健身房的教练去做外卖员,有一些硕士本科生也走到了这一行,甚至还有人白天上班晚上送外卖,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角角落落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决定。所以,男性可以,女性也可以。

《喜宝》的故事背景是在197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时代还没有对女性完全包容,包括现在仍是这样的局面。
去年我曾为亦舒的另一部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女主流泪饮泣。子君数十年如一日维护温馨的小家,有天丈夫毫无预兆的宣布要离婚,没经济独立的她一下子从阔太太神坛跌到了靯柜售货员。这不是法国19世纪的《羊脂球》、《项链》、《巴黎圣母院》,这不是火树银花一场虚无,这是如同你我般在三十岁刚刚跑向中产末端的小家庭。

亦舒把“喜宝”一开始设定为俗气、屈辱、寂寞、算计的名校女其实是有反向意义的,你越排斥它,到最后越能认识到它的必然性。
有很多很多钱,大概率也会有很多很多爱;有很多很多爱,大概率也会有很多很多钱。相反,如果一个女人既不要钱,也不要爱,那她面临的有可能是一场逃不掉脱不掉的宿命。
电影《喜宝》看上去每个画面都是直暴的,但细品之下都是无限因果的叠加。以“安全感”为前提的考虑其实是所有都市女性内心的需求,她们要么面向丈夫、要么面向职场、要么面前孩子,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是有索取过程的。片花中的跑车爱吗?爱。别墅爱吗?爱。帅男艳遇,想吗?想。看故事的人诚实的面对自己,才能体会主角的心情。当然,想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所以女性看《喜宝》在关注什么?她们在关注另一个自己的命运。

从奥斯汀到亦舒,从文学小说到电视剧,间隔两百多年,间隔了多样的表达形式,女性的归宿在何方,至今都没有答案。当然,现在比过去的跨度可能更大,拥有的无限性也更接近,但我们没有一个范本说“这就是正确女性命运”。
新时代女性如同过去一样,内心的火焰根本就没有熄灭过,门户、阶级、财产、爱情、人格缺一不可,绝大部分没有改写命运的女性仍是失落和快乐的叠加,或许拯救“灰姑娘”是一个“老王子”,但总好过一生陷在泥里。
每个人起身时都是道德专家,坐下时都是卑微的芸芸众生。不回避情感的欲望和需求,让理性护航漫漫人生路,正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