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我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悲剧人物。追根溯源,他的悲剧早在1920年的建党初期便已初现端倪了。

1920年4月,苏俄“十月革命”先驱列宁领导的苏俄远东共和国远东局正式成立,这个旨在指导远东地区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和协助周边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很快便成了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后盾。
几天后,作为远东局代表的维经斯基率党小组来到“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并见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手”李大钊,又在李大钊的推荐下,一行人赴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很快,达成共识的两人就这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步——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组织成立了,面临的最窘迫问题是缺乏运行经费。毕竟在那个革命思潮迅速传播、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无论是宣传还是组织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

或许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和道义,亦或是希望日后能占有更多的话语权,维经斯基向陈独秀表达了每月固定由远东局拨付经费的主张。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陈独秀不假思索的果断拒绝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革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人帮助与否,自己都要走上这条道路,而靠别人资助的革命是不可取的。
这话其实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一旦用了你们的钱,以后的革命行动中我们便失去了组织独立性而变成你们的附庸,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道理自己还是懂得的。
在陈独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势下,维经斯基着实尝到了闭门羹的滋味,这次的谈话不欢而散。
一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一大”后,再次向陈独秀提出了申报预算继而由共产国际出资援助中国革命的意见。在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以支部的身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并争取其更多的支持和援助为第一发展要义时,陈独秀却拍案而起。在他看来,中国的革命事业必须保证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力,不能被任何外部力量所牵制和干涉,结合自己的国情走符合社会现状的革命道路才是最终出路。

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嘴巴硬抵不过膝盖软”,建党一年后的陈独秀很快在经费吃紧、入不敷出的艰难情况下勉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方案,当初的慷慨激昂最终在现实面前最终便成了逆来顺受,而这也注定了他领导下的这个新生组织将在共产国际面前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自己的话语分量也随之一落千丈。
很快,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便悄然而至了。其实早在此之前,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继而开展国共合作是持坚决反对意见的。一方面是他对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军阀争斗和各种资产阶级不良习气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认为彼时的中共力量尚处于弱势,在没有自己掌握的足够武装力量的前提下,极有可能面临被国民党分化乃至吞并的风险。
当然,马林和共产国际方面却并不这样看待。在他们看来,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力量占据优势,就实现最终革命目标而言,国民党是不可或缺乃至更胜一筹的合作伙伴,同时,对弱小的新生共产党而言,借助国共合作的契机也可迅速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总之百利而无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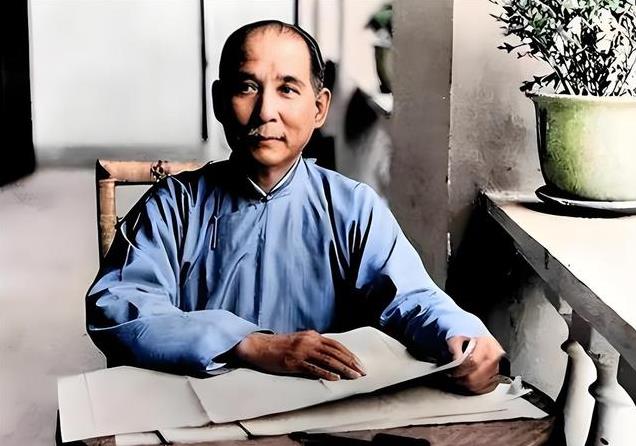
几番争论无果的马林将意见上报了共产国际,结果可想而知,陈独秀得到的命令是无条件配合马林开展国共合作的革命运动。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来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无论对我党还是对全国革命形势都是有利的,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
但与此同时,陈独秀本人却充满了无限压抑和疲惫,他时刻能够依稀感受到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方面共同向他施加压力,自己有种处处被针对的感觉。先是在1926年初的国民党“二大”上,自己据理力争的中央执委席位被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老蒋等人联合压制下仅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后又相继爆发了以削弱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力量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事件,让陈独秀逐渐看清了老蒋的反动和独裁面目。

他向共产国际上书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时刻做好老蒋背叛革命后的斗争准备。毋庸置疑,共产国际的说法无外乎批评、驳斥和坚决纠正等措辞。
几个月后,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面对共产国际一再退让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陈独秀心力交瘁,他主动提出辞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共产国际迫于威信压力,又需要这样一个为中国革命失败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来“背黑锅”,换句话说,在共产国际的“字典”里,陈独秀没有辞职的权利,却有“被开除”的义务。
当然,陈独秀内心也是有苦难言,自己一切行动听指挥,最后却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淮阴侯韩信而被共产国际弃如敝履了,任凭恩怨与无奈也只得藏于心间。

平心而论,共产国际就大革命失败而给予他的免职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毕竟陈独秀本人虽在革命低潮时也曾表达过消极妥协的言语,但归根结底,他的退让之举不过是共产国际因政策失误而导致无人接管的烂摊子形势下的一种被迫无奈妥协罢了。
而陈独秀之所以有着今天的一众负面评价,多半来源于他的书生意气。
1929年春,被解职后的陈独秀在读到苏联党内反对派代表人物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立时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他不仅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要远胜于斯大林的“阶段革命”理论,更是与一众“志同道合”的人于次年联合成立了宣传“托派”理论的“无产者社”,除了公开支持托洛茨基外,也表达了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强烈抗议。
结果可想而知,陈独秀被彻底开除出局。但性格鲜明的他却并未因此止步,又先后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等旗帜鲜明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彻底将自己推向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方向。

如果仅仅是因路线之争表达支持或反对意见这本无可厚非,毕竟人人言论自由,但以党派创始人身份蝉联五届最高领导人的他在受到开除处分后依旧从事另起炉灶的“分裂”行为,任凭哪个党派和领导人都不可能置若罔闻,这也是时隔二十多年后教员将其列为“阴谋分裂”阵营中的主要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陈独秀能少一些书生意气,及时悬崖勒马,避免深陷路线之争的泥潭,亦或是在受到处分后能深刻反思和总结,或许他的正面评价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加丰富立体,尽管如此,他的名字早已成为近代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功过得失不仅是早期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历的真实写照,也是后来人值得学习和反思的重要理论素材。
如今,当我们再度回首那段艰难历史中的陈独秀,除了感受到他彼时的恩怨与无奈之外,或许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自己的那句诗作:“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