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目前已知的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
广义上的三星堆文化包括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末周初时期生活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带中国先民们留下的诸多文化遗址。

而狭义的三星堆文化,则特指发现了8个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黄金权杖的那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遗存。
有什么区别呢?文化是一定时间段内的某一群体创造的面貌相似的痕迹,而遗址则是所有在某一区域生活过的人类遗存,这个遗存可能前后差异较大,时间跨度也久远得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河南安阳殷墟是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文化指的就是商朝晚期文化,但殷墟这个地方并不是只有商朝人生活过,在殷墟文化之下还叠压着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而在殷墟文化地层之上,又分别有周朝甚至更晚的明清时期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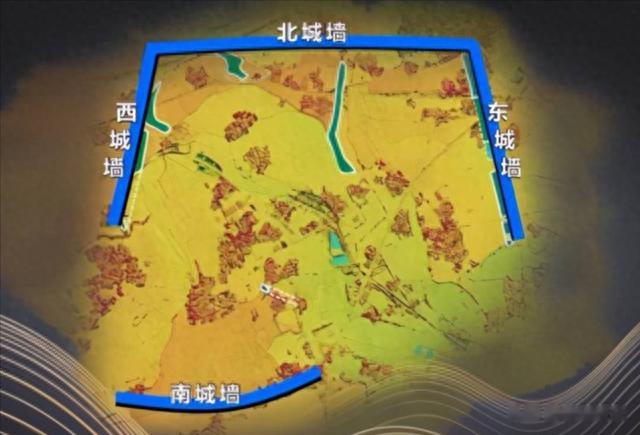
而本文所指的三星堆文化,是狭义的三星堆文化,这就决定了它的绝对年代是夏朝晚期到商末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046年前后。
在三星堆文化出现之前,成都平原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与中原文化平行发展且相互独立。
但三星堆文化却并非是宝墩文化自然发展而来的产物,而是突然崛起在成都平原的,并且直接终结和取代了宝墩文化,二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宝墩文化的底层生活陶器被三星堆文化继承和沿用,但三星堆文化上层精神信仰却体现出浓郁的二里头风格,比如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在商朝时被废弃,但却在三星堆文化中被继承和使用。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牙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形制上还有改进和发展,出现了铜牙璋和牙璋形金箔。更重要的是,牙璋在三星堆人所有的重要祭祀场合中都是必然出现的祭祀重器。
这种情况很难用单纯的文化传播和贸易交流来解释。因为三星堆文化存续的时间是夏末商初到商末周初,其中与商朝的重叠期最久,按道理也应该最容易受到商文化影响。

事实上,三星堆的确发现有明显来自殷商的尊和罍。中科院研究员苏荣誉教授也曾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提出如下结论:“从铜器的铸造方法和工艺系统来看,三星堆铜器与中原系铜器并无两样,它们都是采用块铸法铸造成形。”
此外,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的矿源检测结果显示,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所用的铜矿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但偏偏三星堆人在祭祀时,却选择了夏朝的典型器物牙璋,而不是商朝的鼎,这恰恰说明,在夏朝灭亡时有夏遗民进入了成都平原,与这里的土著居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故而三星堆人的上层精神信仰中才会有夏文化的踪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撰写的三星堆文化研究专著,正文即开宗明义“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时期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但是,如果把三星堆解读为夏遗民遁入巴蜀之地建立的流亡政权,那么就会带来另一个困惑,因为除了牙璋之外,三星堆还有纵目面具、黄金权杖以及青铜神树这些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即便放眼当时整个中原、西北或者长江流域,也都无法找到三星堆这些奇异遗存的源头,在塑像上覆盖黄金面具、金箔的做法以及造型抽象、突出眼部特征刻画的手法,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反而能找到形似物。
所以,三星堆恐怕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夏遗民带着成都宝墩文化土著后裔共同创造了一个全新文化。
要弄清楚三星堆整个来龙去脉,那么三星堆人的祭祀无疑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无论三星堆挖出的东西多么罕见而奇特,从宏观上看,它呈现出的面貌就是一个神权至上的场景,三星堆人日常的重要活动就是祭祀,它的国家财富也几乎全部用来祭祀了。
比如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他们的服式、冠式、发式虽然各异,但却都在同一个祭祀场景出现了,说明无论是世俗权力的掌控者还是负责祭祀的神权群体,他们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被祭祀对象。

三星堆古城极少发现青铜器,但8个祭祀坑却埋葬了数以万计的青铜、黄金以及象牙制品。可以想象,这些弥足珍贵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用于社会生产,而是用来完成某种神秘的仪式。
在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都只有祭祀祖先的宗庙,而没有祭祀自然神的神庙,但三星堆却两者兼有。而根据三星堆8个器物坑出土物可以判定,祖先、太阳、神鸟、龙、神山都是被三星堆人祭祀的对象。
这种祭祀对象的庞杂,就如同三星堆那神秘的祭祀仪式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1986年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神预言,直接猜中了其中缘由。
童恩正是四川大学历史学专业科班出身,但却是个“不务正业”的科幻和考古“两栖”学者,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就是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或许是长期的科幻创作经历赋予了童恩正丰富的想象空间,在1986年三星堆1号、2号器物坑刚刚被发现不久,童恩正即提出:

“在我国的东北到西南存在一条绵延达万里的半月形地带,在此范围之内,生态环境呈现出很多的相似之点,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活动和风俗习惯的相似,流行石棺葬、青铜器上动物形纹饰盛行、陶器或铜器喜用两体相连。
居住于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民族,其风俗习惯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当这些古代民族因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需要迁徙时,往往也是选择与自己习惯的环境相似、居住着与自己经济活动相同的民族的地区,从而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文化的共同性。”
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在童恩正预言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弧”这一概念。
 而此后的考古发现,也的确印证了童恩正的预言。
而此后的考古发现,也的确印证了童恩正的预言。四川彭县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罍,其风格与中原传统之罍有别,但却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罍酷似;四川茂汶营盘山石棺葬出土的扁平钩形格青铜剑在中原地区并未发现,却与内蒙古赤峰南山根遗址出土的C形剑有类似之处。
三星堆8号坑新近发掘出土的一件大型祭祀用品—青铜神坛,经过文物修复和“跨坑组装”后,人们惊奇的发现,这件高达160厘米的三层连体堆叠青铜器,形象刻画了三星堆人的祭祀场景。

最下层镂空基座悬挂铜铃,青铜礼器悬铃的形式起源于北方,类似器物主要出土于辽宁和晋北等北方地区;基座之上有13个人物形象:抬杠力士、坐姿铜人和跪姿铜人各4个,中间还有一个背罍铜人,台基四角面朝外呈跪姿的四个人物,疑似戴有面具,双手疑似握持牙璋;台基四边的中间有四个坐姿人像,双手放在膝上,这种姿势区别于中原人臀部坐在小腿及脚跟上的跽座,而且还穿着翘头靴,明显来自草原地区。
神坛的上层是四名力士抬着的神兽,说明其地位较高,神兽栓有绳索,上有跪人像,有被驾驭的含义。第三层为青铜顶坛人像,似乎在沟通天际,与《山海经》记载的古人乘龙驾雾沟通上天的祭祀场景颇为吻合。

此外,三星堆还出土有络腮胡和高鼻深目的异域人种形象,所以,与其说三星堆有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倒不如说三星堆明显是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在半月形文化带内交汇的结果,所谓的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人物形象、黄金面具等,也都是草原风格的产物。
明显属于西来性质的三星堆黄金权杖,也并不一定是埃及和三星堆直接交流的结果,很可能也是通过北方草原作为传播渠道的,位于陕西西安的西汉薄太后南陵中,就曾发现大量来自草原的罕见金器,也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从考古发现的宏观角度来看,代表中原王朝文明的鼎、爵礼器,在进入三星堆所在的半月形文化带后,就再也没有向西传播;而代表西方文化因素的黄金权杖,同样在进入三星堆所在的半月形文化带后,也没有继续向中原腹心地带传播。
这个半月形区域,就如同一个大熔炉一样,同时吸收了两大互不统属的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兼具两大文明特色的三星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解开一个疑问:三星堆人究竟在祭祀谁?
虽然三星堆人祭祀因素中出现了太阳、神鸟、龙、神山等诸多因素,但三星堆青铜器堆叠的铸造工艺,表明了位居最上层的还是最高祭祀对象。
《山海经》中认为太阳是金乌的化身,也就是将太阳和玄鸟结合起来,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形象地塑造出了“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太阳神鸟。此外,青铜太阳轮、太阳神鸟金箔以及8号坑出土的奇特的一层一层堆叠而成的青铜神坛,最终表达的都是对太阳玄鸟的崇拜。

无论三星堆文明杂糅了多少外来因素,青铜神坛的祭祀场景已经表明,罍、牙璋、铜铃乃至驾驭神兽的跪人像所穿的云雷纹衣服,所祭祀的对象应该就是太阳或者等同于太阳的玄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