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丨卿心君悦来聊嘿,大家听听这个。这事儿啊,得从卿心君悦那儿说起。他讲的东西,我琢磨了下,觉得挺有意思。咱们不妨换个方式聊聊,尽量说得简单直白点,别整得太复杂。其实呢,核心内容没变,就是把那些长句子拆拆短,换个说法,让大伙儿一听就明白。就像是把原文里的那些“高大上”的词儿,换成咱们平时说话用的词儿一样。当然了,意思得保留住,不能改了人家的原意。卿心君悦说的那些,咱们还是得尊重,不能乱加东西进去。句式嘛,多变变,别老是一种调调,这样听起来也更有味儿。就像咱们平时聊天,也不会老用一种方式说话对吧?还有啊,尽量说得简洁点,别啰嗦。字数嘛,差不多就行,别整得太长了。反正啊,就是要把原文的意思,用咱们自己的话,简单明了地说出来。所以啊,大伙儿听好了,这就是我对卿心君悦那事儿的一点小改动,希望大伙儿能喜欢。
鲁迅在《忽然想到》这本书里,讲了个凶兽和羊的小故事:
武者君在路上碰见了两个家伙,一个是凶猛的野兽,另一个则是温顺的羊。他赶紧把这个情况跟鲁迅说了。
鲁迅听完笑了笑,对武者君说,你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路上的事儿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武者君好奇地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鲁迅讲过这么一句话:
他们就像羊一样温顺,可骨子里也藏着猛兽的性子。要是碰到比他们还凶猛的家伙,立马就变得乖乖的,像只小羊羔;但要是遇到比他们弱的羊,那就立刻露出猛兽的一面……这些话是鲁迅说的,意思就是这样。
1920年9月份,鲁迅大佬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叫《风波》的小说。

这么多年来,大家聊起这篇小说,老爱提“张勋复辟”和“留不留辫子”这两档子事,都说它跟《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一个路数,就是想说说革命没搞彻底,还有辛亥革命那场闹剧咋就黄了。
但是,像鲁迅这样的大师,专门研究人性,他通过“发型的变换”和“人心里头那点子不变的东西”所领悟到的,难道就只有这些表面上的吗?
不嘛!
鲁迅啊,他比起政治,更上心的是人,具体来说,就是人身上的那股“国民性”,就像是人在狼和羊之间能来回变似的。
【风波初起】
《风波》一开头,鲁迅就用他那娴熟的白描技巧,给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又暖心的乡村画面——
老爷子坐在小凳子上,拿着大芭蕉扇边扇边聊着天,小孩们像风一样跑来跑去,要不就蹲在乌桕树下比赛扔石子。大妈们端出了黑黝黝的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腾腾地冒着烟。
坐船经过的大文豪,看到这幅炊烟缭绕、满是乡村童趣的景象,心里头诗兴一下子上来了:
“啥烦恼都没有,这不就是田园生活的乐趣嘛!”老李笑着说道,一脸满足。

这地方真的像说的那么漂亮吗?
不,这其实是鲁迅巧妙布置的一出讽刺戏码。你瞧瞧,当你把视线从河面上那悠悠的小船移开,转到河边那块空地上时,你就会发现,这幅所谓的“乡村美景”其实挺不堪入目的。
79岁的九斤奶奶坐在桌子旁边,气呼呼地冲着曾孙女六斤嚷嚷:“六斤啊,你看看你,真是让我头疼!”九斤奶奶满脸不悦,话语中带着几分责备。“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呢?”她边说边摇头,显然对六斤的行为十分不满。六斤站在一旁,低头不语,心里估计也知道自己惹奶奶生气了。九斤奶奶叹了口气,继续用略带口气的语调教训着:“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不知道让人省心。”话语间,九斤奶奶的眉头紧锁,显然对这次的事情很是在意。而六斤呢,只能默默听着,希望能尽快平息奶奶的怒火。
饭马上就要开了,还嚼啥炒豆子,这不得把家里吃空了!
六斤拎着一听装的东西,手里还攥着把炒豆,一溜烟跑到河边乌桕树躲起来。她探出两个小辫子晃悠的脑袋,朝着九斤老太大声喊:
“这老家伙,真是活得够久的啊!”

因为隔得太远,再加上九斤老太年岁已高,她压根没听清楚六斤说了啥,只是习惯性地大声嚷嚷了一句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哎,现在这辈人啊,真是一代比一代差了点儿!”
穷日子真是难熬,就那么一小把炒豆子,愣是让祖孙俩本该有的那份亲近感没了。
没多久,七斤这个主角就亮相了。
七斤啊,他是九斤的孙儿,六斤的老爸。你别看他是个农民出身,但从他爷爷那会儿开始,家里就不再种地了,而是拿起木桨,干起了摆渡的活儿。
他经常进城,回来后就给乡亲们聊起城里的新鲜事儿,比如“哪个地方,雷公把蜈蚣精给劈了;哪个地儿,有个闺女生了个像夜叉一样的孩子”。因为这些离奇的故事,他竟成了村里的“名人”,大家都很信服他。

不过,今天这位“大腕儿”回来了,但没了以前的那股子高傲劲儿,反倒是耷拉着脑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看到七斤坐在桌子旁边的矮凳子上,六斤从树后面窜了出来,大喊了一声“爹”,可七斤却没搭理他。
歇了一会儿,七斤缓缓抬起脑袋,道出了他沮丧的缘由:“皇上又回宫坐龙椅了。”
七斤嫂刚开始没明白丈夫说啥,过会儿才琢磨过来,问道:“是不是又要大赦天下了?”
七斤唉声叹气地说:“我的辫子没了。”
“皇上他想要留辫子不?”
皇上想要留辫子。这话传开了,大家都知道,皇上对辫子情有独钟。可不是嘛,皇上说了,他就喜欢那长长的辫子,觉得特有范儿。这事儿可不含糊,宫里宫外都忙活开了。大臣们琢磨着怎么给皇上弄来最好的辫子,宫女太监们也开始张罗着,准备伺候皇上梳辫子。你问这辫子哪来的?嘿,那可得好好挑挑。得找那发质好的,又黑又亮的,还得柔顺,不能打结。这可得费一番功夫呢。可别说,这皇上要辫子的事儿,还真引起了不少轰动。大伙儿都议论纷纷,说这皇上可真是个有个性的主儿,连这辫子的事儿都得亲自过问。不过话说回来,皇上要啥,那就是啥。这辫子啊,肯定得给皇上弄得漂漂亮亮的,让他老人家满意才行。
得知老公早就把辫子给剃了,我好奇地问:“你咋知道的这事儿呢?”
七斤讲道:“咸亨酒店里的那些人啊,都说这事儿得行。”
一听是咸亨酒店那消息灵通的地儿传来的,七斤嫂顿时愣住了,瞅瞅对面坐着的光头七斤,心里的责怪和愤恨像潮水般涌了出来。她绝望地随手舀了碗饭,往七斤面前一推,带着怨气说:
赶紧吃饭啦!摆着张苦瓜脸,难道就能长出辫子吗?

餐桌上突然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七斤嫂抬头一看,见赵七爷那又矮又胖的身影正穿过独木桥往这边来。他还是穿着那件老样子的“宝蓝色竹布长衫”。
赵七爷那件长衫可不简单,里头藏着不少说道呢。七斤嫂回想起来,这三年里,赵七爷拢共就穿过两回。一回是那次跟麻子阿四闹矛盾,碰巧阿四病了;另一回,则是那个曾经砸了他酒馆的鲁大爷去世的时候。

这次赵七爷又套上了他那件长衫,七斤嫂一看就心里有数了,肯定是他有啥好事,对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她琢磨着,这个对头八成就是自家男人七斤。
七斤嫂回想起两年前那事儿,七斤喝高了,对着赵七爷就是一顿猛批,说他“不是个东西”。现在瞧见这“长衫”,又琢磨着七斤从咸亨酒店带回来的那些话,七斤嫂心里头就开始七上八下,翻腾个不停。

没错,赵七爷步子不稳地走到七斤背后,开始聊起了外面的新鲜事儿。
从赵七爷的嘴里,七斤嫂又得到了实锤,七斤这回是躲不过去了。而且事情还没完,你听听赵七爷怎么说:
这也没办法呀。没辫子能算啥罪,书上那可是清清楚楚、一条一条列着呢。不管他家里有啥人都没用。
听起来好像连家里人都要跟着倒霉,这话一出,七斤嫂立马火了,当着大家的面,直接用筷子点着七斤的鼻子,开口大骂:
这家伙真是自找的!当初闹革命那会儿,我就劝他,别划船了,也别进城凑热闹。可他偏不听,非要往城里闯,结果一进去就被人家把辫子给剪了。以前那辫子又黑又亮,现在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倒霉蛋自己作孽,还连累了我们,这叫我们怎么说得清呢?这半死不活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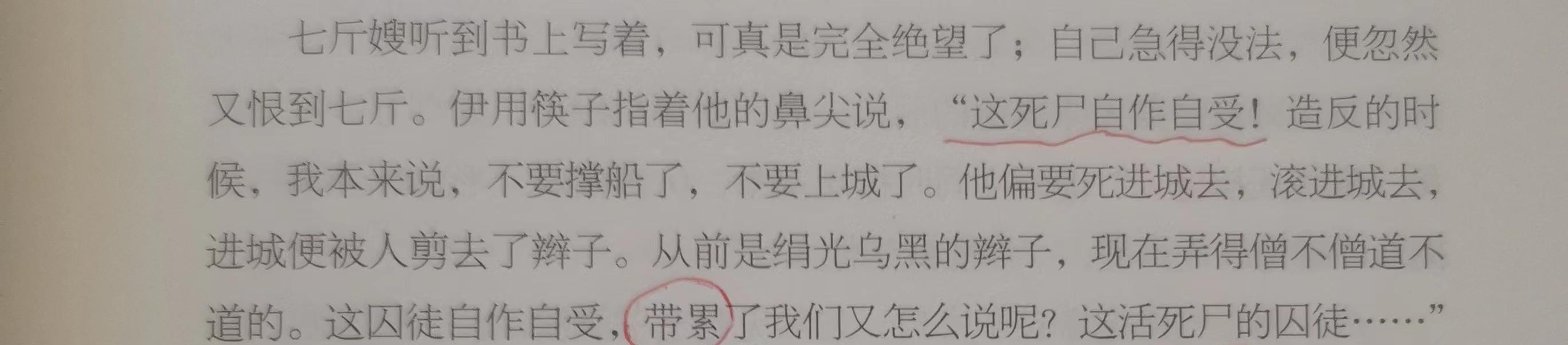
哎,说起来,北京那边闹出的那档子事儿(张勋复辟),到了鲁迅手里,又搅动起七斤一家的小风波。那边的大风浪还没平息呢,这边的小涟漪又泛起来了。
最近这段时间,七斤因为没了“辫子”,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感觉前途一片迷茫。不光如此,他还得在外头受着老婆当众指责和辱骂的窝囊气。
在七斤嫂看来,她现在不怎么担心七斤会不会因为那条“辫子”丢掉性命,她更怕的是“这事儿会牵连到我们”。
从九斤和他曾孙女一开始的互相咒骂,到后来听说“皇上要复位”的事儿,七斤嫂对七斤那叫一个怨恨加指责。这一连串的事儿,明摆着看出七斤一家穷得实在是没法儿了,为了活下去,连人的本性都给扭曲了。
得知道,家里头那种人性变得不正常的事儿,不是碰巧发生的,而是因为连最基本的吃喝问题都解决不了,人身上的那种“野兽劲儿”就给露出来了。
生活一旦陷入“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境地,人的本性就经受着层层考验,家里的亲情纽带也开始松动,往日的和谐氛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家人间出现了争吵和不断的指责谩骂,关系变得紧张。
【“奴性”之见羊是狼】
物质上的匮乏往往伴随着精神上的空虚,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呢,会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说白了,就是精神上的贫穷会让人情味变淡。
这事儿,余华在他的书《活着》里也说过——
人一饿急了,真是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就说那次吧,明明是凤霞好不容易挖到了一个地瓜,王四那家伙,看凤霞不会说话,就趁着她用衣角擦地瓜上的泥那会儿,一伸手就给抢走了……
在那个特别缺吃的年月,就为了争抢一个地瓜,凤霞、福贵和王四在地里差点就闹出大事来了,这事儿背后透出的人性问题,可真让人琢磨。
再聊聊鲁迅的《风波》里头,七斤嫂因为怕自己被“拖下水”,就一个劲儿地骂她老公,那话儿说得又刺耳又难听。
八一嫂这寡妇人心地特善良,她手里搂着个两岁的小家伙,赶紧走上前去劝和:
七斤嫂,别计较了。咱们都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谁能预见将来的事儿呢?就像你之前说的,七斤嫂,没了辫子也不见得就丑嘛。再说了,官府的大老爷们到现在还没发话呢。

八一嫂完全是出于好心,说的话也挺到位,挑不出啥错来。
八一嫂觉得,到了这地步,抱怨也没用了,再说这事也不能全赖七斤。记得七斤刚剪辫子那会儿,七斤嫂自己也说过,“没辫子也不见得难看”,那又何必老揪着七斤的辫子不放呢。
另外,虽说现在大家都在传“皇帝又坐上了龙椅,还想恢复留辫子”,但这种说法终归只是传言,官府那边也没贴出什么告示,说不定事情不会演变得那么糟糕。
七斤嫂一心想撇清自己,听完那话,脸立马就拉下来了:
哎呀,这话可真让人诧异!八一嫂,我自个儿觉得我还清醒着呢,咋能说出这么离谱糊涂的话?那时候,我可是实实在在地哭了足足三天,大伙儿都瞧见了,就连六斤这小家伙也跟着一块儿哭呢……
最后,他居然拿起一根“怒气冲冲的棍子”,朝八一嫂就打了过去:
“谁让你来插嘴了!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小寡妇!”
在这个过程中啊,咱们得说说——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整个流程里,你得明白——说起来也挺简单,就是在这一步一步的操作当中——看吧,就是在这个环节里头,事情是这样发展的——反正就是这么个过程,咱们一步步来看,会发现——按这个步骤走,你会发现其中的奥秘,这个过程真是——反正从头到尾,这整个经历就是——说来说去,整个事儿的关键步骤就在于——你瞧,从开头到结尾,这个流程它就是这样展开的——反正就是这么个道理,在整个过程中,你得注意到——
七斤嫂用筷子轻轻一点六斤的脑袋,喊饿的六斤手一滑,空碗掉地上摔出了个小口子。七斤一看这情形,火就上来了,从凳子上猛地站起来,捡起碗仔细瞧了瞧,发现碗真破了,气得他大骂一句:“真是的!”接着,一巴掌就把六斤拍倒在地。
旁边的赵七爷,本来因为那个逼他剪辫的“对头”七斤要倒霉,正得意洋洋,满脸笑容呢。可八一嫂突然冒出一句“衙门还没发告示”,这让他心里不痛快了,立马转头就开始怼八一嫂。
八一嫂本想好心劝和,结果却被两边的人一起指责,气得她全身发抖,憋屈地就走了。

有意思的是,旁边那些围观的人,竟然觉得“八一嫂”是多管闲事,压根没去琢磨她说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七斤嫂拿起“恨棒”就朝八一嫂打去,赵七爷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对着八一嫂就是一顿指责。而那些看热闹的“看客”呢,宁可围着看戏,听赵七爷在那瞎忽悠,也不愿搭理八一嫂那些冷静的分析。说到底,这背后的原因就一个:
八一嫂是个没了丈夫的女人,在村里头算是数得上的低收入户。
咱们当然可以讲,这些人对八一嫂的“瞧不起和打压”,是因为被封建老一套害得不轻。但往深了琢磨,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心里头穷得慌,就专门挑软柿子捏,欺负那些比他们弱的。这反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冷淡、疏远,还有对人家苦难的看不起、不屑一顾。
在这儿,鲁迅想要抨击的就是那种“国民劣根性”,说白了就是“看到羊就以为是狼”的心态。
有些人遭遇的苦难,表面上看像是碰巧摊上的倒霉事儿,比如说八一嫂成了寡妇,还有《祝福》里那个祥林嫂,儿子被狼叼走了,但她们心里头真正的苦,其实不是因为生活难熬,而是被“身边人就像地狱一样”的精神折磨给闹的。
在物质匮乏的时候,精神也会变得贫穷,这样人们就容易丢掉最基本的同情心,不再关心身边的人。甚至,当一个人遭遇不幸,他可能会遭到周围人的疏远和嘲笑。

在这种环境里,鲁迅深深地感觉到,那些人的痛苦被大家排挤、忽视,他们周围的人对更弱小者的苦楚充耳不闻,甚至有人还因为能欺负比自己更弱的人而得意洋洋,觉得自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指责更弱小的人,心里还挺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祥林嫂,她儿子被叼走了,周围人不仅不同情,反而还嘲笑她。还有孔乙己,科举没考上,穷得叮当响,却被“短衣帮”的人挖苦讽刺。八一嫂呢,丈夫死了,孤儿寡母的,还要被人骂作“偷汉的小寡妇”。再说阿Q,他被欺负得够惨,只能靠那种“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
【“奴性”之见狼是羊】
在《灯下随笔》里头,鲁迅先生深沉地记录道:
世间万物,各有差别,分着高低贵贱。你要是被人欺负了,其实你也有机会去欺负别人;要是你被人占了便宜,那你同样有机会去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咱们老百姓的“性子”,说白了就是“顺从心”。
很多人觉得,“奴性”就是说一个人“被当奴隶当久了”。这话没错,但其实这只是“奴性”的冰山一角,没讲全。
许子东在聊到《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时,他说了说“奴性”得满足的三个要点:他说啊,第一呢,就是得有那种被人使唤、不反抗的心;第二,就是得习惯听别人的,自己没啥主见;第三,就是得甘愿处于低人一等的位置,不觉得有啥不对。这就是许子东对“奴性”的三个看法,挺直接也挺到位的。
在生活中得使劲儿找乐子,发现那些值得夸赞的事儿,去好好感受,好好享受。很多人觉得,这就是“过惯了苦日子”的表现。
有的人啊,碰到比自己厉害的就怂得跟羊一样,任人欺负;但一转身,对弱小的人就凶得跟狼似的。这不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嘛,也就是大家说的“奴性”表现。
起床后呢,心里也琢磨着想当老大,也想有属于自己的小跟班。这事儿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头,表现得特别突出,咱们留到文章最后再来细说。

再聊聊《风波》里头,八一嫂被刁难那会儿,她那“看羊成狼”的倒霉事儿已经明摆着了。反过来,大伙儿对赵七爷那股子“见狼当羊”的劲儿,也是表现得明明白白。
赵七爷呢,是七斤隔壁村茂源酒馆的大掌柜,他还是这周围三十里地界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学问也是顶呱呱的。
村里的人,对赵七爷那叫一个敬重,原因嘛,就两个。
赵七爷他真的就算得上高贵吗?
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
鲁大爷曾把他的酒店砸了个稀巴烂,他却只能憋着不敢吭声。他说的那点学问,也就仅限于知道五虎将的名字,还有“黄忠叫汉升,马超叫孟起”,这些知识都是从赵七爷那引以为豪的藏书里学来的,就是那套金圣叹批注的《三国志》。但其实啊,金圣叹哪批注过《三国志》,他批的是《三国演义》才对。

这么说吧,赵七爷其实并不算是那种老派的、死守封建规矩的“保护者”或者“占了便宜的人”。他啊,就是比周围的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稍微霸道了点儿,就这么简单。
所以,村里的人都使劲浑身解数去巴结他。
赵七爷一出现——大伙儿的目光立马就聚焦到他身上了。他迈着步子,缓缓走进来,那派头,就像是村里的老大哥回娘家一样自然。赵七爷这名字,一提起来,村里老少谁不知道?今儿个,他又带着那股子特有的气势,走进了大家的视线。没有啥花哨的开场白,赵七爷往那儿一站,就是焦点。他的眼神,犀利中带着几分和蔼,让人一看就心里踏实。村民们私下议论的事儿,到了赵七爷这儿,总能找到个说法,仿佛他就是那能解决一切疑难杂症的活神仙。这次回来,赵七爷肯定又是带着啥新鲜事儿,或者是要给大伙儿指条明路。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跟着赵七爷走,准没错。这不,连平时爱凑热闹的孩子们都安静下来,瞪大眼睛,生怕错过赵七爷说的每一个字。赵七爷的出现,就像是一颗定心丸,让村里原本有些浮躁的气氛瞬间平稳下来。大家都知道,有啥事儿找赵七爷,保管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让你心里豁然开朗。
大伙都站了起来,用筷子敲敲自己的碗,热情地招呼着:“七爷,来咱这儿一块儿吃点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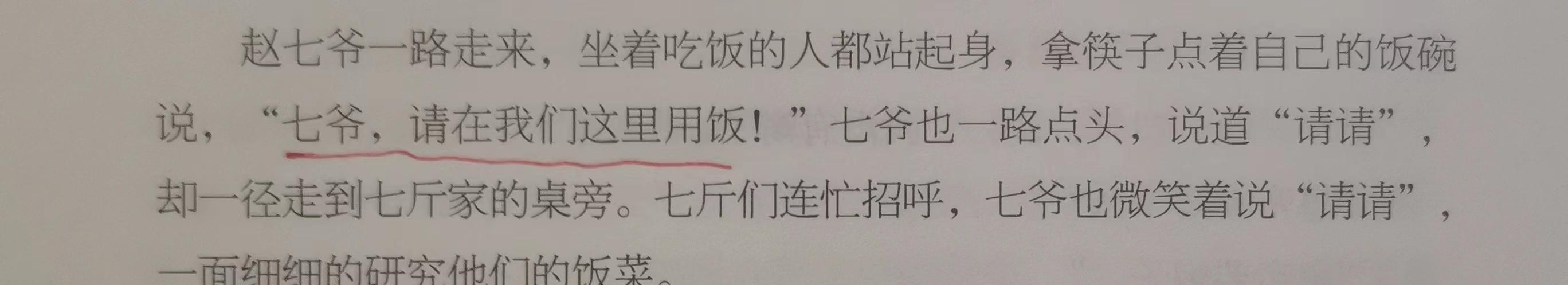
碰到家里那位厉害得很的七斤嫂,连带着家人、丈夫还有八一嫂都得忍让三分。但在赵七爷那股子威严下头,七斤嫂也不敢太放肆,只能憋着不敢多吭声。
看看村民们对待赵七爷和八一嫂的态度,那差别可明显了,简直就是欺软怕硬的典型“奴性”表现。对赵七爷,那是一个巴结讨好;对八一嫂呢,却是另一副嘴脸,欺负人家。这“媚强凌弱”的性子,一眼就能看出来。
明白了这种“顺从”的性格后,再瞅瞅那些物质和精神上都挺匮乏、变得呆呆的人群,也就能懂为啥现在社会底层的人有时候会相互为难了。
【结语】
1991年2月那期的《鲁迅研究月刊》里头,周海波聊起了《风波》这篇作品,他是这么说的:
那些不那么看重信仰,更关心生存的人们,在自己的平淡无奇日子里,像没了魂儿似的,反复经历着“没事干就瞎折腾”的无奈。这种情况挺普遍,算是人们常碰到的人生难题。鲁迅也是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体会中,慢慢理性地看到了这一点。
用“信仰”来剖析精神层面和“国民性格”这样的视角,确实挺值得夸奖的。
特别是,换个角度看,能帮我们摒弃长久以来的一个“误会”——每当说到鲁迅写的“庸众”,大家总会把他们想成是那些被打上“无知”“守旧”“跟不上时代”等烙印的、没有灵魂的人。
鲁迅的批评,目的是想让人觉醒,不是为了给人乱扣帽子或者只是冷酷无情地指责。

读鲁迅的文章,咱们得深挖细想:他笔下那些事儿背后,藏着的是啥样的思想性格,还有这些性格是咋来的。
经常听到有人这么说,觉得“国民性格”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因为东西不够,钱包瘪瘪。
对于这事儿,我嘛,也就认可一半。
《管子·牧民》里头说了:“粮食满仓,人才懂礼貌;衣食无忧,人才知荣辱。”但话说回来,要是把精神上的事儿全赖到物质头上,是不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

说说现在这个时候吧,生活条件那是嗖嗖地往上涨,但咱们的精神层面呢,有没有跟着一起提升啊?
网上那些层出不穷的“丑事”,仿佛在悄悄告诉我们:人们的精神和文明状态,好像正面临着“走下坡路”的风险。
我琢磨着,鲁迅先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他咋会在《阿Q正传》里头,专门写那段让人琢磨不透的“土谷祠里的梦”呢。
可怜的阿Q,在梦里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一翻身,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同样过得不咋地的小D出口恶气。整完小D后,他脑子里又冒出抢钱、抢女人的念头……这事儿说起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阿Q在梦里是痛快了,可他那报复的对象和后续的想法,却还是离不开身边那些同样受苦的人,还有那些世俗的念头。哎,这阿Q啊!

这么说吧,其实问题的根子,不一定在物质上,更多的是心里头那股子“老毛病”——就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留在咱们骨子里的那种“国民性格”里的“顺从”。
所以,在《大江大河》这部剧里,阿耐写下了这么一句挺让人琢磨的话:“那些从农奴翻身的人,说不定也会变成恶霸呢。”
卿心君悦,看看别人的经历,过好咱自己的小日子。文字里头找温暖,暖你,也暖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