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编辑:nirvana
第一章有时候,我觉得“乞丐”这个词挺不公平的。说到底,谁又不是呢?
有人跪着讨饭,有人站着讨生活,有人坐着讨人喜欢。
你说现在是不是同样整天在讨这讨那:讨房东宽限一周房租,讨老板多给点奖金,讨客户别再跳单?
所以有人活成了讨钱专家,有人活成了讨命高手。
日子讨着讨着,我们就不叫“乞丐”了,换了个体面点的名字,叫生活玩家。
当然,有些人讨得高端,比如求点赞的朋友圈文案,第一句话写得比抖音文案还扎心;
还有些人讨得古怪,比如搞拼多多砍一刀,把亲戚朋友砍得没耐心了,最后自己花钱买刀谢幕;更有些人讨得直接,把一生都写进直播间的苦情剧本,赚一笔算一笔。
要我说,讨生活从来不是羞耻的事,它是人类的本能。
你可以骂别人没尊严,但你骂不出别人的胃酸和体力透支。

所以,讨饭是门艺术,是种哲学。艺术和哲学不好学,但活着的人总得边讨边学。
这种事情也不是什么现代人的独创,丐帮这种事情,古人玩得透彻,我们不说洪七公,不说乔峰,我们今天来说说一百多年前的旧广州的一帮“职业讨饭人”,这帮人厉害,把“乞讨”做成了生意,还搞成了一个规模化的行业。
他们有组织、有分工、有江湖规矩,甚至还有自己的“企业文化”。
他们就是广州街头臭名昭著的“关帝厅人马”。
先说说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你以为乞丐就是蹲墙角的可怜虫?那是你没见过“关帝厅”的排场。

他们的地盘可以覆盖整个广州城区,街头巷尾,摊位市场,哪怕是一场葬礼或婚宴,都可能有他们的影子。
这么说把,如果你是个普通的乞丐,想在“关帝厅”辖区讨口饭吃,你就先别急着端碗,你娃得先交两块大洋的“入厅费”,再领个锡葫芦挂在胸口,这才算拿到“营业资格证”。
而且他们讨饭,还讲究门面功夫。
衣衫褴褛本来是乞丐的标配,够了吗?对不起,还不够资格,高端的你得学会穿戏服站街头演大戏,或者拿块臭肉敷在腿上装瘸子,或者抱个从别人家租来的孩子扮“落魄母亲”。
他们还分不同的“业务类型”:装病、装死、卖艺、哭丧、吓唬人——每一项都有专业培训和技能考核,行乞的礼貌用语甚至都经过严格审核。
更夸张的是,这帮人有完整的“公司式运营”:讨来的钱按照“帮规”分成五份,小弟拿三份,丐头拿一份,剩下一份用来“打点”段警。

年终的时候,还有个特别规矩:广州城内有喜事的人家,得主动备上一桌酒席,请丐头喝一杯庆贺,剩下的菜全给他端回去给手下人吃,规矩摆得明明白白。
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些“职业乞丐”已经够离谱了,但如果没提到一个人,这个故事就少了灵魂人物。
他就是“关帝厅”的初代大佬——陈起凤。

陈起凤是个什么人?
这么说吧,这哥们绝对是传奇人物,他愣是在广州把一帮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变成了一群有规矩、有面子的“职业讨饭人”;
你要再往高处抬举,那他也是个旧社会的“草根资本家”,懂地盘、懂规则、也懂怎么讨好别人。
陈起凤是哪里人,如今已经无从查询,只知道他是在光绪年间带着一帮流浪汉闯进广州的。
他的逻辑简单又管用:“别人的富贵是富贵,我的地盘才是根本。”
他不是最有钱的乞丐,但他是最有脑子的乞丐。
在他来之前,乞丐人员主要集中在广州城西一带,那时也有一些互不统属的头目,住在西关洪圣庙、文昌宫、孔子庙、湄州寺、莲花庵等寺庙,而总头目住在华林寺里面,而且总帮主还是世袭制的。
陈起凤来到广州后,也是从城西起家的,这哥们确实有点能力,最基本的本事,能打!

而且据说他的功夫还是少林派的,所以这么一来,不但他手下都懂些拳脚功夫,而且陈起凤还和城西这边的武馆产生了联系。
这么一个人,做到了乞丐界的大哥大,靠的是狠、准、稳三板斧:狠在打破江湖规矩,准在挑选门徒收地盘,稳在建立规则上让所有人信服他。
接下来,我们就聊聊陈起凤的发家史,聊聊他如何用一碗讨饭的故事,搅动整个广州的江湖风云。
第二章陈起凤的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从外地漂泊到广州的流浪汉,硬是在一个到处都是人的地方,划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能做出这种事,靠的无非两样东西:拳头和脑子。
他的发家史简单到让你怀疑人生:没有英雄救美,没有被贵人提携,也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传奇。他的崛起,是一场漫长的拔河——左手拽着地盘,右手拽着人心。你以为他和别人一样是个普通的乞丐,实际上,他早在讨第一碗饭的时候,就不是来讨饭的,他是来讨江湖地位的。
开局只有一双脚,他先讨了个地盘

陈起凤第一次踏进广州城,走到西关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传说他当时在华林寺门口看了很久,心里盘算着要不要进去借宿。进是进了,没人赶他,但他很快发现,寺庙虽然是穷人的天堂,但它从来不是没有规矩的地方。
乞丐多了,地盘就显得金贵。寺里的地盘,早就有本地的老丐头占着。他们吃肉喝汤,分剩饭剩菜给新来的,规矩是:你要吃这口饭,就得叫老大。换句话说,哪怕你是来讨饭的,也得先交“保护费”,这规矩让陈起凤看得眼热——他没带几天,脑子里就开始琢磨:“这事能不能换个我来做?”
拔河的第一步:搞定“人”
打只能证明你有匹夫之勇,陈起凤真正的手段是“结交人心”。他发现,本地的乞丐其实没多少技术含量,吃完上顿愁下顿,活得散漫而没有目标。靠着一张嘴,他从和这些人套近乎开始:
“吃剩饭算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吃上桌菜?”
“规矩是别人定的,凭什么我们不能改规矩?”
陈起凤很会挑时间和场合。他等着老丐头们喝醉的时候,把几个能打的流浪汉拉到一起,私下给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这个地方很大,地盘也很多。我们如果不主动抢,就永远只能分别人剩下的。”
那帮人听了很服气,觉得陈起凤是个明白人,跟着他出去到更远的城西转了一圈,果然发现还有空着的庙——关帝厅。所以后来他的人马被江湖上称为关帝厅人马。
拔河的第二步:抢到地盘并守住它

人心拉拢到手之后,陈起凤带着这帮人,果断选择了“出走”——不是为了浪迹天涯,而是去抢城西的一片空地。
当时,这片地方靠近华林寺边缘地段,没人去管,属于半荒废的地盘。陈起凤带人进驻后,用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办法:“谁想进来讨饭,先叫我们一声爷,送我们一顿饭。”
这听起来像个无赖做派,但对流浪汉来说很有吸引力:大哥既然能抢地盘,那就有能力护住我们这点可怜的饭。慢慢的,原本散漫的流浪汉们一个个自愿入伙,整个城西一带的乞丐逐渐集中到了陈起凤的名下。
陈起凤的成功不是靠抢,而是靠“抢了能守住”。他有两张“底牌”让其他丐头不敢轻易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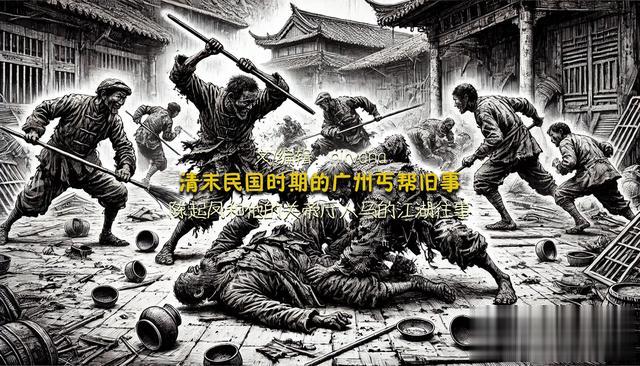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的第一张牌,他会些功夫,而且有武馆的朋友。他的手下稍微学得能出腿抡拳的,就能在地盘上立威。
这套打法,别说对付普通的乞丐,就是有心惹事的地痞,也不敢轻易动他的人。
第二张牌比打更重要,那就是把“地盘”变成“饭盘”。陈起凤设了一个特别的规矩:凡是入伙的乞丐,每日的讨饭钱都要按比例上交,他再负责从每人头上抽点钱,统一办一顿热饭,谁都能吃饱。乞丐其实没有太多奢求,吃饱就比什么都强了。久而久之,这套“丐帮管理制度”让陈起凤的势力范围越扩越大。
拔河的终点:打破世袭制,做唯一的大佬
陈起凤混了几年,名声渐渐在广州乞丐圈传开,连其他几个老丐头都不得不承认,陈起凤这人有本事。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原本的“丐帮世袭制”。以前,乞丐界的头目是家族传承,但陈起凤靠人多、靠地盘硬抢下了这块权力,这也让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新规矩:“谁有本事,谁当老大。”
从此,广州的乞丐界,就以陈起凤为中心,慢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你可以说他是流浪汉里的开创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幸存者。
陈起凤有句经典的话:“我不求发大财,但我要吃得饱;我不求别人仰望,但求别人听我的话。”这话听起来很普通,但它就是陈起凤成功的真相:他知道什么该争,什么可以不争。

所以我们说,陈起凤建立起这么一个庞大的组织,还能很有效率的运行,靠的绝对不是武力,也不是运气,而是一个朴素的生存逻辑:“人先能吃饭,才会听话;规矩定得合理,江湖才能长久。”
他不是在做乞丐的生意,他是在做一场比乞丐更大的生意。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关帝厅人马”的那些故事——他们是怎么靠着一碗饭吃出江湖地位的,又是怎么用“讨饭”的荒诞手段,把广州的街头巷尾变成他们的“表演舞台”。
第三章如果你以为乞丐的日常只有“跪地磕头喊好心人”,那只能说你低估了“关帝厅人马”的想象力。
在陈起凤的带领下,这帮乞丐早就甩掉了传统意义上的“沿街要饭”模式,转型成了一群手段多样、分工明确的职业讨饭人。他们的职业化程度,放到今天,也能算是“讨饭界的高配创业公司”。
KPI很严:讨饭也是门精细化管理
“关帝厅人马”作为一个帮派,最重要的资源是地盘,最重要的手段是规则。陈起凤从来不允许手下人在讨饭这件事上“胡来”。他制定了严格的行乞规则:
规则1:分区而治,绝不越界。

每个乞丐负责一个特定的地段,譬如西关的菜市场、河南的码头、上下九的繁华街道。谁在哪块地盘讨饭,赚多少钱,都是帮派内部安排好的,越界是大忌。新来的乞丐想讨饭,得先交“入厅费”,还得按月缴纳“地盘税”。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特许经营体系”。
为了杜绝越界混乱,陈起凤甚至发明了一套标志:早年是一个锡葫芦,挂在胸前,算是“会员身份牌”。后来锡葫芦取消了,但行乞范围的划分依然清晰——每块地盘都像写好了“用地红线”的街区图。外来乞丐如果硬闯地盘,轻则被赶走,重则可能遭一顿拳头。
规则2:技能匹配地段,讨饭也讲“战略部署”。
陈起凤深知,讨饭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乞丐的技能和地段匹配度。他在分配人手时,特别注重“人岗适配”。举例来说:
在上下九那种富人扎堆的地方,安排了一批“能唱会演”的乞丐,比如穿着戏服唱粤剧、讲古仔的“地上佬馆”;

在人流量大的菜市场附近,派上装惨卖惨的“假残疾人”,譬如腿上敷块臭肉,拄着拐杖行走的“装假狗”;
在码头和茶楼,安排那些靠嘴皮子讨钱的乞丐,比如唱莲花落和“数乐宝”的盲人乞丐。
每个人都有明确的KPI,讨不到钱的,轻则被罚一天没饭吃,重则直接被踢出组织。“不敬业、不努力的乞丐,连同行都瞧不起。”
专业乞讨手段:把讨饭做成“艺术表演”
关帝厅的门人,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他们五花八门的讨饭技能。一个词形容就是:凡是能讨到钱的手段,他们都愿意试试。
(1)收长租:死缠烂打型讨饭

收长租的乞讨方式,最符合“丐帮”原教旨主义的风格:唱、哭、喊,一直耗着你不给钱不走。比如:
你在铺子里做生意,门口来了个唱粤曲的盲妹,唱完一整段《帝女花》后,递过碗来说:“老板,个仙(仙:铜币)啦,好心啦。”
你不给?没关系,她还会唱第二段,直到你耳朵快炸了,给钱打发她走为止。
有时候,他们还会搭配小道具表演,譬如“打花鼓”、“抛砖”、“翻筋斗”,让你觉得不打赏实在过意不去。
这套路听起来不像艺术,更像一种荒诞的“心理拉锯战”:你想走开,他们用唱、哭、喊缠着你;你想清净,他们偏偏不让。关帝厅的人不懂艺术,他们懂的,是如何把你逼到掏钱止损的地步。
(2)装假狗:最经典的“卖惨”技法
“装假狗”是关帝厅人马的经典讨饭套路,流程听起来简单,但细节上颇见功夫:
找一块牛肉,放进臭水沟里泡几天,等它发臭、变色,再贴到自己的腿上或手上;
找条烂绷带把这块肉绑住,装成“重度感染的伤口”,然后满街走,嘴里念叨:“可怜吓啦,好心救命吓啦。”
有些“装假狗”的老手,甚至会演出自己“伤口溃烂、行走困难”的样子,跪着用手爬到人家面前,像狗一样。广州的行人怕被追着不放,怕臭味沾身,大多会掏几个铜板扔给他们,求个清净。
如果你以为“装假狗”只是无奈,那你就错了。这是门学问。臭肉泡的时间太短,别人会觉得假;泡的时间太长,臭味太大又容易露馅。
能把这门手艺做到“骗到钱且不被举报”的,才是真正的高手。
(3)地上佬馆:街头戏班讨饭的鼻祖

最有艺术气息的乞丐,是那些穿着破旧戏服,在街头表演粤剧的“地上佬馆”。他们是老戏班的“失业演员”,拿几件从戏院捡来的旧衣服,凑合成了一个“移动戏班子”。
演的戏无非是老一套,比如《包公审郭槐》《薛刚打太庙》。有时候,戏服破得连背后的绑带都系不上,看着让人心酸。

演出结束,他们站在人群里拿碗转一圈,一边收钱一边客气地说:“多谢老板,多谢奶奶。”
这些人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乞丐,他们对粤剧的感情是认真的,只不过,表演完戏后,他们连台阶都下不去,直接就地把“剧终”变成了“乞讨开始”。
(4)哭丧:利用封建迷信的“特殊技能”
如果说以上的讨饭方式还算正常,那么“哭丧”这门手艺就完全是旧社会的荒诞操作。
关帝厅人马会在附近富户家有人去世的时候,强行派人去送“香花冥烛”,一边摆阵一边跪地磕头,最后不忘说一句:“老爷,给个香油钱吧。”如果丧主不给,他们可能直接在墓地上嚎啕大哭,甚至威胁说:“不给钱,我们就天天来哭。”
这套“敲诈式讨饭”的手段,让人哭笑不得,却因为封建迷信的背景有了市场——在旧广州,“不送香油钱,丧事不圆满”这种说法很普遍。丧主为了图个吉利,最终都会选择破财消灾。
3. 丐帮“企业文化”:道义还是生意?
关帝厅的人虽然看起来像一群毫无底线的职业乞丐,但他们的“企业文化”却体现出一种诡异的江湖规矩。
比如:
如果帮派里的成员病了,组织会安排人送医看护;
如果乞丐去世,陈起凤会亲自派人抬棺下葬,甚至组织“乞丐送殡团”,仪式感拉满;
大年初一,陈起凤还会给地盘上的所有乞丐发“喜钱”,算是一种过年的福利。

这一套“管理制度”,让关帝厅成为乞丐中的“避风港”。对于那些失去一切的底层人来说,加入关帝厅意味着至少能吃口饱饭,活着有个盼头。
但反过来,这些人讨来的每一分钱,也被帮派牢牢地掌控。
道义和生意,总是共存于这个江湖里,谁也无法分清界限。
在关帝厅的江湖里,乞讨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它被陈起凤改造成了一个荒诞又细致的行业。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向生活要饭,有人靠表演,有人靠卖惨,有人靠坚持不懈的死缠烂打。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这个“丐帮”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故事,看看它是如何从一个庞然大物,一步步崩塌成散沙的。
第四章陈起凤之死:地盘不会永远属于谁

称为丐帮帮主后的陈起凤,个人生活在当时的社会可以说是相当土豪的,他住在华林寺的一周精舍里,有几房妻妾,分住在附近的民房,他常穿着纱稠衫裤,大金链大金表,裤头还挂上了许多古玉,手执长烟筒,有时要登门向人道贺时,则另有长袍马褂,俨然阔商富户。
当冬天到来的时候,陈起风嗜爱狗肉,常率其門人到河南(广州人说的河南是珠江以南的市区)隔山一带,大吃香肉(在广州,狗肉一名香肉),食必尽一大肥犬,并邀当处的地头有同嗜者大醉而归。
江湖总是这样,繁华的时候风光无两,破落的时候满目狼藉。没有什么比“盛极而衰”更能概括“关帝厅人马”的结局。
陈起凤是个聪明人,他明白所有江湖都靠规矩活着,但他没想到,规矩久了会腐。规则是地盘,规则也是枷锁。关帝厅撑起的,是广州城一帮最底层的流浪汉和乞丐。他们有体面的讨饭方式,有固定的分赃制度,甚至还有年终分红和“丐帮版医保”。
这一切在陈起凤活着的时候,运行得像一台齿轮紧密的老式钟表,每一个零件都听从指令,准时转动。
但问题在于,老式钟表一旦少了上发条的人,齿轮就会生锈,就会卡死,就会分崩离析。

陈起凤死得不算突兀。一个活得豪气的人,葬礼也相当风光。他的葬礼热闹得像一场江湖盛宴。 门徒们倾尽全力凑钱办了一场排场巨大的“丐帮式大典”。
抬棺的路上锣鼓齐鸣,几个丐头亲自披麻戴孝,所有人按江湖规矩围着他的棺材转了三圈,算是给这位曾经的大哥最后的尊重。
最夸张的是,这场送别的队伍,竟然在他的地盘上绕了整整一圈——从华林寺走到河南金花庙,沿途围观的路人越聚越多,到最后整个广州城都知道了:凤爷走了,但“面子”还在。
规则失灵:地盘混乱,忠诚消失
然而,人一走,茶就凉。关帝厅表面上有一整套规矩和章程,但这些东西的根基不是制度,而是陈起凤个人的威望。
他活着的时候,这个体系井井有条;他死后不到三个月,整个“厅”就乱成了一锅粥。最先乱的是地盘。
江湖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佬死后,小弟们要么集体忠诚,要么集体造反。关帝厅的人没想造反,但忠诚也谈不上。他们对大佬死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地盘谁管?陈起凤留下的地盘实在太多,老城有,西关有,河南还有。

每一个片区的乞丐头目都觉得自己有资格“接管”这些地盘,但每个人又都知道,谁先动手,谁就会被当成众矢之的。
所以,为了这块地盘,这些曾经的兄弟先是互相戒备,后来直接开始打架,谁也不服谁,争地盘争得头破血流。
地盘争了三个月,关帝厅的核心组织就已经散了。每个区域的乞丐头目都各自为王,开始自立门户。
他们保留了“入厅规矩”,却不再接受任何统一管理。
更荒唐的是,地盘分得越小,争执却越多。

过去,广州的街头巷尾分工明确,乞丐们互不干涉;陈起凤死后,这些规则逐渐被抛弃。比如小北一带的乞丐跑到河南行乞,河南的乞丐不乐意,几句话不对付,就可能演变成街头斗殴。
广州城的地盘多,但大大小小的地段争夺,却越来越像无头苍蝇乱撞,混乱不堪。
最典型的故事是“锡葫芦”的废弃。
陈起凤时代,每个乞丐胸前挂着锡葫芦,象征自己的“入厅资格”和“地盘归属”,谁都不敢造次。
可陈起凤死后,地盘乱了,锡葫芦也没用了。
新来的乞丐发现,这块地盘的头目收两块大洋,隔壁地盘的头目收一块大洋,收费标准不统一,标志也不统一,慢慢地,大家干脆都不挂了。
锡葫芦的取消,让关帝厅最后一丝“秩序感”也荡然无存。没有了标志,乞丐和乞丐之间不再认“身份”,只认拳头,谁打得过,谁占地盘。
外部冲击:政府管制与时代巨浪
丐帮的内部在腐烂,外部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清末民初的广州,社会变得愈发复杂。

城市的街道变多了,政府的管理也逐渐跟上,街头上的乞丐再也不是没人管的“灰色地带”。最早的一批“丐头”发现,街上突然多了警察——这些人不像段警那样吃黑钱,而是会真刀实枪地驱逐乞丐。
政府后来甚至要求每个区域的“丐头”登记备案,乞丐的行乞活动被一刀切地控制住,所有人都觉得不自由了。
更大的冲击来自时代本身。
陈起凤的地盘逻辑,建立在乞丐的数量稳定的基础上,但从清末到抗战爆发,大量的外省难民涌入广州,乞丐人数急剧增加。
1934年,社会局的一份报告统计,广州城里的乞丐人数超过了五万,而到了抗战时期,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地盘没变,人数却成倍增长,乞丐和乞丐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在意什么规矩?
曾经的关帝厅就像一艘巨大的旧船,尽管有破洞,但还能在陈起凤的带领下勉强漂浮在水面上。
可陈起凤死后,这艘船开始下沉,水涌进来,洞越来越多,最终完全崩塌。那些江湖规矩被一点点撕碎,江湖气变成了生存的肉搏,关帝厅人马从一个庞然大物,变成了散沙一片。
关帝厅的结局:没有人能幸存于江湖之外

到了抗战后期,广州城已经没有“关帝厅”的影子了。旧社会的乞丐再多,也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偶尔还有人记得陈起凤的名字,但提起他,语气里更多的是感慨,而不是敬畏。
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是混乱的故事,是荒诞的规矩,也是一些人性里的挣扎和无奈。
江湖散尽,但讨生活的规则从未变过关帝厅人马的故事结束了,可“讨生活”的戏台从来没有散过。
广州的街头巷尾不再有乞丐胸前挂锡葫芦,可工牌、KPI、年终奖……
这些现代规矩,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讨饭”吗?
今天没有丐头了,可每个上班族都有自己的“老板爷”;今天没有喜钱了,可年会上的红包,发得比当年陈起凤的还敷衍。
生活的核心命题从来没变:人活在世上,讨饭也好,讨老板赏脸也好,讨的都是一个能继续活下去的资格。
过去,关帝厅的乞丐靠规矩活着;今天,我们靠“职场规矩”活着。
过去的乞丐分地盘讨饭,今天的打工人拼资源抢项目。
过去有陈起凤教兄弟们“规矩吃饭”,今天有老板教育下属“为团队奋斗”。生活的方式变了,挣扎的本质没变。
但仔细想想,关帝厅的人至少还有一种江湖气:有问题当面拳脚解决,有争斗直接划地盘抢,赢了地盘就坐下吃饭。
可今天的我们,为了争一个订单,抢一个名额,活成了一群键盘侠、社交场上的表演者,争得拧巴,争得疲惫,争得连敌人都懒得正眼看我们。
江湖的规矩散了,可“讨饭”的艺术一直在。这既是生活的荒诞,也是生存的真实。
所谓江湖,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靠人活着,但活不过人。
参考文献:
王楚夫:广州乞丐集团——关帝厅人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