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 12 月,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雪粒子,恶狠狠地砸在坦埠镇的青砖墙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地主李子厚的宅院里,气氛紧张而压抑。

管家弓着腰,带着几个下人正神色匆匆地往地窖搬运粮食。李子厚站在一旁,眼神中透着几分得意与贪婪,他看着这些粮食,仿佛看到了自己牢牢掌控的财富和地位。
这个拥有全镇七成田产的大户,在饥荒年月竟将三千斤小麦深埋地下,丝毫不顾百姓的死活。院墙上新刷的 “减租减息” 标语,被石灰水覆盖得斑斑驳驳,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李子厚的抗拒。
刘锡琨带着警卫员神色凝重地蹲在镇公所里,桌上摊着三份截然不同的账册。他眉头紧锁,眼神在三本账册间来回扫视。
农会提供的租佃记录、李子厚上缴的 “减租清册”,还有地下党员李秀兰从李家厨房灶膛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扒出的真实账本。三本账册一对照,李子厚的恶劣行径便暴露无遗。他通过 “虚报田亩数”“伪造借据” 等手段,实际收租量比战前增加了三成。
“这个李老爷,把《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当擦屁股纸了。” 刘锡琨翻着账册,嘴角浮起一丝冷笑,心中满是愤怒。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李子厚次子李继宗在账本上的签名,那字迹工整有力,与伪造借据上歪歪扭扭的佃户手印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让刘锡琨心中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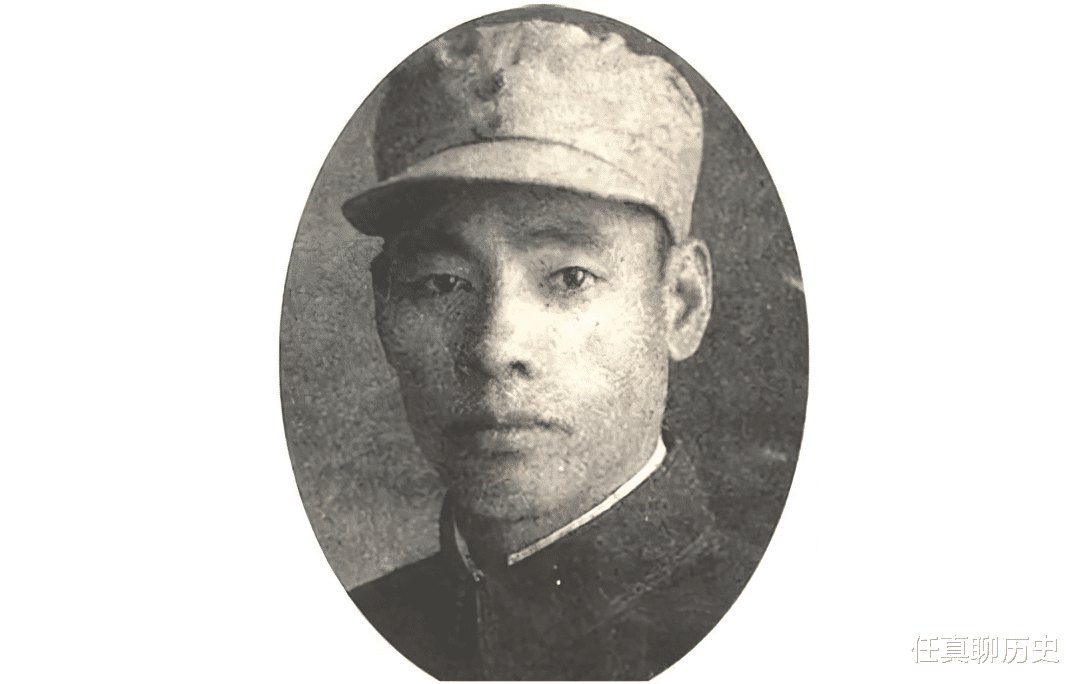
腊月二十三小年,刘锡琨带着武工队迅速突查李家祠堂。祠堂里,满屋族老正襟危坐,神色各异。刘锡琨深吸一口气,稳步上前,当众播放了秘密录制的蜡筒录音。“八路军要减租,我们就加秤”,李子厚与维持会长密谈时那阴狠的声音在祠堂里回荡。
族老们听闻,不禁交头接耳,面露惊讶与不满。更致命的是,刘锡琨不慌不忙地出示了李继宗提供的分家文书,目光看向李大少爷,不紧不慢地说道:“李大少爷,令尊把西跨院三十亩好田都给了三姨太生的幼子,这事您不知道吧?” 李大少爷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狠狠地瞪了一眼李子厚。
李子厚当场瘫坐在太师椅上,脸色惨白如纸,他怎么也想不到,八路军竟能如此巧妙地利用家族矛盾打破这看似铁板一块的局面。原来,刘锡琨早通过私塾先生王守谦,细致入微地掌握了李家内斗的情况:大少爷不满父亲偏爱幼子,心中积怨已久;三姨太的丫鬟正是农会秘密会员,在内部传递着关键信息。
当夜,李家粮仓被迫打开。刘锡琨站在一旁,指挥着将七千斤存粮中四千斤充作军粮,三千斤当场分给佃户。这个数字是他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的,既达到惩戒效果,又给李家留下过冬口粮。

最具创造性的处置在三天后。刘锡琨没有简单地批斗李子厚,而是深思熟虑后,让他担任 “减租减息促进会” 名誉会长,将其绑在抗日统一战线上。
起初,李子厚心中满是抵触,但随着形势发展,他逐渐意识到这是一条新的出路。
当日军扫荡队扑来时,这个昔日的铁公鸡竟主动献出二十匹骡马转移群众。后来在鲁中行署的《土改经验汇编》里,此事被总结为 “打击与团结的辩证法”,成为了一段经典的土改范例,启发着更多人在复杂的斗争中寻找平衡与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