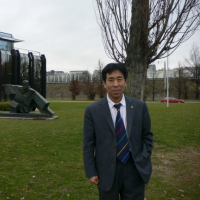听公司的小伙子说,如今冰雪运动火得不可开交,火得一塌糊涂。作为一个不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我实在难以理解那些痴迷于冰雪运动的爱好者,也无法完全体会各地方政府为打造冰雪旅游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但作为体育收藏爱好者,我曾亲眼目睹“冰墩墩”一物难求的盛况,也在媒体上见证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然而,无论冰雪运动如何火热,它终究受限于时间和空间。我一直认为,冰雪易消融,而藏品却能永存。

1953年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奖杯(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于1953年2月15-19日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举行)(李祥收藏)
冰雪收藏作为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故事和冰雪精神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自北京最早提出申办冬奥会以来,我已经举办了20余场大大小小的冰雪体育展览。当各地的文旅局长们为冰雪季的客流量欣喜若狂时,我也想提醒他们:真正能留住“冰雪热”的,或许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冰雕雪塑,而是那些能够被百姓珍藏于记忆抽屉中的温暖载体。

1955年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奖牌(李祥收藏)
当亚冬会在哈尔滨盛大开幕燃爆朋友圈时,联想到全国尚未建立一座正式的冰雪体育博物馆时(截至2024年5月18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全国博物馆名录6833家,没有冰雪体育博物馆),内心总会想起加拿大魁北克冰雪博物馆门前的那句铭文:“我们收藏的不是冬天,而是人类与严寒对话的勇气。”

在正文开始之前,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亚冬会的小趣事。这次亚冬会竟然吸引了所有七位国际奥委会主席候选人的到来(每位都获赠了北京祥体育博物馆的文创产品),这在区域性的体育赛事中实属罕见。这体现了他们对亚冬会的高度重视,也许更是为了自己不久后能够“上位”而杀出一条“雪”路。不管如何,来了就是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助力。
一、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冰雪文化历久弥新
“千年冰封,万里雪飘”,这八个字不仅生动描绘了中华大地上壮丽的冰雪景观,更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冰雪历史的深情回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冰雪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成为其独特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在新疆阿勒泰山村发现的老雪爬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不仅学会了如何抵御冰雪的严寒,更掌握了利用、观赏乃至嬉戏冰雪的技艺。追溯古代冰雪活动的足迹,我们可以发现,近2000年来,中外史籍中关于滑雪板及滑雪活动的记载颇为丰富。滑雪板的名称更是五花八门,如“蹄”、“木”、“木马”、“察纳”、“踏板”等,这些名称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从战国到晋代,《山海经·海内经》中便记载了“钉灵之国”,其民从膝以下生有长毛,擅长以马蹄般的步伐行走于冰雪之上。到了隋唐时期,《隋书·北狄传》则描述了室韦人因地处积雪深厚之地,为防陷入雪坑,而骑木滑行的场景。及至清代,“乌拉滑子”成为滑雪板的新称谓,其形如弹弓,系于双足,可在雪地冰面上疾驰,速度堪比奔马。

老登雪山木板铁钉鞋(李祥收藏)
在宫廷冰雪运动方面,宋代是冰雪运动兴盛的起点。《宋史》中记载了皇帝亲临后苑观赏冰嬉的场景。清代入主中原后,冰嬉不仅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还被纳入军事训练体系,乾隆帝更是将其誉为“国俗”,并载入《大清会典》。据史料记载,1625年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有文献记载的冰上运动会,进一步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与普及。

冰嬉图是一幅生动展现宫廷冰嬉场面的绘画作品。满清入主中原后,将冰嬉这一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带入内地,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盛况。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会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在冬至至“三九”期间于太液池上(今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进行表演。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为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便是根据这一盛况而精心绘制的。

1953年首届东北地区冰上运动大会银质奖杯(李祥收藏)首届东北地区冰上运动大会于1953年2月1-6 日在哈尔滨市八区体育场举行。
此外,冰床作为一种冬季冰上运输和娱乐器具,也在古代中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便较早记载了“凌床”这种器具。明代时,更是出现了十余个冰床并联在冰上豪饮壮游的现象。清代时,冰床的制作技艺更加精湛,有的还装有铁条以提高滑行速度。清代皇帝及达官贵人所用的冰床更是装饰豪华、防寒保暖,堪称“冰上游艇”。

1929年,北海溜冰场在成功的举办了溜冰比赛之后,又创办了化装溜冰表演比赛。新中国成立后,首届东北行政区冰上运动大会于1953年2月1日-6日在哈尔滨八区体育场举行,同年的2月15-19日,首届全国冰上运动大会同样在此举行,全国性的冰雪赛事极大地推动了冰雪运动的发展。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加速了中国冰雪体育活动的普及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人培养起“冰雪情缘”,选择冬季活动作为娱乐和健身的方式。
二、冰雪热潮:政策引领与市场共舞的欢乐颂
推动冰雪经济发展,政策“暖风”频吹。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202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12月,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推动东北地区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实施方案》。

20世纪50-60年代,“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滑冰玉雕(李祥收藏)
中国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强调,“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冰雪运动一定要全面开展”,“让冰雪运动进入寻常百姓家”,“把群众冰雪运动热情保持下去”。”这股席卷全国的“冰雪热”,正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成功落地的生动体现。

1954年《冬天到了·滑冰去》宣传画(李祥收藏)
从数据上看,中国冰雪运动消费市场规模相当可观,各类冰雪运动消费总额已经超过了1500亿元。而在最近的冰雪季,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范围内参与各类冰雪运动项目的人数高达5735万人,参与人次更是突破了1亿大关。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冰雪经济蓬勃发展、活力四溢的真实写照。

清代雪地皮靴(李祥收藏)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正全力推进冰雪经济发展,致力于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以冰雪资源“出圈”的哈尔滨,其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阿勒泰的冰雪民俗文化也日益受到关注;湖北、贵州等地巧妙融合民族风情与自然风光,打造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项目;而上海与广东则通过建设室内雪场,为南方地区带来冰雪体验的新可能……冰雪热潮在全国范围内涌动,冰雪“冷资源”正持续释放“热”活力,为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冰雪虽热易消融 文化遇冷需深耕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点燃了中国冰雪运动的热情。滑雪场、滑冰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冰雪旅游成为冬季消费新宠,冰雪装备制造企业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中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已突破6000亿元,预计2025年将达到万亿规模。但在这场冰雪经济的热潮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冰雪运动的文化内涵建设明显滞后于产业发展。

许多冰雪场馆重设施轻文化,游客体验停留在浅层次的娱乐层面,缺乏对冰雪运动历史、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一些地方在发展冰雪旅游时,简单复制国外模式,忽视本土文化特色,许多冰雪场馆缺乏文化展示空间,游客体验停留在浅层次的娱乐层面,对冰雪运动的历史渊源、精神内涵知之甚少。这种文化缺失导致冰雪运动难以形成持久吸引力,许多消费者将滑雪视为一次性“打卡”体验,而非长期坚持的运动习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老冰刀鞋(李祥收藏)
“冰雪虽热 文化遇冷”,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深层矛盾:重商业开发轻文化积淀,重短期效益轻长期价值。冰雪文化的缺失不仅导致产业同质化竞争加剧,更使得冰雪运动难以真正融入大众生活,形成持久的文化认同。从国际经验看,冰雪强国无不拥有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这种文化积淀既是产业发展的根基,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冰雪产业的发展,亟需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注重文化内涵的建设。通过挖掘传统冰雪文化、培育现代冰雪文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雪文化体系,为冰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延安时期,冬季的延河上,滑冰活动开展的异常活跃!延安《解放日报》有两次报道溜冰比赛,一次是1941年12月延安体育会筹备溜冰赛;一次是1943年2月延安溜冰比赛。1943年,延安各界为纪念“二七”大罢工20周年,在延安大学前的滑冰场举办了“延安溜冰大会”。此组照片上有“延安溜冰大会”字样,反映的是1943年延安时期,机关、学校及社会各界群众参加“延安溜冰大会”时的场景。
“冰雪易消融,文化需深耕”。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从古代冰嬉到近代“体育救国”理念下的冰雪实践,再到当代冬奥会的辉煌成就,文化积淀深厚,但这些历史记忆多以碎片化形式散落,缺乏系统性保存与展示。例如,延安时期延河冰场上的群众滑冰活动,不仅是革命年代的体育实践,更承载着“强种强国”的精神内核;而民国《图画时报》记录的北京冬季溜冰盛况,则映射了社会大众对冰雪运动的热爱与文化认同,这些历史细节亟需通过博物馆的集中展陈与教育普及,转化为当代冰雪文化的根基,从而真正实现“冷资源”向“热文化”的升华。
四、每个滑雪场都可以是一个博物馆
笔者看来,每个滑雪场都可以建一座冰雪体育博物馆,甚至,毫不夸张的说,每个滑雪场都可以是一座“原址冰雪体育博物馆”。“原址博物馆”这个名词是笔者的个人总结,就是在俱乐部主场原址或者场馆遗址的基础上建设博物馆。在全球冰雪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原址博物馆”为传统滑雪场与赛事场馆的转型提供了全新思路。它突破了传统博物馆的静态陈列模式,将场馆的物理空间、历史记忆与冰雪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活态化”的文化载体。这一模式不仅是对冰雪运动历史的致敬,更是一种可持续的遗产活化方式,兼具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的复合意义。

原址博物馆的核心在于“在地性”与“真实性”,与传统博物馆不同,其依托的滑雪场或赛事场馆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者:冰面上的划痕、观众席的欢呼声、运动员更衣室的私人物品……这些细节构成了场馆独有的叙事语言。例如,挪威霍尔门考伦跳台滑雪场在保留赛事功能的同时,将百年跳台改造成“冰雪运动历史长廊”,利用VR技术还原历届经典赛事场景,游客可通过穿戴设备“化身”运动员体验高空飞跃的瞬间。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鲜活记忆,使场馆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纽带。

在运营层面,原址博物馆能够有效破解滑雪场“季节性闲置”的难题。以加拿大惠斯勒滑雪场为例,夏季利用缆车站、赛道缓冲区等空间开设“冬奥名人堂”,展出历届奖牌、装备及运动员手稿,并开发主题研学课程,吸引家庭游客与学校团体,使淡季客流量提升40%以上。同时,场馆通过文创衍生品(如复刻版赛事海报、冰雪主题盲盒)与数字藏品实现二次变现,形成“文化IP+商业运营”的闭环。

新疆阿勒泰老滑雪板(李祥收藏)
更深层次上,这种模式能强化社区认同感。日本长野冬奥会场馆改造的“冰雪遗产中心”,定期邀请当地老人讲述赛事筹备故事,并举办青少年滑雪队训练营,使场馆成为凝聚代际情感的公共空间。原址博物馆由此超越了单一的商业属性,升级为区域文化地标与社群精神象征。

1932年《中国康健月报》,封面刊有文字我国妇女不健康的原因,封面图为妇女滑冰图。鼓励妇女进行滑冰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李祥收藏)
原址博物馆不仅是冰雪运动历史的保存者,更是未来冰雪文化的孵化器。它通过空间重塑与技术赋能,让废弃场馆重获新生,使每一次滑雪体验都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这种模式为全球冰雪产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范式——当运动场馆超越物理功能的局限,成为承载记忆、激发创新的文化容器,冰雪运动的魅力将在历史与未来的交织中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