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总是短暂的。今天是周一,上班日。
与往常一样,你被闹钟叫起床,匆忙洗漱完毕下楼赶去地铁,如果隔着一两公里路还得首先扫描一辆共享单车。地铁里人头攒动,排着队过安检进站。到达车门附近,你终于在人群中挤上地铁,因为不是始发站,此时早已没有了座位,连站立的空间也是拥挤的。站在车厢里,脑子里还在不断过近期的项目方案,愁苦之际低头瞥见对面坐在座椅上的陌生人摊开了笔记本电脑,一边敲着字,一边不时扶一扶屏幕谨防滑落在地。

《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剧照。
到了办公楼,身体蜷缩在格子间,开始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后,再重复地铁行程,以此往返于住处和办公室。
前不久,“京沪高铁班味比办公室还浓”“班味最浓的高铁”多次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这是一种与办公室的庸常相似却在形式上极其奇特的“班味”(网络流行语),它快捷、高效,它安静、克制。京沪高铁,中国最繁忙的高铁,在这条高铁线上,乘客们齐刷刷在高铁开动后打开电脑,有的在做标书,有的在做方案,有的戴着耳机在开电话会议。有人在苦苦加班,有人借着旅途提前完成任务,为的是到了目的地后可以躺下睡上一觉。他们讲着行业术语,盯着屏幕,偶尔望向窗外。四五个小时的旅程,足够他们开完一场会、修改一份文案。如此画面,让京沪高铁被称为是“班味超标”(网络流行语)的地方。年轻的上班族乘客感叹,小时候总觉得在火车飞机上用电脑打字的大人很厉害,直到自己成为打工人。上班这件事的“时间”与“空间”在这里发生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变化。
“班味高铁”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但是它在最近的走红,似乎和不少流行的“职场梗”形成了呼应,自嘲的背后,多少反映出了当下职场生态中普遍的疲态。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有一位作者,他的家乡在京沪沿线,后在南京、上海两地求学,毕业后在上海咨询行业从业多年,作为“资深打工人”的他时常到北京出差。他是京沪高铁线上的乘客。比起飞机,“我更喜欢选择高铁,原因之一正是它更好地提供了移动办公的条件”。旅途是否消失,是否被工作取代(或者可以借用哈贝马斯的“被殖民”概念),这段行程的意义是什么?“班味高铁”是让工作侵入了生活,还是为我们灵活工作提供了便捷条件?其中滋味,恐怕没有唯一的答案。且从“班味高铁”里蕴含的几组关系聊起。

撰文|徐一超
工作与生活:
尴尬的“居间态”
“在路上”的通勤时间属于工作还是生活?也许,它是一个尴尬的“居间态”,需要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填充”。如果选择步行、骑车或者驾车通勤,这段时间似乎不容选择也无可填充,因为我们深度投入在这个位移行动的本身之中。

《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剧照。
如果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我们的身体和注意力被“解放”出来,“居间态”的时间就成为一个需要被“处置”的对象。初入职场的时候,我倾向于用发呆、听音乐、刷手机、闭目养神之类的方式“打发”这段时间,就像从前人所说的“消闲”。成了资深打工人以后,我好像会开始思考怎么“利用”这段时间,比如回复一些工作时间没来得及回复的琐碎信息,读一些片段性的文献,或者加入“知识经济”的消费大军,给自己充电。
某种程度上,京沪之间的差旅之路,就是放大版的通勤时间,而“班味打工人”们的普遍选择,就是充分地“利用”它。这种对“间隙时间”最大程度的占有和利用,在全球范围内恐怕已经流行了上百年。马克思指出,与19世纪大规模的劳动和生产重组相伴出现的是“流通时间”和“通信时间”的加速与控制,前者以铁路这样的新型交通工具为代表,后者以电报这样的新型通信手段为代表,两者交织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的增长起到关键作用。他还说过:“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成就,如更快的货运速度或即时通信的实现;而是说,如果资本的本质过程是流通,那是因为‘这个过程永恒的持续性(constant continuity)’。”
这段话转引自美国学者乔纳森·克拉里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美]乔纳森·克拉里著,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1年5月。
24/7体制真是当代社会一个形象且鲜明的符号。24/7的时间里,在人们重要的行动和任务序列中,原本存在许许多多的“间隙时间”,但如今它们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克拉里书中还比较了福柯所谓“规训社会”和德勒兹所谓“控制社会”的区别。如果说前者像“全景敞视监狱”一样的权力机制还不是弥漫性的,那么后者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化控制持续不断、没有界限,且基本上全天候:“控制社会的特点是间隙消失了,敞开的时间和空间也消失了。命令机制和规范化的效果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而且以更全面更微观的方式进入到人的内心”。这大概就是“班味高铁”背后的职场生态吧。
你若问我作为“班味高铁”上打工人的一员有何感受,我想说,倒也还好,因为我并不讨厌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有时甚至有点喜欢。于是我就在想,姑且撇开工作不谈,如果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间隙时间”同样消失了,但恐怕就不会有“班味高铁”这样的酸辛苦涩。我还想到有一年去青甘大环线包车旅行,第一次用上了无人机,途中忍不住赶紧将所拍所感记录下来,就把Surface(电脑)和迷你键盘放在腿上,一路颠簸,一路码字,竟有点乐在其中的味道。

《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2016)剧照。
所以,“班味高铁”的话题热度,恐怕并不源于“在高铁车厢里工作”这个客观事实,而是源自万千打工人心底的感受以及背后深远而普遍的职场生态问题。如果工作和打工人的关系成了马克思说的“外化”甚至是“异化”,也就是工作及其成果成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甚至“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工作对日常生活“间隙时间”的无限侵占,自然就带上了某种悲剧意义。
但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一个热爱文字的职业作家在京沪高铁上码字写作,算不算有“班味”呢?“在高铁车厢里办公”本身不是工作的“异化”,但这个客观现象所引发的广大劳动主体的强烈反响,反映出了更深广的职场“异化”问题。
旅途与目的地:
你会不会说我酸?
“班味高铁”涉及的另一组重要关系,是旅途与目的地,虽然这里的“旅途”不是“旅行之途”,而是“差旅之途”。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大学的当代文学课上读过的这首现代诗: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知道这不该
我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插腰
右手作眉檐
眺望
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账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功夫
黄河已经远去
——伊沙,《车过黄河》

王福春摄影作品。图片源自《火车上的中国人》,王福春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2017年6月。
不论诗里蕴含着多么深重的隐喻,末两句已经足够有力地描摹了搭乘高铁的旅途状态。曾经的天堑,迢递的空间,一下子被速度和时间征服了。在“班味高铁”上,可能码下一行字的工夫,长江就已经远去。在京沪高铁最快班次的4小时18分里,可以开完一场激烈拉扯的电话会,画完几十页精致美观的PPT,却欣赏不了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说,铁路一方面让人们通达从前不易抵达的空间,另一方面却也破坏了起点与终点之间的“旅行空间”:“这个中间物,或者说旅行空间,过去在使用低速的、劳动密集型的始生代交通技术时,是可以慢慢‘欣赏’的,在铁路上却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旧式的地方认同感”(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高铁无疑让这种“消失”更加彻底,它用一个个瞬间所跨越的历历晴川、沃野千里,对于车厢里无暇四顾的乘客来说是那么遥远,又那么隔膜。

《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著,金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8年7月。
作为资深打工人,我曾经因工作去过很多从没去过的城市,但如今对它们的记忆似乎大都只有某个具体的目的地——酒店或办公楼的室内空间,而旅途——无论是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还是在目的地城市之内的交通过程——好像真的被“消灭”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旅途景观都在碎片工作的“一会儿工夫”里即时性地远去,还是记忆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些在潜意识里并不重要的“过程”。
鲍曼说:“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战争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只能进行防御性的壕堑战并阻碍时间的前进。时间则是战争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它永远具有进攻性:具有侵略、征服和占领的力量。在现代时期里,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掌握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工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班味高铁”可谓这种现代“时空之战”的典型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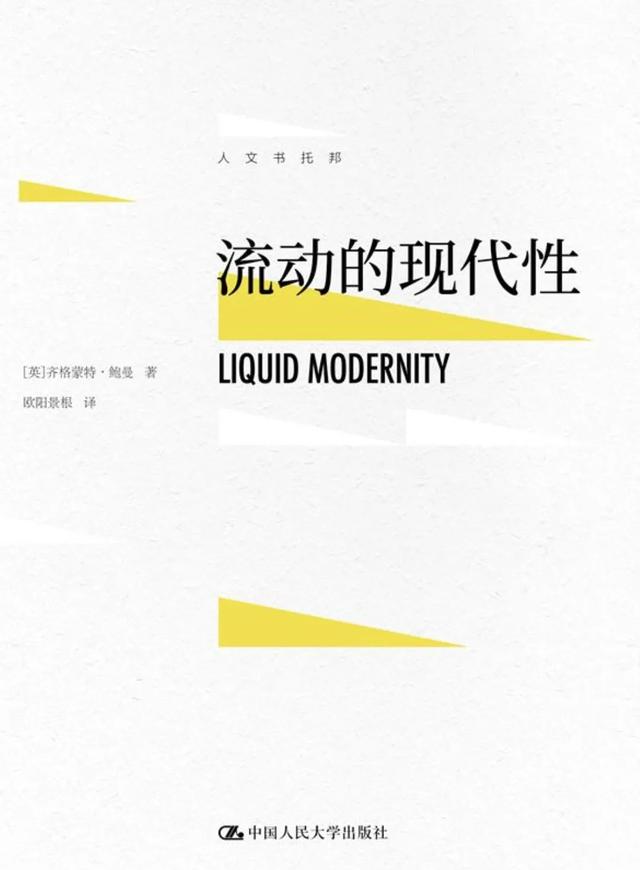
《流动的现代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然而“旅途性”空间的“被消灭”,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我这个资深打工人的心底,好像一直存留着对于美好“旅程”的眷恋。我的家乡是沪宁线上的中间城市——江苏无锡,去南京读本科的时候,沪宁高铁往西北方向开,过了镇江,渐渐能看到起伏的丘陵,穿过几个山洞,也就到了南京;去上海读研的时候,沪宁高铁往东南方向开,一路平畴,过了苏州,沿线就是阳澄湖,晴好的天气里能望见水光潋滟。“包邮区”这迥异的旅途风貌至今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开车往返无锡和上海之间,但我不走距离更近、限速宽松的沪宁高速,而宁愿绕弯走沪常高速,原因就是两段旅途不同的体验:开沪宁高速就像吃有“班味”的工作餐,绝对划算和正确;而沪常高速在太湖边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穿过名胜旧迹,途中能看到起伏的丘陵和山顶的古建,一个个高速出口还连缀起“南泉”“望亭”“东渚”“藏书”“天池山”“胥口”“木渎”“横泾”“光福”“香花桥”这些美丽的名字。
“旅途性”的空间绝不仅仅存在于从一城到另一城的大尺度里,而且可以孕生在任何一种规模的“过程状态”之中。

《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
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城郊的仙林大学城生活过两年,学校又在大学城的边缘位置,可谓“城郊之城郊”。那时我们要进城,只能坐公交,有些线路甚至还是那种十分颠簸的老式公交车。后来,当我们要搬去市中心的校区时,地铁通了,但我和好友有时仍然会选择坐公交。我们戏称,和地铁相比,那种又慢又颠的老式公交车真有几分“蹇驴”的味道。“从前慢”的“学生郎”坐在车窗边一路颠簸、一路发呆,让我们联想到“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的苏轼,“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陆游,还有“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的孟浩然。
你会不会说我酸?但“酸味蹇驴”和“班味高铁”确乎是两种迥然有别的“过程状态”的隐喻。
和“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班味高铁”不同,“蹇驴”是慢的,散淡的,沉浸在过程之中的,它让空间“制衡”时间,让旅途“制衡”目的地。“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唐彦谦《忆孟浩然》):读到这几句的时候,打工人们也是要心动的吧?
手段与目的,
过程与结果
忍不住针对有热度的“班味高铁”写点什么,是因为这一现象让工作与生活、旅途与目的地这两组重要的当代关系交叠在了一起,而背后则是更为抽象的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之争。
前些年人们在反思金钱的意义时,不时能听到一句话——“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很多人把金钱本身当成了目的”。这个关系框架如果转用在工作和生活之上,似乎也是适用的:工作只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描绘了原始部落里的劳作状态,那大概代表了前现代社会工作的原初面貌——工作和生活、手段和目的尚没有二分,劳作本身就是目的、就是生活。中国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计”,传达出的也是这样的意味。到了现代社会,工作、职业成为人们实现特定生活、人生目的的手段,二者产生了分化。而在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驱动下,手段和目的“异化”地纠缠在一起:“营利变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对于人天生的情感而言,这简直就是我们将谈到的‘自然’事态的倒错,毫无意义,然而如今却无条件地公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指导纲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1995)剧照。
更要命的是,即使工作和赚钱不是人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也不知道“目的”为何物了。在“手段”(means)和“目的”(purpose)之间,可以存在无数层“目标”(objective),习惯了KPI和“结果导向”的打工人也习惯于把“目标”当作“目的”。有一句英文名言,译成中文大意是:应该根据星辰来确定航向,而不是追随来往船只的灯光。(Set your course by the stars,not by the lights of every passing ship.)“目的”就是那“头顶的星空”,只要朝向“北斗”的方向不错,航路和旅途的曲直缓急和阶段性结果,似乎就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内心始终是笃定的,旅程本身就是体验和价值所在。
换言之,如果能更好地把握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也就能更好地把握过程和结果的关系:结果固然重要,但过程也需要更松弛地“敞开”。当下职场高度膨胀的工具理性的可悲之处在于:一方面消灭目的,把手段当作目的,另一方面消灭过程,把结果奉为圭臬。消灭了“间隙时间”和“旅行空间”的“班味高铁”,大概就是这样一种职场生态的隐喻。
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呢?作为打工人,我能想到的比较关键的对策,是重思和重建个体的“目的”性:在职业发展的“目的”甚至人生“目的”的全景中审视每一趟旅途,它的值与不值,它的个中况味,它的勤进或背离,它对于主体而言的意义感,都会更加清晰。

《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1999)剧照。
重建“目的”事实上也是在工具理性膨胀的职场生态中重新呼唤价值理性,它有可能让打工人从被动的劳动者转变为主动的工作主体,让“班味”变成“自驱”。而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我想有必要呼吁一种更加开放多元的价值取向,即当代职场、当代社会的运作并不只有“班味高铁”这一种范式,我们可以反思它的合理性,也可以享用它的灵活便利,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创新创造的可能性。
最后,如果“班味高铁”也算是移动办公、灵活办公的一种最新形式的话,我想用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写下的一段话来作结:
“灵活性,就像科技一样,是一种工具,一个机会:它就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人们去拿起来享用。……最后,就看办公者是否能赋予这份自由真正的意义:看看他们是否能把劳工合同打磨成切实有效的合同,看看他们是否能将这份‘自主权’行使得真实可靠,看看他们是否能让办公空间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美] 尼基尔‧萨瓦尔著,吕宇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8年5月。
“班不班味”,你可以选择。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徐一超;编辑:西西;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