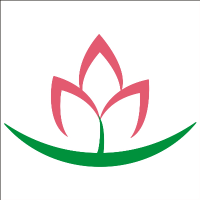中唐文坛恩怨录(中)|半生真情元与白,死生契阔三十载
文:枯木
(续上)

上篇谈了中唐挚友韩柳刘一生君子情,其中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友情最令人称道。二人同科中举,志向高远,性情相近,兴趣相投,从此结下深厚友情;后来共同参与永贞革新,作为主将,废旧立新,革弊兴利,大展宏图,挥斥方遒,可谓同声同气,意气风发。
然而时不我与,风云突变,宦藩勾结,新主登基,二王八马,折戟沉沙,贬谪荒远,郎永屈就。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情,二人既不卖友求荣,更无谄媚图起;反而愈挫愈勇,不屈不挠,十五年间书信不断,相互勉励,相许养老为邻。
奈何天妒英才,子厚中道而亡,临逝托孤,感人肺腑。退之倾心而为,梦得不负重托;撰文树碑,结集刊书,此情可鉴,昭昭日月!三人不但因诗文皆为大家流芳百世,也因友情深厚青史留名。
而在同一时期,还演绎着另一段友情传奇,虽然未必有刘柳那么感人,然而也是情真意切,友情真挚,那就是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三十载深厚情谊。关于二人友情的文章,自媒体多有论述,不过不少文章为了哗众取宠,附和现时低俗潮流,竟然有说二人为“同性恋”!
如此臆测调侃实在可悲,也令人汗颜。固然元稹因品行操守多受人指责,不过就事论事,二人交往皆因性情相近,兴趣相投,各自又才华横溢,从而惺惺相惜,结下深厚情谊,概非他人之臆测。看来这些人从来不知何为友情何为朋友?正如佛偈所云“相由心生”,心中有魔,所见皆魔,说的通俗点就是以小人之见度君子之腹,纯属污蔑之举。
那么,元白二人交往究竟如何?就以白居易的总结而言“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祭微之文》),两人的诗词书信多达近千首(篇),创下了自古以来朋友之间书信诗词相和最多的纪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关于诗词,有很多文章列举,这里就不赘述,我们就从《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史料记载,还原二人交往的历史。
一、秘书省里秘书郎,门下省中左拾遗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和诗人刘禹锡以及李绅(772年~846年)同岁,幼时就聪颖过人,贞元十四年(798年),27岁参加进士科,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
白居易虽然和刘禹锡同龄,并且比柳宗元要大一岁,可是因为中举晚比二人5年(刘柳为793年),因而从科举辈分上来说属于晚辈,当然比韩愈更晚。可是白居易对自己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那一年中举只有自己年龄最小,因而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诗句。
而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却中举要早,不过并非进士科,而是明经科。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今洛阳),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以明经擢第,不过并未任职。贞元十八年(802年),二十四岁的元稹调判入等,被授为秘书省任校书郎,与在此已经作秘书郎五年的白居易初次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友情。
当元白二人结识之际,这一年,恰巧也是韩柳刘三人在御史台相遇之时,两段友情同时萌发,同时生长,并且相互之间并无交集。不过此时的光辉属于刘柳二人,二人积极参与革新派,并且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达到极点,在二王支持下,刘禹锡擢升为屯田员外郎,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此年韩愈因为得罪德宗被贬广东连州),掌握着朝廷人事大权,朝廷众臣为之侧目!
然而不久革新失败,刘柳被贬偏远州司马,仕途进入下坡阶段。可是针对元白来说,才是开始!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时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并且一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以制策第一,授门下省左拾遗。白居易制策乙等,调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为集贤校理。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元和三年五月,拜门下省左拾遗。
二、元稹母逝白为铭,白母坠井元作文

元稹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于是在元和元年(806年)四月上任伊始,便上书《教本书》痛斥“永贞革新”,获得既得利益者唐宪宗赏识,然而因谈论西北边界政事,被宰辅忌惮,出为河南县尉,九月份因母亲去世丁忧,上任几个月就离职,这是元稹第一次失意。
不过,此时元稹得到白居易的友情安慰,为元稹母亲写了墓志铭《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其中有“居易不佞,辱与夫人幼子稹为执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号慕,哀动他人,托为撰述,书于墓石,斯古孝子显父母之志也。”说明二人交情匪浅。并且白居易母亲也因为元稹是儿子好朋友,予以极力照料和关怀。
这可从后来元稹为白居易母亲撰写的祭文中得知,祭文有“太夫人推济壑之念,悯绝浆之迟,问讯残疾,告谕礼仪,减旨甘之直,续盐酪之资,寒温必服,药饵必时,虽白日屡化,而深仁不衰”,这让元稹非常感恩,于是“重戴冠缨,再展升堂之拜”。可知元稹在母亲去世后,深感白母眷顾,此时便拜白居易母陈氏为义母,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丁忧后除服拜为监察御史,出使剑南东川,弹劾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此时严砺已死,不过得罪了同党,于是被撤回,派往监察东都洛阳。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
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谩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脸面,元稹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湖北荆州)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白居易此时依然是左拾遗,上书替元稹鸣不平。认为元稹为官正直,在东川有功;不过也认为元稹做事有点过,“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然而对宦官击打元稹却是“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认为贬谪元稹带来的影响较大,然而皇帝未理睬。
元和五年,依例改官,皇帝允许白居易选择,白居易以家贫奉母为由,被授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即元和六年(811年)四月,白居易母亲因为看花坠井去世丁忧。元稹远在江陵府无法前来吊唁,便写了祭文让弟弟前去祭拜,同时赠送赙仪二十万(相当于如今20~30万元),这在白居易的诗词《寄元九》中有:“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
不过白诗也无意之中披露了元稹的为官有瑕疵,作为一个偏远州府九品的士曹参军,一出手就是二十万钱,而且在元稹自己上表中叙道:“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说明家境较差,贞元十八年(802年)才成为秘书郎,为官不久遭遇丁忧三年,因而只是做了几年小官,就能拿出二十万赙仪,即便是给自己的义母——好友的母亲,也确实令人咋舌!不过这是闲话,也说明两人感情之深。
三、白贬江州观念改,元造蹉跎时运来

白居易在元和九年(814年)服除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此时发生“宰相遇刺案”,元和十年(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杀,副手裴度被伤躲过一劫。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认为是博名,再加上有人提出白居易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其却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因而被贬黜到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雪上加霜,因而被再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经此一变,从此人生观念发生重大转变,虽然其坚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念,然而真实情况是,前半生“穷则心忧天下”,被贬后心灰意冷,除了少数几次为政之举,大多醉心山水,到晚年“达则独善其身”,皈依佛门,再无兼济天下的行动。
而此时,久遭贬谪蹉跎了近十年的元稹迎来命运的曙光,这应得益于元稹在江陵时期结交的宦官监军崔潭峻。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去世,唐穆宗登基,唐穆宗喜欢游玩,当太子时就喜爱元稹诗歌,宫中呼为“元才子”。继位后宠幸崔潭峻,崔“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穆宗大悦,问元稹何在?得知为南宫散郎,便立即授元稹祠部郎中、知制诰。数月后,又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

而元稹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也埋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患。首先是元稹同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交好,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而李德裕与中书舍人李宗闵之间怨恨颇深。源自李德裕父亲宰相李吉甫曾经错误把牛僧孺和李宗闵降职,后来李吉甫被贬,从此形成恩怨。
李宗闵跟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穆宗朝被拜为中书舍人。长庆元年(821年)发生科场复试案,前宰相段文昌、李绅等曾经托主考官,然而未果,于是揭发科场舞弊,其中中举的有李宗闵之婿、裴度之子等。穆宗询问李德裕、李绅、元稹意见,认为属实,于是派人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三人勉强及第,李宗闵等被贬官,从此积怨更深。
而三俊也各怀鬼胎,李德裕执意要打击李宗闵,牵带宰相裴度;李绅公报私仇,勇往直前;元稹是官迷,十年蹉跎压制,自然要扬眉吐气,再加上因为穆宗宠爱和宦官的支持,因而目标是宰相之位,自然要把以前的宰相打落马才有空位。于是三人不谋而合,寻找对方弱点攻击。
裴度是当时朝廷倚重的重臣宰相,平定淮西,辅佐宪宗创立元和中兴,功勋卓著,忠心耿耿。当时在山东指挥作战,军事论奏多被元稹留持,于是忍无可忍,三次上表《论魏弘简元稹疏》弹劾元稹勾结宦官魏宏简,谋乱朝政,在群议汹汹之下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而穆宗非常宠爱元稹,于是在长庆二年(816年)元稹拜平章事,被任命为宰相。然而“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旧唐书》)。
元稹当上宰相后,急于立功,未经其他宰相同意,就给人二十张空白文告招募勇士拯救被王廷凑围困的牛元翼。这时另一阴险宰相李逢吉知道后,给裴度说元稹“将刺公”,裴度不为所用,于是李逢吉又派人到神策军告发,说元稹要刺杀裴度,这让皇帝非常震惊。于是朝廷派李逢吉等审案,元稹派发空白文告自然罪行严重(当然可能最后说是裴度派人诬告),结果两人都被贬去平章事,元稹贬为同州刺史,裴度为仆射东都留守,被免去兵权。
四、元稹实无宰相才,居易论奸让人猜

就在元稹谋划着罢免裴度兵权的时候,白居易出于公心,上书《论谏请不用奸臣表》替裴度鸣冤,其中有:“矫诈乱邪,实元稹之过”,“天下人心,无不惶战,何执元稹之言,居(裴)度散司之职?且同议裴度今功业今代一人,卿侯士庶,无不同惜。今天下钦(裴)度者多,奉(元)稹者少,陛下不念其功,何忍信其奸臣之论?况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嚣轩之过。”直指元稹为奸臣,也是二人相识十余年来第一次。(不过宋代也有考证,说白居易不是如此刚烈之人,此文不一定是白居易所写。)
然而不管是不是白居易所写,元稹身败名裂却是事实。可笑的是,元稹费尽心力,在穆宗宠爱和宦官支持下,只当了几个月的宰相,却丝毫无宰相之能,操权弄势,纸上谈兵,不但使得朝廷混乱,最后还埋下了党争祸患,因而遭到群臣斥责,甚至连挚友白居易都看不过去也有可能。
长庆三年(823年),元稹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图谋复起,入朝为尚书左丞,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在官署去世,卒年五十三岁。
而白居易元和十五年(820年)夏,从忠州刺史位上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第二年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年),加朝散大夫,成为五品大员。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中间曾同元稹在杭州短暂相聚;
长庆四年(824年),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后病免;文宗大和元年(827年),任秘书监,成为三品官员。大和二年(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四年(830年)任河南尹。
五、 微之品行堪称哀,不掩元白真情在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元稹去世,临去世前去信请白居易为自己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六七十万钱(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元稹为官不检点),白居易拒而不受,结果无法推辞,最后将其布施于洛阳香山寺。白居易在元稹去世后先写祭文《祭微之文》,回忆二人三十年深厚感情,非常感人。
在第二年墓志铭中历举元稹政绩和突出的文化地位,最后评价:“呜呼微之!年过知命,不谓之夭。位兼将相,不谓之少。然未康吾民,未尽吾道。在公之心,则为不了。嗟哉惜哉,广而俗隘,时矣夫!心长而运短,命矣夫!”也认为元稹到死都是不服气,认为自己有将相之才,却时不我与,心胸狭隘,短命而亡。
事实上,元稹却是非常善于紧抓时机之人,从史料来看,元稹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中年宰相,位极人臣;诗词虽浅,却引领文化潮流。虽然肯定和妻子韦丛感情甚笃,然而不能否认少年风流,中年多情,而且无论是娶妻续娶,都有政治目的,和诗文无关。
总体来说,元稹只不过空有文采,而无宰相之能,正如《旧唐书》所言“然以稹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新唐书》所论:“然稹素无检,望轻”,史书评断,非常公允。
(限于篇幅,下文待续)

2021/4/16榆木斋
主要参考文献:
《大唐六典》
《唐摭言•卷一》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韩张孟刘柳传》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六•元稹白居易传》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李绅传》
《新唐书•列传•第九十九•二李元牛杨传》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零六•李绅传》
《唐才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