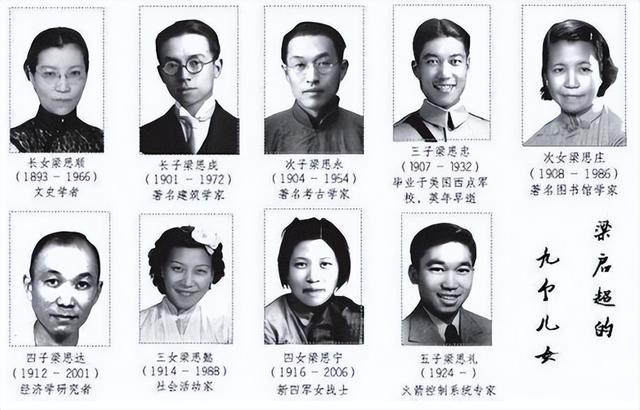作家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阿坝地区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1994年冬,他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阿来代表作还有《格萨尔王》《空山》《瞻对》《蘑菇圈》等。
吴小莉专访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阿来,2025年1月6日晚20:30凤凰卫视中文台首播。
1
阿来:我的文字也罢,
在社会上做别的事情也罢,
我希望有一点点建设性……
吴小莉:回到您创作的最初,您说在创作《尘埃落定》的时候,其实想写出不一样的藏文化。
阿来:对。大家都有一个想象,就是过去讲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说西方想象东方,我说我们内部也有东方主义,发达的地方想象不发达的地方,这个民族的人想象那个民族的人,这个宗教的人想象那个宗教的人,我们都有一些先入为主并且不切实际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文化,人家说很神秘,我说什么地方神秘了,不都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吗?然后权力、金钱,文化无非就是这些嘛!除非有些人要故意神叨叨的,我说那有人装神弄鬼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了,我们今天这个文化装神弄鬼的人多了,需要一面照妖镜。
吴小莉:您真的要落笔写这本书的时候,用了三年时间去行走、去了解?
阿来:30岁,30而立,我之前的两本书立了吗?我觉得不够好,这是第三本书,也是很多契机。当一件事对一个年轻人产生冲击,你要何去何从?它背后包含的是国家要何去何从?那个时候你突然觉得,以前写的那些东西轻飘飘的,干什么呀?世界上难道还少了这样的文字吗?怎么办?我说不行,我要写我们自己的小历史,小历史也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小历史不行,然后我就开始做这种田野调查,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行走。
那个时候又没钱,没有交通工具,公共交通也远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所以大部分抵达都是走路去的。大概三年时间,也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把一些忧心忡忡的事情开始忘掉。
吴小莉: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自己忧心忡忡的事情开始忘掉,都忘掉了什么?
阿来:就是你觉得你考虑自己个人的前途也好,还是有点忧国忧民也好,往往有时候大而无当,就是你想的问题很大,但是这个大的问题自己在里头能做什么?我发现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到自己力所能及的那个地方,重新出发,我叫建设性。不要光批判,新文化运动,鲁迅他们就开始批判,但批判要不要?要,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愤青”,这个社会也没有进步。
吴小莉:要有批判的精神,但是要有建设性的行动。
阿来:对。我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我的文字也罢,我作为个体在这个社会上做别的事情也罢,我希望有一点点建设性。
吴小莉:《尘埃落定》的问世解决了您自己的迷茫之外,其实您也在看您用什么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原生文化。
阿来:对,原生文化,原生的历史是什么?
吴小莉:这样的文化您书写起来,好处是大家一定会有先天想窥探的欲望,坏处就是可能之前有很多误解和迷思,您想要破除的迷思是什么?
阿来:其实迷思就是把西藏的文化浪漫化。有两种人,一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藏民族以外的人,尤其是有点文化的人、都市里头的人,他们觉得西藏就是我们这个文化的反面,如果我们是物质的,它应该是很精神的,如果我们是很复杂的,它应该是相对单纯简单的,他们其实想象了一个自己的背面,像月亮背面一样。而这个时候,西藏尤其是宗教界,他们从这种想象当中能得到好处,不是老百姓,是这些人能得到好处,他们也愿意助长这样的想象。
吴小莉:那您觉得《尘埃落定》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真相?
阿来:即便一个小小的土司的政治,难道跟一个国家的政治打开不一样吗?这个文化在表现上,有一些和其它文化的不同,但是它的本质不就还是权力、金钱、美色。所有历史大戏的驱动,不就是这三个东西。这本书也不例外,它把一个文化的内在结构展开给你看,它也是一个权力支配的世界,物质和美色驱动的世界。

2
阿来:不只是藏文化,
有时候想唤醒更多的人,
但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期待值有点高……
吴小莉:《尘埃落定》得到了很多奖项,但您说迄今为止20多年过去了,对它的争论还是存在的。
阿来:尤其是藏民族内部,说给他们抹黑了,他们不是书里这样的,而且往往可能是一些,我把他们叫做半吊子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希望描绘的藏族文化不是这样的。
吴小莉:他们希望描绘的就是全面的美好。
阿来:对,美好世界。
吴小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些得奖的作品,常常会是那个文化当中比较落后的、黑暗的,或者就像您说的,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的部分。
阿来:第一,文学有个真实原则,这个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像信仰一样;第二,你的文化要提供反思,因为藏民族是悲剧性的,在唐朝的时候它曾经很先进,是唯一可以跟盛唐抗衡相始终两百多年,还没有斗出胜负的一个文化,当这个地方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宗教,变成所谓政教合一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社会的结构,几乎就停留在这个时期一千多年。
所以我打过一个比方,我说这个文化就是一座老房子,曾经很恢宏巍峨,但经过一千多年雨打风吹去,你们说是共产党来把你们打倒的,那唐朝那么强大都不能把你打倒,共产党就把你打倒了?是老房子自己出问题了,人家顺手一推你就倒了,你腐朽了,你没有跟这个世界进步,你整个文化所有产生的资源都是为少数宗教服务的。
吴小莉:但我在您最近的一次演讲当中看到,您还是提到了,对于现在藏文化的民族文化,误解仍然存在。
阿来:其实这个不只是藏文化。有时候想唤醒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人来认同,但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期待值有点高。因为今天又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过去我们已经想清楚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已经摒弃的问题,又假借爱国、爱民族的名义重现。
吴小莉:哪些问题?
阿来: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好,洋人的什么东西都不好,不加区分。过去五四运动以来,教给我们是所有东西,包括传统文化、引入的西方文化都要加以区分。
吴小莉:您会担心什么?
阿来:我就担心沉渣泛起。尤其西方现在对我们,也有种种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反的作用力。但我觉得我们要警惕,反作用是必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路径和方法要对,不然反作用力,像打枪的后坐力,不但没把人家打死,经常把自己弄伤的情况比比皆是,所以我觉得思想也是一种武器。

3
阿来:我们除了认识人以外,
周围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生命世界……
近年来阿来将创作重心由历史转向生态,由小说转向散文,代表作:“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因此阿来也被读者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吴小莉:您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的?
阿来:因为我觉得,我们除了认识人以外,周围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生命世界,就是植物和动物。
吴小莉:您做了一些尝试,像《西高地行记》,或者是《去有风的旷野》,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生态文学的尝试?
阿来:这个有。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不断地开辟新领域,开辟新领域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题材上、内容上。比如说过去我写《尘埃落定》是历史,但今天我觉得要更关注现实,过去我读某一本书,可能更多关注人文方面,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对自然界的关注少,尤其相对于西方的文学来讲是这样的。西方文学在工业革命以后,人对大自然的破坏、对环境的污染,就已经在它们的文学当中迅速出现了,它们就叫自然文学。
比如说差不多一百年前的几个美国作家,他们书写大自然的同时,还要唤醒公众来保护大自然。他们到处演说,游说议会,甚至成功地把当时的美国总统带到山野里去,说你要跟我们去露营,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最后的结果是第一批全世界的国家公园的创立。其中他们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优胜美地公园的创始人约翰·缪尔,写过一本非常骄傲的书,叫《我们的国家公园》。他们设计了这样一个制度,不光是书写了大自然的美好,他写过的《夏日走过山间》,讲怎么欣赏大自然美景,但是光这个不够,既然有这个先知,就应该行动起来。
吴小莉:那您觉得中国的生态文学,您在尝试,有没有更多的人在进行尝试?
阿来:现在慢慢我们有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说尝试的人很多,但是水准我觉得还不够高,确实需要非常多的专业知识。而中国大部分作家过去都还是比较偏人文一点,我们中国文学当中,当我们只写人的时候,至少内容上美好的文学不多,因为就是人的勾心斗角,我经常说只关注人和人的关系,只能往暗黑处去写。
但是唐诗宋词里,大量美好的内容都是和自然有关,所以要真正有这个理念,真正要付诸实践,真正要把自然作为对象来进行书写,而且不是过去那种审美化的,当然审美是必须的,同时还是科学化的,同时又是跟人文结合的。如果只是科学地书写,过去有很多科学家、科普作家,写出来就是冷冰冰、干巴巴的,也没有感染力。我们要把它变成文学,要跟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对接起来,西方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当中,已经有非常成功的尝试,到今天还长盛不衰。
4
阿来:生命是用更大的一种方式
在延续、在存在……
吴小莉:您曾经说过,我们对于自然的描述太少,或者是说我们很快把自然定性了,定了它的人格、象征意涵,这对于我们认识自然或认识它的本质有什么样的妨碍?
阿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就是缺乏科学观。我们古人也非常热爱大自然,之后迅速地对自然有选择地看见。比如说写梅花,他是要写梅花吗?不是,梅花耐寒,因为迎春最早开放这个特性,它就有了一个高洁的人格化的象征。最早象征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太好了,但是最后所有人写梅花都这样写,思维就固化了;中国画和中国诗里写荷花,“君子出淤泥而不染”……写任何一种植物都有一个固定的意义,最后它就套路化了。第一个这样写的人当然非常了不起了,但第二个第三个,它就变成因循守旧,所以后来我们的诗歌包括国画,失去活力,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再在这当中发生新的东西了。
吴小莉: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深刻地体验,还是因为什么?
阿来:体验已经套路化了。后来的诗人、画家再写这些东西,也写不出新鲜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天人感应,但这个感应是怎么发生的?面对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个世界和菩提,是怎么感知到的?必须把这个具体的过程重新书写出来,那个只是一个大的路径的书写,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上发生的时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感应,互相交织的。
吴小莉:有没有到现在,您还印象深刻的那种感应?
阿来:有。有些时候你突然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风景,它并不那么客观,跟你当时的某种情绪非常对应,尤其是看到一些小花小草,当你抵近观察,把它当一个世界打开的时候,那种内在的结构、内在的美,那种内在的充沛,不因为小而不完整,都给你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
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时候人会悲观,我们绝对的悲观就是在于我会死,生命终有一天要结束。但是你看到生命是用另外一种代际的方式,传递生生不息的时候,你又开始有一点乐观主义,但是这个乐观主义就超越个人了,原来生命是用更大的一种方式在延续、在存在。

制作人:韩烟
编导:梅苑
编辑:金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