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组缃是著名小说家,早二十世纪世纪三十年代,就发表了《官官的补品》、《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小说集《西柳集》、《饭馀集》,得到著名作家茅盾和文学史家王瑶、夏志清等人的高度评价。

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又是著名古代小说研究专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表了《<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等几篇重要论文,堪称学术经典。还担任过中国红楼梦学会第一任会长。石昌渝说,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吴先生也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的贡献。”[1]这一评价,吴组缃当之无愧。
吴组缃是怎样走进红学研究领域的?他的一系列经典论文是怎样产生的?对当代红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吴组缃,还是研究红学史,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吴组缃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1954年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2]
1955年秋季,吴组缃首次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红楼梦》专题课。一个教现代文学的教授,突然讲授古代小说《红楼梦》,看似不合常理,实则水到渠成。
据吴组缃晚年回忆:“1954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不知怎么搞成批判运动。听说是朱总司令讲:‘你们讲人家研究《红楼梦》讲得不好,那么你们讲一讲嘛!’有了这么一句话,就叫北大中文系开《红楼梦》专题课。这样,就打鸭子上架,一下子落到我头上来了。”[3]
“打鸭子上架”当然是吴组缃的谦虚,《红楼梦》专题课落到吴组缃的头上完全在情理之中。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吴组缃第一个发言,发言稿于1954年12月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并略谈<红楼梦>》,是吴组缃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
同年,为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吴组缃撰写了长篇论文《<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发表在《人民文学》1954年8月号上。两篇论文显示出吴组缃在古典小说研究方面精深的造诣,开讲《红楼梦》,吴组缃是不二人选。
1955年秋季,吴组缃第一次在北京大学讲授《红楼梦》,听课学生是北大中文系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吴组缃的讲义首页有记载:“三年级课代表:王振兴。四年级课代表:崔道怡。”即1952级和1953级学生。
曾经听过吴组缃讲《红楼梦》的张相儒回忆:“1955年秋,他将潜心研究《红楼梦》的成果首先拿到课堂上去经受检验,引起强烈的反响。听者又一次如醉如痴,不少学生惊叹:听吴老师讲《红楼梦》,就像磁石吸铁那样,你不想听都不行。”[4]
为讲授《红楼梦》研究专题课,吴组缃撰写了详尽的讲义。笔者于2011年4月在整理业师沈天佑先生的文稿时,发现了吴组缃的《红楼梦》研究讲义。

《沈天佑文存》
讲义用A4大小的活页纸撰写,共17张,正反两面书写,34页,约5万多字。题为“红楼梦研究”,题后注明“选修课,专题讲授”,“1955.9.14写”。所注时间应该是第一次备课时间,全部讲义是1955年秋季学期写成。
首页列了8篇参考论文和10个专题的讲授内容:“一、《红楼梦》的时代社会背景简述。二、《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三、《红楼梦》典型人物分析。四、关于作者(曹雪芹、高鹗)的生平及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问题。五、《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六、《红楼梦》的情节结构。七、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八、选文讲读。九、新旧红学批判。十、关于《红楼梦》的版本。”另有一个专题“《红楼梦》的艺术语言”没有序号。
这些专题应该是讲课计划,每个专题后面还写了计划讲授时间。而现存讲义并没有完整的10个专题,第2页至第6页写了三个问题:“一、本课的性质、目的及任务。”“二、关于本课讲授内容和课程进行方面的一些问题。”“三、《红楼梦》时代背景简述。”
第7页写了一个专题的题目与大纲:“《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一、概述。1、什么是作品的思想倾向性。2、《红楼梦》的思想倾向性。二、贾宝玉的典型形象。1、关于艺术形象。2、宝玉性格的形成与发展。3、宝玉形象的特征。4、作者对宝玉形象的了解与态度。5、宝玉形象的限制性。三、贾宝玉的婚姻悲剧。1、林黛玉形象的特征。2、薛宝钗形象的特征。3、宝玉的爱情及婚事的发展。4、宝玉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源。四、贾宝玉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集中写了两个专题,一个是“《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共4页。
一个是“《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贾宝玉的典型形象。”共23页。后一专题写了五个问题:“一、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形成。”“二、宝玉思想性格的发展。”“三、宝玉典型形象的主要特征。”“四、宝玉形象的限制性。”“五、作者对于贾宝玉的态度与了解。”

《吴组缃小说课》
显然,“《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贾宝玉的典型形象”原本是作为“《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的一个问题来写的,后来越写越多,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计划,索性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
这份讲义只是一学期讲课内容的一部分,讲义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关于《红楼梦》的主人翁贾宝玉的艺术形象的研究,我们讲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虽费去许多时间和篇章,宝玉的艺术形象的问题并未谈完。因为我们在以上的研究中,把贾宝玉的重要的一方面搁下未谈,即关于他和林恋爱与和薛婚姻这一全书中心事件,一字未提。所以宝玉的艺术形象或思想性格,以上并未能谈得完全。因为我们要用一篇章专门来谈这一作为全书中心事件的问题。”
后面未见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的内容,这些讲义可能佚失。
1956年秋季,吴组缃再次讲授《红楼梦》专题课,这次是和何其芳在北京大学同时开讲,这就是红学界津津乐道的“打擂台”。

《红楼梦的艺术生命》,吴组缃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据吴组缃的研究生李厚基回忆:“在与先生讲《红楼梦》的同时,北京大学还请校文研所所长、诗人何其芳作《红楼梦》的学术报告。何、吴二先生是挚友,他两人对《红楼梦》的看法却有较大分歧。听说二位先生为此曾有彻夜之争,但谁也不能说服谁。吴先生曾把这种分歧的观点讲给我们听。给我总的印象是表现在对薛宝钗的认识上。吴先生说,有人说宝钗一脑袋的封建思想,是个典型的淑女,吴先生不同意,他认为‘薛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利就干什么。她多少有点市侩气。’”[5]
关于吴、何彻夜之争,张锦池曾当面向吴组缃求证,“吴老说:‘实有其事。没有辩论一夜,那天是从下午三点多辩论到六点多,直到你师母端出煨肉汤让吃晚饭。’”[6]
吴、何关于《红楼梦》的争论,当时并没有写成文章,主要发生在课堂和客厅,但对当时听课的学生影响极大,多位学生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此事。
二

吴组缃研究《红楼梦》的经典论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就是在1955年讲授《红楼梦》的讲义的基础上增补、修改而成,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在讲义中都已经提出。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共三万六千多字,正文之前有“内容提要”:“前言——贾宝玉性格的形成——贾宝玉性格的发展——贾宝玉性格的矛盾与限制——作者的处理态度与了解——结语”。[7]提要精炼地概括了全文的主要内容。
论文分十四节,并不是每个问题一节,作者根据问题的大小,分别用两节或三节完成。题目叫“论贾宝玉典型形象”,实际上涉及到《红楼梦》的中心事件与主题(第一节),贾宝玉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第二节、第三节),贾宝玉性格的发展过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贾宝玉性格的主要特征(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贾宝玉性格的矛盾与限制(第十节,第十一节),作者对于贾宝玉的态度(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贾宝玉性格的民主主义的因素(第十四节)。

《吴组缃文选》
这些内容与讲义中“《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贾宝玉的典型形象”这一专题基本相同,通过讲义与论文章节的对照可知,二者其实就是初稿与定稿之间的关系。
吴组缃关于贾宝玉与《红楼梦》的一些重要观点,讲义中都已提出。
在讲义“《红楼梦》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倾向性”专题中,吴组缃写到:“《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婚姻悲剧。这是《红楼梦》悲剧的中心事件。”
这是吴组缃对于《红楼梦》主题的基本认识。这段文字,吴组缃移到了论文的开头,只是在“婚姻悲剧”之前加上了“恋爱”二字,对《红楼梦》的悲剧概述得更加准确。
讲义在写“贾宝玉的典型形象”之前,批评了当时《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有关《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与论文中,常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见解出现:如说,研究《红楼》,不可忽略了人物描写以外,如何表现反封建的思想,如何反映社会问题。他们不只如此说,而且实际是取了这样的研究途径。报刊上有不少的文章,就采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比如从《红楼》中举出枝节事例,说明作品中如何暴露贾家的奢侈,一顿饭花二十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举出一些数字,证明贾家如何剥削农民血汗等等(乌进孝送地租),当然这些是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参考的,不是说,这样举例,就不允许,但是,一个贵族、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生活总是比平民百姓为奢侈的,他们总是要剥削与掠夺人民的,若是一部《红楼梦》,只证明了这个,只提供了这些死的数字和事例,那这部作品有何伟大?”
<img border="0">
这是吴组缃对当时的红学研究中存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清醒认识和严厉批评。这一段文字,吴组缃也写入了论文,只是作了修改,文字更为简洁。
为何要研究贾宝玉的形象?与他在书中的地位有关。
吴组缃在讲义中写到:“任何作品中的人物,是有主次从属之分的。《红楼梦》中的重要中心人物应该是宝、黛及钗,因为书中以三人婚姻问题为中心事件,《红楼梦》悲剧是以此三人为中心,《红楼》的主题思想,所反映的矛盾斗争,所提出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从这三人的思想性格上和关系上引起来的。而宝玉又是三人中之最重要的中心人物,即在书中居于主人翁的地位。”这段文字也在论文第一部分可以找到。
吴组缃分析贾宝玉形象,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贾宝玉的性格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在讲义中也明确提出来了,他说:“宝玉如现实中的一个小孩,他的思想是发展的。”论文中,只是将“小孩”改为“人”。
讲义中,在写贾宝玉的典型形象之前,吴组缃对于“宝玉形象的特征”有一个提纲式的概括,共六点:“1、对于女性的尊崇(男性自卑)。2、对于下属微贱人物的同情与亲近(阶级自卑)。3、对于个人意志的尊重(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要求)。4、对于封建秩序的反□与叛逆(对兄弟、对伦常、对功名富贵)。5、对于爱情的要求之内容(知己、专一、深挚)。6、对于纯真、美好与高洁的事物的倾慕。”
而在正文中集中写了两点:
第一,“贾宝玉思想性格最初的也是突出的两个基本特点,就是对于男性的厌恶和对于家庭出身的厌恶、自卑,这两方面其实是相连的,不可分的,即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否定。”“《红楼梦》中一开始就非常强调宝玉对男性的厌恶与由此相应而生的对于女性的崇敬与同情。”“宝玉对于家庭出身的厌恶或阶级自卑以及对于处于寒素与微贱的下层人物的亲密与好感,也是很突出的。”

第二,紧接着便分析贾宝玉这种性格的意义:“宝玉对于这些处在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与奴役、侮辱与损害、轻视与贱视的地位的人的亲近与尊重、倾慕与爱护,另一方面,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权思想或人道观念,换言之,即人权平等、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要求,所谓民主主义思想,这些就是重要的因素。”“这种思想,自然与封建主义相抵触,是直接破坏封建秩序。”
正文中,吴组缃将提纲中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揉在一起写,而将第三点和第四点作为宝玉形象的意义来论述。第五点和第六点则没有涉及。
在论文中,吴组缃主要论述了三个方面。
第一,“贾宝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
第二,“贾宝玉还有一种意识,那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家庭或阶级阶层的憎恶,以及与此相应的对于有些比较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
第三,进而分析贾宝玉性格的意义:“综观上述贾宝玉思想的这些特点——即一方面对自己出身的本阶级抱着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一方面对他所接触的生活环境中居于被压迫地位的人物——尤其是女孩子们则给予尊重、同情和无限亲爱体贴之心: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初步的民主主义精神。”[8]
从提纲到讲义,再到论文,吴组缃对于贾宝玉思想性格及其意义的概括,可谓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有些问题弃而不谈,有些问题加强论证,最终清晰地表达出吴组缃对于宝玉形象的认识与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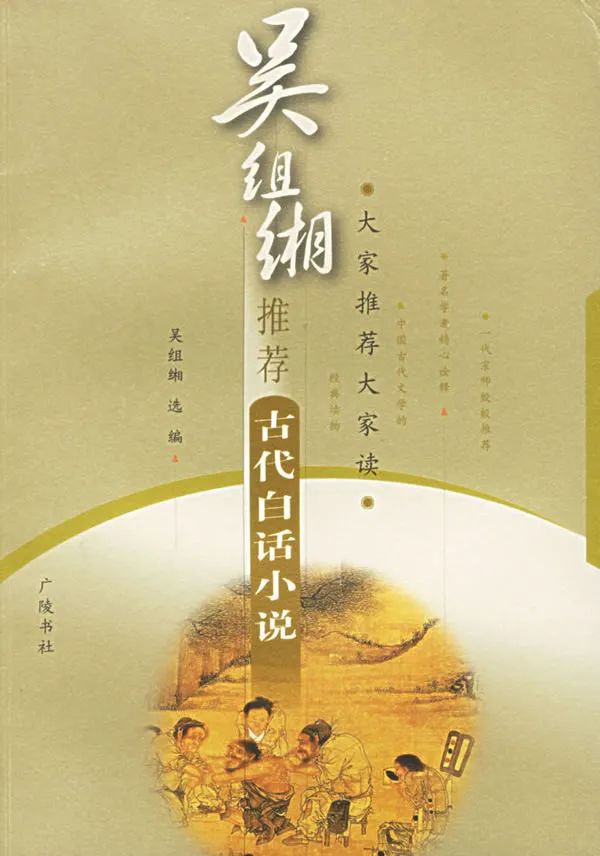
《吴组缃推荐古代白话小说》
吴组缃认为,贾宝玉形象存在明显的局限,讲义写到:“我们从上面的说明中,已经可以看到宝玉形象所反映的民主主义思想特征的限制性。他反封建的立场很坚定,不妥协,不调和,不相容的。但同时又显得很幼稚,很不成熟,很软弱,看不到胜利的未来,只是一片暗淡的前途。”
“贾宝玉性格上这种显著的缺点,根源于一个问题,即他的主观思想里,虽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否定了衰败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社会,但并未能否定君权和亲权,即封建主义的统治权。这是贾宝玉的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这个思想问题,使他的斗争带着阴暗成分和悲剧色彩。”
这一观点,吴组缃稍作修改,也写进了论文中。
吴组缃第一次讲授《红楼梦》的讲义,写于1955年秋季,1956年春夏修改,论文最后注明了修改时间,“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补毕”。1956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四期发表。也就是说,吴组缃的讲义和论文的写作,与何其芳的“打擂台”没有关系。

《史诗红楼梦》,何其芳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版。
吴组缃与何其芳同时讲授《红楼梦》在1956年秋季,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写于1956年下半年,论文后面也有写作时间的记载:“1956年8月至9月初写成前八节,10月至11月20日续写完。”1957年5月,在《文学研究集刊》第五辑发表。何其芳的论文写于吴组缃的论文之后,又在吴组缃论文发表之前。
吴组缃的讲义和论文《论贾宝玉典型形象》都没有与何其芳商榷的内容。直到1963年5月,应邀到宁夏大学讲学,演讲稿由陈新记录整理,发表在《宁夏文艺》1963年第4期,题为《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在这篇演讲稿中,我们看到了吴组缃批驳何其芳观点的文字。报告开篇就说:“对于《红楼梦》,向来有人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写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一个写封建统治阶级的崩溃。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不像鸡蛋那样,可能有双黄蛋,它是一个黄,一个主题。《红楼梦》主要是通过主人翁的恋爱婚姻悲剧,表现产生这个悲剧的原因。”[9]
这一批评就是针对何其芳的观点而发。何其芳在《论红楼梦》中写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是《红楼梦》里面的中心故事和主要线索。然而全书所展开的生活是那样广阔,远不只是写了这个悲剧。……它写了宁国府和荣国府这样两个封建大家庭,主要写了荣国府。也可以说,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发生的环境。然而,它却又并不是把这两个家庭仅仅当做背景来写,这也正像生活本身一样,在真实的生活中许多人物和事件常常是互相联系而又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我们难于把它们仅仅当做某一部分的背景。”[10]
这就是吴组缃所说的“双黄蛋”。因为何其芳写作《论红楼梦》和在北大讲授《红楼梦》的时间都是在1956年下半年,论文的观点与课堂讲授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何其芳批本红楼梦三种》
1963年12月29日,何其芳应北京大学团委会和学生会的邀请,作了《<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他对《红楼梦》主题的看法:“过去,有些《红楼梦》的研究者把爱情摆得太高,认为《红楼梦》的主题就是爱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荣宁二府的兴衰和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悲剧来批判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爱情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据有人统计,描写爱情的部分,还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贾宝玉考虑的也不只是爱情,而是有很多方面。认为《红楼梦》就是写的爱情,是‘爱情的颂歌’,这是贬低了《红楼梦》的价值。《红楼梦》是伟大作品,而伟大作品就没有一部是专写爱情的,它必然写到广泛的社会生活。”[11]
何其芳批评的就是吴组缃的观点。
另外,在宁夏大学的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吴组缃对于薛宝钗的评价,“有人说,薛宝钗一脑袋的封建思想,是个典范的封建淑女。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且看《红楼梦》如何描写。在二十二回以前,作者写薛宝钗老是跟着宝玉转,每当贾宝玉、林黛玉在一起时,紧跟着总是‘宝姑娘来了’。用北京的土话说,叫做‘夹箩卜干儿’。论理,像宝钗这样的人,应该成天跟着李纨、迎春、探春、惜春等人才是,现在成天跟着宝玉转,这又算得个什么封建淑女!”[12]

《论红楼梦》
这一段也是批评何其芳的观点。
何其芳认为,“书中写她(薛宝钗)‘稳重’,也即是拥薛派所说的‘端重’,写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种或者可以说是她的性格上比较突出的特点也正是符合封建主义所提倡的淑女的标准的。”[13]
“薛宝钗主要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因而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来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14]
这些互相商榷的内容,大多发表在1956年秋季“打擂台”之后,也应该是当年课堂上讲授的内容,从听过吴组缃和何其芳同时讲授《红楼梦》的李厚基、刘绍棠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刘绍棠说:“后来,我听了他(指吴组缃)的讲座课。他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同时讲《红楼梦》。那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哲学楼,也受北大领导。何、吴二先生本是同窗好友,又都是红学名家,同时讲学,共讲一个题目,很像梅(兰芳)程(砚秋)唱对台戏。何、吴二位先生的讲座我都听了。”[15]
刘绍棠用梅程对台戏比喻吴组缃和何其芳的《红楼梦》专题课,讲授内容肯定有彼此之间的商榷与驳难。
三

吴组缃的《红楼梦》专题课与论文,不仅吸引了一批学生听课和阅读,而且培养了一批从事《红楼梦》研究的学者。

《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吴组缃的博士生刘勇强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吴先生主要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撰写了《<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等一批至今仍有影响力的论文,并培养了大量文学研究的学术人才,一时间古代小说史领域的贤俊硕彦,多出于先生门下或曾受先生沾溉。”[16]
这批“贤俊硕彦”可分两类:
一类是吴组缃指导的研究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指导的研究生有程毅中、赵齐平、李厚基、齐裕焜、李灵年、张菊玲、孙文光、李银珠、李有德等。
程毅中原为浦江清的研究生,因蒲先生病逝,转到吴先生门下。
齐裕焜本来安排吴小如指导,因吴小如当时是讲师,上报教育部时,导师为吴组缃。
八九十年代指导的博士生有张国风、刘勇强、张健。张健研究古代诗论,由吴组缃和张少康两位导师指导。

《红学探索:刘世德论红楼梦》
另一类是听过吴组缃的《红楼梦》和古代小说课的本科生,包括刘世德、周兆新、沈天佑、刘敬圻、朱彤、李汉秋、黄岩柏、陈熙中、张锦池、周中明等。
刘世德于1955年已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文学所就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哲学楼,有机会听完吴组缃的《红楼梦》课。[17]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编写《中国小说史稿》,指导教授为吴组缃,参编学生有张菊玲、黄岩柏、闵开德、李汉秋等。[18]上述学生中有十几位后来成为以研究《红楼梦》著称的学者。
这批学生不仅仅是听过吴组缃的课,接受过吴组缃的指导,而且从学术观点到研究方法都受到吴组缃的影响。
张锦池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级学生,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红学论文《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就是吴组缃指导的学年论文。
据张锦池回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便是在吴老的指导下写成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篇论文的写作,吴老教给了我治学的方法,使我受用到如今。”[19]
关于薛宝钗的形象特征,是吴组缃与何其芳的争论焦点,张锦池概括为,“一派认为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是封建道德的虔诚信徒;一派则认为薛宝钗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淑女,而是一个典型的女市侩。”[20]
前者是何其芳的观点,后者则是吴组缃的观点。张锦池认为两派都有点“偏颇”,提出了“薛宝钗性格”,“简言之,貌似温柔,内实虚伪;看来敦厚,实很奸险;随时而不安分。或者说: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21]

张锦池《红楼梦考论》
张锦池毫不讳言,“拙作《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便是取舍于二者之间而略参己意。”[22]张锦池看似综合了两人的观点,从其表述来看,明显更倾向于吴组缃的观点。
吴组缃不只是指导张锦池完成了学年论文的写作,而且教给他做学问的方法,据张锦池回忆:吴组缃对他提出来四点要求,“一是要读一点清史,把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二是要再读两遍《红楼梦》,把薛宝钗这一典型性格放到整个《红楼梦》的形象体系中研究;三是要同时研究一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特点,把薛宝钗与贾宝玉和林黛玉作对比考察;四是要好好阅读一些有关评论文章,既要虚心吸收其成果,更要勇于标新立异。”[23]
正是吴组缃的悉心指导,张锦池在写完学年论文之后,还“情不自禁地撰写了《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一文的初稿。”[24]
《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也能看到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的影响。吴组缃认为,贾宝玉的思想性格的形成,与他的生活环境和具体遭遇又密切相关。宝玉的生活环境,“区分为两个互相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罪恶腐败势力,一边则以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女孩子们为主——无论她们的主观思想如何。”[25]

《红楼管窥:张锦池论红楼梦》
张锦池说:“贾宝玉所生活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便是这样一种现实。它一经作者的艺术处理,遂形成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一边是居于统治地位作威作福的男子,一边是居于被压迫被牺牲地位的少女。”[26]
吴组缃指出,贾宝玉的性格有一个发展过程。张锦池提出,“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但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其具体的发展历程。”[27]并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从观点到语言,都能看到吴组缃论文的影子。张锦池的三篇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公开发表,奠定了张锦池在红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沈天佑于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长期担任吴组缃的助教。读书期间听过吴组缃的《红楼梦》专题课和其他古代文学课程;工作期间,从教学到研究都得到了吴组缃的细心指导。
沈天佑曾深情回忆吴组缃给他修改讲义的情景:“我写好讲稿后,总先送给老师看。老师对我的讲稿看得那么的细致认真,在讲稿上批上很多话:这点讲得好,这点欠妥等等。老师还把自己的讲稿给我们看,要求我们提意见。”[28]
吴组缃的一些学术观点为沈天佑所接受,并撰文作进一步的论证。
王熙凤是一个市侩的观点,最早是吴组缃提出来的。吴组缃《在第六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说:“王熙凤正是个市侩主义者,什么孝道、贤德全都不讲;把丈夫也踩在脚底下,抓得紧紧的。丈夫另外搞女人,她就同他打闹;她自己在男女关系上却乱七八糟。”[29]

《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
这一观点,他应该在《红楼梦》专题课上早就讲过。沈天佑对老师的观点烂熟于心,他在《论王熙凤和市侩主义》一文专论王熙凤的市侩主义性格特征。其“表现之一是在处世态度上的圆滑、狡诈和凶狠。”“另一鲜明表现是对财富的热衷追逐。”“还表现在全然不顾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种种束缚和禁锢,恣意地追求享乐,努力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王熙凤的“聪明、能干被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市侩主义油彩。”她的“聪明、能干集中地表现在富于权术和机变。”[30]
如果说吴组缃对王熙凤的市侩主义性格作了定性,沈天佑则对王熙凤的市侩主义性格作了细致的分析。
沈天佑的《谈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一文几乎就是吴组缃论文《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中谈刘老老一节的扩充和细化。
在吴组缃的论文中,刘老老只是所论四个陪衬人物之一,只有两千多字,主要分析刘老老形象的意义,一方面,“她让我们从最低洼的地方——乡村里的破落户——来看山的。”“通过她所经验的一些日常琐事和生活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贾家的‘贵’(生活享用和势派)。”另一方面,“作者安排刘老老进来,正要从一个最好的角度、从最尖锐的性格对比里,来揭示贾母和王熙凤的思想性格特征。”[31]

《宋元文学史稿》
沈天佑的论文详细分析了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的不同作用。“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主要是突出这个国公府的威严和势派。”“二进荣国府的重点在于全面、深入地揭示这个贵族之家的奢靡和挥霍无度,表现出它在走向没落时的回光返照。”“三进荣国府时,其情景和上面两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显赫一时的国公府已陷入绝境,到处是一派凄凉败落的景象。”[32]
周中明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在高校从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他说:“我之所以毕生从事于元明清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我对《红楼梦》和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我教学的内容和风格,都受吴先生的影响很大。”[33]
周中明研究《红楼梦》,侧重于人物分析和艺术鉴赏,他对薛宝钗形象的分析,明显受到吴组缃和何其芳争论的影响和启发。
他既不同意吴组缃的观点:“这一切难道只是为了表现宝钗的阴险奸诈,对黛玉进行感情拉拢和物质收买么?如她果真有意要跟林黛玉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何不给林黛玉制造难堪,对她进行精神折磨,促使多病的林妹妹早死,而却相反地给她以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呢?”[34]也不赞成何其芳的观点:“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私情,如此抑制不住地喷薄而出,这难道是‘封建社会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所能容许的吗?”[35]

《周中明文集》
进而提出:“曹雪芹的《红楼梦》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写法。它既不是把薛宝钗写成‘全坏’,也不是把她写成‘全好’,而是把她写成亦好亦坏,既丑又美。作者采用化美为丑、化丑为美的办法,着力写出她生来就具有天然美,只是在许多方面被那恶浊的社会环境污染成世俗丑;这种世俗丑并未能湮灭她的容貌、学识、才能等方面所具有的动人的美,而且最后其人又被整个社会环境的‘丑’所毁灭。”[36]
尽管周中明没有引述吴组缃和何其芳的观点,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吴何之争的烙印,熟悉红学史的人都知道,当代最早为薛宝钗的评价问题产生激烈争论的就是吴组缃与何其芳。
当然,吴组缃的教学与研究对当代学术的影响并不限于红学领域,他在北京大学还讲过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等专题课,程毅中、齐裕焜、黄岩柏、刘勇强的小说史研究,李汉秋、张国风的《儒林外史》研究,李厚基、李灵年的《聊斋志异》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吴组缃的影响,这些问题非本文所能一一解决。

《吴组缃全集》
一位大学教授,指导一批研究生,将他们培养成为研究方向大体一致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团队,这在当代学界并不少见。像吴组缃这样,给本科生讲授专题课,培养出一批学术兴趣相同、学术风格相近的学者,在学术界可不多见。这固然与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和吴组缃所处的时代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吴组缃的精深的学术造诣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本写作,得到齐裕焜教授、刘勇强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1] 石昌渝《吴组缃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2] 方锡德《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
[3] 吴组缃《在第六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1页。
[4] 張相儒《我们大家都倾心向着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07-108页。
[5] 李厚基《吴组缃先生教我们读<红楼梦>》,李厚基《红楼梦与明清小说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年,第107页。
[6] 张锦池《忆恩师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40页。
[7]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05页。
[8]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05页。
[9] 吴组缃《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67页。
[10] 何其芳《论红楼梦》,《何其芳论红楼梦》,白山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11] 《<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89页。
[12] 吴组缃《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79页。
[13] 何其芳《论红楼梦》,《何其芳论红楼梦》,第33页。
[14] 何其芳《论红楼梦》,《何其芳论红楼梦》,第34页。
[15] 刘绍棠《敬悼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53页。
[16] 刘勇强《嫩黄之忆·后记》,《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第513页。
[17] 参见刘世德《何其芳论红楼梦·序》,《何其芳论红楼梦》,第1页。
[18] 参见张菊玲《永念师恩》,《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66页。李汉秋《吴缘》,《嫩黄之忆——吴组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第216页。
[19] 张锦池《忆恩师吴组缃教授》,《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37页。
[20] 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249-250页。
[21] 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红楼十二论》,第250页。
[22] 张锦池《忆恩师吴组缃教授》,《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40页。
[23] 张锦池《忆恩师吴组缃教授》,《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37页。
[24] 张锦池《忆恩师吴组缃教授》,《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38页。
[25] 吴组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12页。
[26] 张锦池《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红楼十二论》,第156-157页。
[27] 张锦池《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红楼十二论》,第191页。
[28] 沈天佑《沉痛悼念吴组缃教授》,《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220页。
[29] 吴组缃《在第六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317-318页。
[30] 沈天佑《论王熙凤和市侩主义》,《沈天佑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95页。
[31] 吴组缃《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第262页。
[32] 沈天佑《谈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沈天佑文存》,第343页。
[33] 周中明《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巨人》,《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第176页。
[34] 周中明《红楼梦的艺术创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35] 周中明《红楼梦的艺术创新》,第106页。
[36] 周中明《红楼梦的艺术创新》,第83-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