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书念得不是很好,可运气好。高中时偏科严重,数理化成绩都只在及格线的边缘上。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大学扩招,号召在机关、军队中的青年知识分子报考大学。考虑到他们理科基础差,所以当年考文科的考生都不考数理化和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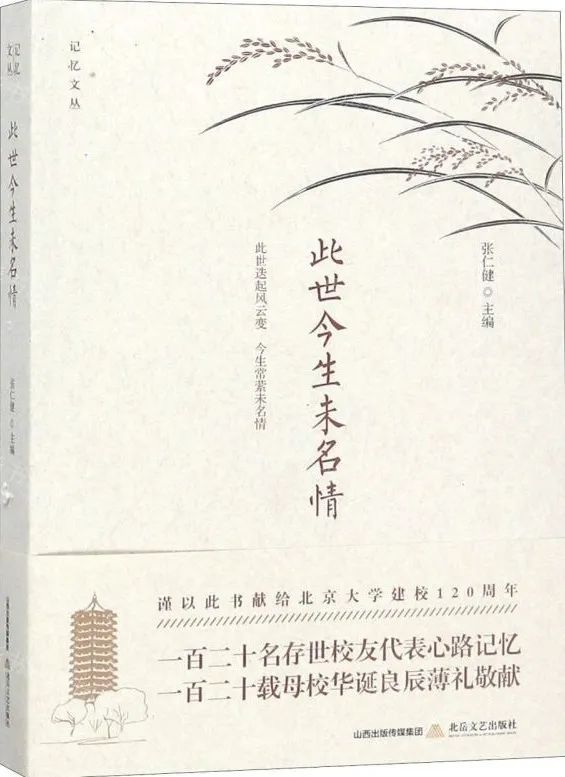
《此世今生未名情》
这对我是天大的福音。我文科成绩好,于是顺利地考上北大中文系。当时如果加一门理科或外语的话,我肯定就无缘北大了。
经过四天奔波,我从海防前线福州到了北京。到北大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工作人员领我们去宿舍,一座平房,20个男同学住一间大房间,架子床。旅途劳累,我就躺下呼呼大睡。
后来,觉得有人揪我的头发,原来是睡在上铺的刘烈茂,他说:“你这个小家伙,怎么打呼打得这么响!”从此我在美丽的燕园度过了十八岁到二十七岁这段最难忘的青春岁月。
我的北大九年(1956年9月至1965年7月),是波诡云谲的九年。1956年入学时大家意气风发,埋头苦读;1957年5月起,风云突变,先是反右运动,接着是1958年大跃进,参加修十三陵水库,大炼钢铁、深翻地,批判学术权威、大搞集体科研。
1959年底开始困难时期,逐步调整政策,没有劳动和政治运动了,我们又埋头苦读;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又开始折腾,到平谷县劳动,写公社史;1964年10月到湖北江陵参加社教运动,1965年5月回校,集体写批判《三家巷》的文章,研究生就算毕业了。
大学五年(当时学制五年)、研究生四年(学制是三年,因为参加“社教”延迟了一年),共九年,用于读书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五年到六年的时间。
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因此,我在一篇文章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师辈,有着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底,因而在学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的学生辈,现在条件好,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精力充沛,时间充裕,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而我们这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处在愧对前人,羞见来者的尴尬局面里。”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毕竟我是在北大,她有科学、民主的优良传统,有全国名校的特殊地位,有群星灿烂的师资队伍,有素质较高的学生群体。北大九年我受到北大精神的哺育,打下了终生事业的基础,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杨晦评传》
想起燕园,北大人都有很深情结。今天,我回忆起几位名师轶事,他们的风采和北大学风,依然那么清晰、生动。
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闯将,作家、文艺理论家,他和冯至等人组织的“沉钟社”是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社团,他的剧作、翻译作品也有一定成就,特别是《曹禺论》得到广泛的赞誉。
作为学生,我和他没有很多接触,但仅有的几次接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和几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去他家反映对教学的意见和请教如何做学问。他反复强调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求成。
他非常推崇浦江清先生的论文《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因为浦先生用精深的天文学知识解决了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纠正或补充了从王逸、朱熹到郭沫若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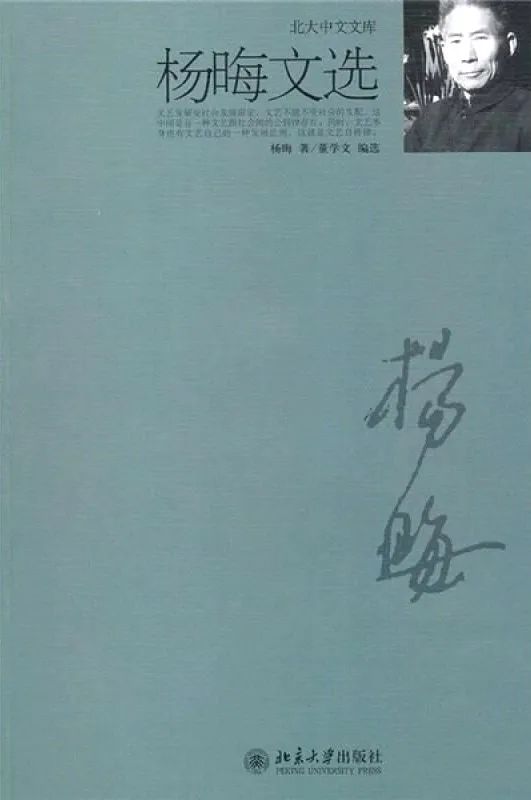
《杨晦文选》
接着他尖锐批评姚文元和李某某,说他们到处写文章,他们的学问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是要跨掉的(以上这些见解,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据说,“文革”中,这成为杨先生的一条罪状,说他污蔑了被江青称为“无产阶级金棍子”的姚文元。
“反右”之后,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上面提出教师要集体备课、写出完整的讲稿,甚至要审查讲稿。而作为系主任的杨先生不但没有认真执行,还唱起了反调。他说大学老师要发挥他们的专长和独特的见解,怎么能集体备课?怎么能拿着讲稿去照本宣科?写一个讲课提纲去讲就是了。
杨先生上《中国文艺思想史》课,“禹铸九鼎,使民知神奸”,就讲了好几节课;他用了半个学期来论证他的观点——《西厢记》的作者是关汉卿而不是王实甫(《再论关汉卿》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回忆燕园,最不能忘却的,当然是我的两位研究生导师“大吴先生”和“小吴先生”,他们都是安徽泾县人。两位吴先生我有回忆他们的文章,这里就不全面介绍,只说几件事吧。
吴组缃先生的文学研究,视野开阔,把握时代思潮,从宏观上分析作品,如《〈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论贾宝玉典型形象》等论文,就是从时代的高度,宏观地深刻论述经典名著,成为学术史上的宝贵篇章。
他又是著名作家,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能从微观上对作品作精妙细致的赏析。他说读名著就像品好茶,要慢慢品味,而不能作“牛饮”;他又说就像吃橄榄,要含在嘴里才能慢慢尝出味道。只有精细阅读才能真正领会经典作品丰厚的内涵和艺术的奥妙。
如他分析《王桂庵》,说这篇作品通过一个痴情而又不脱世家子弟轻浮毛病的王桂庵与一个珍惜爱情、追求纯洁感情的贫家女子的对比,写出了两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下,足以显示蒲松龄的伟大。

《吴组缃小说课》
他细致分析作品,如王桂庵为挑逗芸娘,先是吟诗,继之以财诱之,“以金锭一枚遥投之”,芸娘“拾弃之,若不知为金也者”,后来又投金钏,“堕足下,女操业不顾”,可是当她父亲来时,王桂庵急坏了,但是“女从容以双钩覆蔽之”。
吴先生特别欣赏这个情节,因为它反映了芸娘复杂的心理活动。对王桂庵的挑逗,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同时,对王桂庵也有好感,怕父亲伤害他,如她后来所说:“使父见金钏,君死无地矣!妾怜才之心切否?”
吴先生的比喻特别精彩,我们研究生毕业考试,我和李灵年等人都得了“优”,但吴组缃先生批评我,他说,树上有三只鸟,李灵年用三发子弹就把他打下来了,你也把鸟都打下来了,可是用了十发子弹。
他的比喻也给他带来麻烦,他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像母亲对孩子,先打了一下屁股,后来又给一颗糖吃。于是“反右”时被取消了中共预备党员,到“文革”后才恢复了党籍。
说到吴小如先生,众所周知,他学问渊博,在小说、诗歌、戏曲、散文等各方面都有建树。《读书丛札》《吴小如戏曲文录》等著作蜚声海内外。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还翻译了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

《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
像他这样的全才,是极为罕见的。如我同窗好友彭庆生所说是“乾嘉学派之鲁殿灵光”。陈丹晨学兄说他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吴先生还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救火队”,什么课没人教了,就叫他顶上,如浦江清先生去世了,词、曲方面的课程就由吴先生来教;要开《工具书使用法》还是吴先生上,而他都能胜任,教学效果极好。
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先生都很赞赏他。“吴小如虽是讲师,完全可以当研究生导师”,是系主任杨晦一锤定音,我成了他一生唯一的正式的研究生。但是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他当了28年讲师,最后愤然离开中文系,阻力究竟来自何方?
他对学界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尤其是对缺乏最基本的古代文化修养而又大胆妄为地标点、注释古书的人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为民族文化的健康大声疾呼。这也为我敲了警钟。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读书笔记把“光芒”写成“光茫”了。他指出后,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这么普通的字都写错了!从此,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注释古书;不写没有把握的文章;上课时不要写错板书,念错字。
我在上学时和语言学方面名师接触不多,但还记得一些轶事。
我们《古代汉语》是杨伯峻先生教的。他是著名学者杨树达的侄子,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拜国学大师黄侃为师,成为“黄门弟子”。
解放初,他曾任湖南《民主报》社长、湖南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我们的时候是副教授,中共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委员。

《杨伯峻治学论稿》
他教古汉语是用他刚出版的《文言语法》作教材。他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方面有重要贡献。时隔60多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杨柳岸晓风残月……”,他那带有湖南口音抑扬顿挫的朗读,让我至今难忘。
1957年6月底,杨先生给我们出卷子考试,并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开学时听说他成了“右派分子”,调到兰州大学去了。
戴着右派帽子去,当然日子不好过,甚至连著作的署名权也被剥夺了,他的《孟子译注》出版时,署“兰州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直到1980年左右,中华书局致函兰州大学中文系,要求作者改署为杨伯峻。我们召开全系教工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孟子译注》本来就是杨先生的著作,当然应该署他的名字,所以1982年以后出版的《孟子译注》就改过来了。
因为我在兰州大学工作,对杨先生在兰州的悲惨遭遇,有所了解。1959年到1960年,全国处在极为困难的时期,而甘肃省尤其严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荒唐的口号就是甘肃提出的。“共产风”、浮夸风,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更为恶劣的是还在欺上瞒下,说农业大增产、粮食大丰收,直至农村饿死不少人、城市里也以野菜充饥,此类谎言才被戳穿,中央撤了省委书记的职,紧急从新疆调运粮食救济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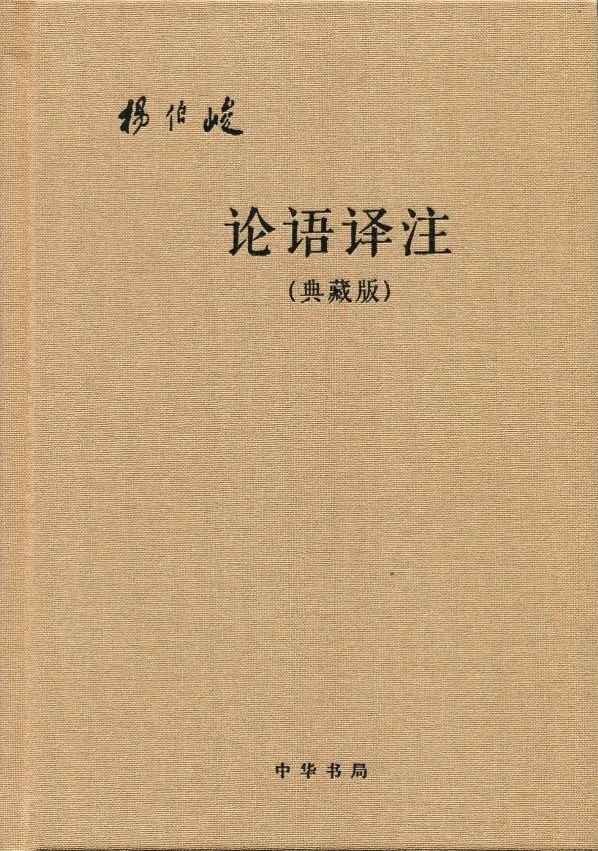
《孟子译注》(典藏版)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时候杨先生又得了重病,生命垂危。1960年,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把他调回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位杰出的学者才得以“保存”下来,也才有后来的《春秋左传注》等重要著作,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我们的《语言学概论》是高名凯先生教的,他把比较枯燥难懂的语言学理论讲得生动有趣,课堂上笑声不断。我只记得他说到语言是信号,引起条件反射,一说现在下课,你们就联想到食堂的红烧肉,同学们大笑。
我从高先生说话的口音,觉得他可能是福建人,后来才知道他是福建平潭人。平潭是个小海岛,过去交通极不便,是一个贫穷、荒凉的地方,现在因为它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地方,成为闽台交流往来的窗口,成立了综合实验区。它离福州近,风景好,所以有外地学者来,我常陪他们去。
我常想,当时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走出高先生这样一个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大学者?高先生有《汉语语法论》《普通语言学》等重要著作,还是翻译家,不但翻译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等重要语言学著作,还翻译了巴尔扎克20多部小说,真是一个奇才。
朱德熙先生教《现代汉语》,记得朱先生在课堂上讲到词组动宾结构,说到语法规律和语义矛盾时说过“吃”字。“吃饭”是正确的,从语法结构说“吃大碗”,“吃二两”应该都是正确的。虽然语义关系上有不同,但不能说语法不正确。那么“ 吃亏”呢?“亏”怎么吃啊?哄堂大笑。

《朱德熙文集》
在关于燕园的记忆里,不仅有老师们的点滴趣事,也有老师挨批的心酸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而来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而在北大校内则是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学术阵地”的运动。老教授们,经过“反右”,惊魂未定,接着又受到更让他们痛心的批判,他们为之呕心沥血,引以为荣的学术成就被说得一钱不值。
我们年级四个班作了分工。一班批判王力先生,二班批判林庚先生,三班批判王瑶先生,我们四班批判游国恩先生。游先生是《楚辞》研究的权威学者,当然要从批他的楚辞研究入手了。
当时的批判是再简单粗暴不过了,比如,游先生有一篇文章考证《九歌》中《山鬼》的故事来源。我们的批判非常简单,很得意地说,一句话就把他批倒了,因为鬼是不存在的,您的研究就是“伪科学”。后来当我写《中国讽刺小说史》,研究《平鬼传》《斩鬼传》里的钟馗形象的来源时,想起我们当年的粗暴和幼稚而感到汗颜。

《中国讽刺小说史》
当批判告一个段落之后,又传来周扬同志的指示,无产阶级不但要“破”,而且要“立”。我们班的任务是研究陶渊明。开头同学们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作家”,不劳动,还“悠然见南山”,应该否定;有人说,鲁迅说他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应该肯定。
后来要我们先编一本陶渊明研究资料集。于是,彭庆生等开始着手借书。当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借书非常容易,一封介绍信就把北京各大图书馆的书借回来了。
然后,我们班30位同学,人手一书,见“陶”就抄,不管他是“陶靖节”还是“陶彭泽”,也不管是什么内容,先抄下来再说。抄了几万条材料,就逐条鉴别,把有用的留下。依靠这样的“人海战术”,居然把陶渊明的研究资料收集得比较完整。
接下来是要把资料按年代先后排列,这可难住我们这些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因为有的人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年代,在《人名大词典》里也找不到。这时只好求助于“资产阶级权威”了。
游国恩先生没有因为我们班批判过他而生气,而是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表现了一个学者的博大胸怀和对学生的爱护。绝大多数人物,他都知道,马上告诉我们是哪个时代的人,哪一年中的进士等等,个别人物他回去查了一下,第二天就告诉我们。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才知道他们真是渊博。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
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任务,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和《陶渊明诗文汇评》两本书,现在合为一书,书名改为《陶渊明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的一种)。
拉拉杂杂地回忆些往事,已经写了5千字了,就此打住了,不知能否博朋友们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