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新《唐书》所载韩愈驱鳄鱼事,人多沿袭之,默认之。然早已有不以为然者,如宋释契嵩即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1]363

释契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韩愈若果真如此作为,则显然荒诞而不合情理。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诸家对所谓韩愈逐鳄鱼事过分恶评。如胡适谓:“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语,这更可鄙了。”[2]304
吴世昌谓:“既然说到韩愈在潮州的情况,自然令人想到那篇著名的《祭鳄鱼文》。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3]
郭朋说:“堂堂的一代大儒、朝廷命官,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当成谈判对象。要同他进行‘谈判’,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而最后那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的劲头,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道学家韩愈,竟是如此的迂滞,如此的迷信,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呵!”[4]356
近来亦多有不批评韩愈,而从韩愈的思想认识、信仰、文化背景等角度评论韩愈《鳄鱼文》、驱鳄事者。他们肯定韩愈曾作文以祭祀或讨伐鳄鱼。[5]
只有王仲镛[6]与丘述尧[7]两先生指出,韩愈《鳄鱼文》乃游戏文字,不必认真对待所述祭鳄、驱鳄之事。与上述诸作者意见有别。
鄙见如下:

一、韩愈《鳄鱼文》确是一篇游戏文字
诸批评韩愈者之共同点,是皆充满审视古代典籍之严正感与崇尚科学之精神,此则无可非议也。

但遗憾者,多缺少审视韩愈著作之幽默感——他们不知,韩愈《鳄鱼文》乃此老之游戏文字,却误以为记实;当然也未重视旧、新《唐书》作者将张读《宣室志》所载神话传说撰入正史。
批评者遂多将史书“作文驱鳄”之陋笔归咎于韩愈,而攻击其“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自我造神”——此类作为,适可戏仿《红楼梦》林黛玉女士嘲笑贾宝玉滥评其姊妹之诗以讥之:“无端弄笔是何人?笃信退之《鲛鳄文》。不悔自家无见识,却将丑语诋他人!”[8]
王仲镛如此回应吴世昌对韩愈的批评:
据我们看,这篇《祭鳄鱼文》,不过是象柳宗元的《骂尸虫文》那样一类的游戏文章。他遣人致祭,先礼后兵,我们说他卖弄文才,故弄玄虚,倒还可以。韩愈自己未必想借它作为鼓吹自己诚可通神的宣传品。至于鳄鱼,既为民害,最后对付它的恐怕还是“强弓毒矢”起了作用,才迫使它“西徙六十里”。
既然为人民作了好事,总会产生种种传说,柳宗元不是也被传为做了罗池神吗?鳄鱼远徙的神话,必然也是这样造出来的。
著《新、旧唐书》的宋祁、刘昫,一则素称好怪,一则鉴裁不精,这是早有定评的。他们杂采传说,写出本传,却不能由此反过去坐实韩愈的造谣。
不然的话,编纂《韩集》的是韩愈的学生李汉,他一定是习闻师训的,在《韩集》中,他把《祭鳄鱼文》和《毛颖传》、《送穷文》之类的游戏文章放在一起,称之为“杂文”。而在“祭文”一类中,则连《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龙文》都收了。
可见韩愈本来并不把“祭鳄鱼”看成一回什么郑而重之的事,他又怎么还会借此来制造神话,欺世盗名呢?[6]


笔者按,这一段文字判断之正确者,是《鳄鱼文》乃游戏文章(亦称“游戏笔墨、游戏文字、游戏之作”),故编纂《韩集》之韩愈学生李汉,将《鳄鱼文》与《毛颖传》、《送穷文》之类游戏文章置于一处,称之为“杂文”[9]436。
以情揆之,此文应是韩愈莅任潮州刺史后,理事之暇自娱自乐之文。为可乱真,故作义正辞严,寓谐于庄,夸天子之威风,消刺史之块垒。
读者会心哂之可也,谓之多事可也,仿之戏作可也,一笑置之亦可也;以为确有其事而赞其行、惊其神固不可,以为确无其事而斥其谬、嗤其妄独可哉?不皆几乎牛心如堂·吉诃德者,指风车为敌方勇士,能无触碰而不头破血流乎?
一时为聪明所误而指谪嘲笑韩愈者如胡适等文人,令人欲引用其嘲骂之语“请君入瓮”:真是“拙劣可笑,无聊之极”,“竟是如此的迂滞,如此的迷信,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呵!”
载藉可见者,大凡学问“绝类离伦,优入圣域”之文人,必多有超凡之异趣,时或发为游戏文字,以抒雅怀,以寄逸致。故荀卿撰《赋篇》以伏隐语,扬雄赋《解嘲》以抒胸臆,枚乘设《七发》以振太子,陶潜拟桃源之境,活龙活现——而南阳刘子骥欣然规往,岂非痴哉?
韩愈戏撰讨鳄之文,人或赞其精诚通神,或嗤其夸诞诬枉,不皆妄也?必以韩愈《鳄鱼文》坐实其于潮州除鳄鱼之事,不几于以其《毛颖传》所载管城子老而见疏事责秦之少恩,而讥陶潜之虚构理想国桃源仙境,因误陷高尚士刘子骥之一命也哉?此必贻笑于大方也!

今补充王仲镛说:《韩集》中有《潮州祭神文五首》——祭太湖神三首,祭城隍神、界石神各一首——皆韩愈赴潮州刺史任后所作,是其认真恭敬之真祭神文。[9]316韩愈学生李汉于此中独不收《鳄鱼文》,证明其根本不以此篇为其师真祭神物之文也。
另外,王仲镛指新、旧《唐书》作者宋祁、刘昫“一则素称好怪,一则鉴裁不精”,固是。
由于旧、新《唐书》皆属官修正史,影响颇大,而大学者、大文学家苏轼又偏偏于《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赞扬韩愈“能驯鳄鱼之暴”、“约束鲛鳄如驱羊”,[10]509于是天下学人多不能不从风而靡,信之不疑矣。
然而毕竟事涉神怪,荒诞不经,故后来又有不信者。然其人不懂韩愈是在写文章开玩笑(所谓“游戏文字”),故不批评史家刘昫、宋祁与文学家苏轼妄发无稽之言,却批评《鳄鱼文》之作者韩愈,是与刘昫、宋祁、苏轼等人同为此老所卖也:他们未尝料能拚一死而谏迎佛骨之儒学大师,甫被免死贬责烟瘴之地,旋即现其狡黠风趣之一面(当然亦因诸人有好奇炫怪之病,此则旧文人之陋习也)。
即使如见识超人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者流亦未能免俗,其诗《送潮州吕使君》亦曰“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11]225——其人虽不好怪,然亦为韩愈狡狯之笔所惑矣。
然而王仲镛文谓“至于鳄鱼,既为民害,最后对付它的恐怕还是‘强弓毒矢’起了作用,才迫使它‘西徙六十里’。既然为人民作了好事,总会产生种种传说,柳宗元不是也被传为做了罗池神吗?鳄鱼远徙的神话,必然也是这样造出来的”,盖王君以为韩愈真有驱鳄之事。
殊不知《鳄鱼文》既为游戏文字,其所谓驱鳄事亦子虚乌有。王君实仍未彻底识破韩愈《鳄鱼文》狡狯之笔,等于未完全承认韩愈《鳄鱼文》为游戏文字,而无意中“坐实了”旧、新《唐书》韩愈本传之部分说法,遂弄巧成拙,欲益反损,与己文为韩愈辨白之主旨相龃龉矣。

韩愈到潮州之后,上表宪宗,称潮州环境恶劣,“飓风鳄鱼,患祸不测”[9]458:其语庄重而涉“鳄鱼”者,仅此而已。
且其学生、友人兼同僚皇甫湜,于韩愈死后所撰《韩愈神道碑序》中,语及韩愈在潮州事,亦不过“贬潮州刺史。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等语而已,[12]189并未提及其“彪炳史册”之“驱鳄”伟业,此又为《鳄鱼文》乃韩愈游戏文字之一证也。
故凡不知韩愈《鳄鱼文》为游戏文字,而以认真态度作长篇大论以分析者,率皆上此老之当,而其论亦难着边际也。
当然,游戏文字亦往往有为而发。如韩愈之《送穷文》,借送穷鬼,以抒己屡穷而不遭时之感。不然,韩愈一超凡智者,岂喃喃呢呢,与穷鬼争语,最后竟理屈词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延之上座”乎?[9]434
与此同者,韩愈《进学解》,亦不过游戏文字——“国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而训之”,岂有如此无礼之狂生,先生言未既而笑于列者,谓“先生欺余哉”?且长篇大论,侃侃而谈,语涉揶揄,历数师短,至讥其妇子,必不然也。此不过韩愈借师生对话,以抒发自己虽不得重用,然亦心安理得之意,巧妙发泄未得高位之牢骚,又不得罪君王与宰相,而显示其高妙文才也(李汉列此文于“杂著”,杂著者,近于杂文也)。[9]186

又,丘述尧先生如此评《鳄鱼文》:
责鳄鱼“与刺史亢拒,争为雄长”,令“率其丑类南徙于海,以辟天子之命吏”,不听,“必尽杀乃已”……意在根据尊王攘夷思想,宣扬唐代天子威德,镇慑海蛮凶顽者和不安其份(不安溪潭)的人反侧为非之心,同时维护本身的尊严和安全。故曰:“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辟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是他治潮的策略寓言。
所以《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材、吴调侯认为“词严义正,是一篇讨贼文。”“全篇只是不许鳄鱼杂处此土,处处提出天子二字、刺史二字压服它,如问罪之师,正正堂堂之阵,能令反侧子心寒胆裂”。二吴虽也把此文看成祭文,却看出了文章精神。韩愈送刑部郑权节度岭南《序》:“蛮夷悍轻,易怨以变。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控制失所,依险阻,结党仇,机毒矢以待将吏……好则人,怒则兽。故常薄其征入,简节而疏目,时有所遗漏,不究切之,长养以儿子。至纷不可治,乃草剃而禽杀之,尽根株痛斩乃止。”[7]
他说“二吴虽也把此文看成祭文”,意思是不赞同此文是祭文。又谓“此文又用祭文形式开头,人们就以为韩愈曾祭鳄,是祭文”,“人多以此文为韩公游戏之作。其门人李汉编《昌黎集》,亦以之与《送穷文》为一类,朱熹则编为杂文类”。
察丘君语意,似乎祭文就不是游戏之作,而杂文可以是游戏之作。张煜文亦谓:“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13]
窃以为,游戏文字与祭文、檄文等并非对立、对等关系,而可以是包容关系。从写作态度上分,文学作品有严肃与游戏文字两类,祭文、檄文既可以是前者,亦可以是后者。以实揆之,《鳄鱼文》盖为一篇以游戏笔墨写成之讨鳄檄文。


二、神话作品《宣室志》是旧、新《唐书·韩愈列传》之蓝本
有关韩愈驱鳄之文,非始于后晋刘昫《旧唐书·韩愈列传》。丘述尧先生文谓,首先宣扬此事者,是离韩愈时代很近的张读,唐宣宗大中时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生于韩愈死后十年。其外祖父牛僧儒,著有《玄怪录》。
张读之书《宣室志》中记韩愈事三则,丘先生皆概述之。按,笔者亦曾考察《宣室志》中此类文字,三则之中,与“驱鳄”有关之事二焉。今细绎之。其卷之四谓:
吏部侍郎韩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贬潮阳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长者百尺。每一怒,则湫水腾溢,林岭如震。民之马牛有滨其水者,辄吸而噬之,一瞬而尽。为所害者,莫可胜计。民患之有年矣。
及愈刺郡,即至之三日,问民间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鳄鱼也。”愈曰:“吾闻至诚感神:昔鲁恭宰中牟,雉驯而蝗避;黄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鸟兽矣。”即命庭掾以牢醴陈于湫之旁,且祝曰:“汝,水族也,无为生人患。将以酒沃之。”
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为潮阳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盖谓此也。[14]45


值得注意者,唐张读比韩愈晚生六十余年,约当皇甫湜卒年、韩愈死后十年;而皇甫湜仅比韩愈晚生九年,其人待韩愈如师友,又为同事(愈为吏部侍郎,湜为工部郎中)。
且张读《宣室志》即述仙鬼灵异故事之传奇小说(书名取李商隐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不问苍生问鬼神”笔意),皇甫湜说与张读说,孰者更为可靠,必有能辨之者。
皇甫湜《韩愈神道碑序》中“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张读却改为“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鳄鱼稻蟹,不暴民物”。所改前二句自可通,不必细绎;后二句,皇甫湜谓“(潮州)遂生鲜鱼稻蟹,(韩愈之治)不暴民物”,张读却改作“鳄鱼稻蟹,不暴民物”。
若曰鳄鱼可暴民物,蟹可害稻,尚可通;然“暴民物”干“稻”何事?足见张读说之伪。皇甫湜《韩愈神道碑序》“鲜鱼稻蟹”,本说潮州物产,张读为证成己说,改“鲜鱼”为“鳄鱼”,谓为祸害,甚无谓也。
而后晋刘昫撰《旧唐书·韩愈列传》全用张读《宣室志》文,竟至不掩其迹:韩愈之游戏文字《鳄鱼文》本谓“恶溪之潭水(有鳄鱼)”,张读却谓“郡西有大湫,中有鳄鱼”,刘昫《旧唐书·韩愈列传》亦谓“郡西湫水有鳄鱼”;韩愈之文本谓“潮之州,大海在其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张读《宣室志》文却作“是夕,郡西有暴风雷……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亦随而徙焉。自是郡民获免其患”,而《旧唐书·韩愈列传》亦作“呪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是《旧唐书·韩愈列传》几乎全抄张读《宣室志》文,而撇开韩愈文“恶溪之潭水”“南徙于海”于不顾。[15]4203

《新唐书·韩愈列传》则袭刘昫旧传,作:“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16]5263则两《唐书·韩愈列传》之抄袭因循之迹,昭昭可知矣。
而复有可疑者:张读《宣室志》卷之五又有与韩愈、鳄鱼皆有关涉之另一事: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鳄,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
元和五年,一夕闻南山有雷震暴,声闻数百里,若山崩之状,一郡惊惧。里人洎牛马鸡犬俱失声仆地,汗流被体。屋瓦交击,木树颠拔。自戌及子,雷电方息。明旦往视之,其山摧堕,石壁数百仞殆尽,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满四野,蛟鳄之血,遍若玄黄。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自是居人无复患矣。惧者俱息,迁者亦归,结屋架庐,接比其地。
郡守因名其地为“石铭里”,盖因字为名,且识其异也。后有客于泉者,能传其字,持至东洛。
时故吏部侍郎韩愈,自尚书郎为河南令,见而识之。其文曰:“诏赤黑示之鳄鱼天公卑杀牛人壬癸神书急急。”然则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蛟鳄之词,令戮其害也。其字则蝌斗书,故泉人无有识者矣。[14]67

此段文字与其书卷之四所记不同者:
一、其事发生地非潮州,乃泉州之南山;二、时间为元和五年,比史载元和十四年韩愈贬潮州早九年;三、无何人祭鳄鱼、鳄鱼迁徙之事,乃雷暴击碎石壁,砸死鳄鱼。
与当时为河南令之韩愈有关者,仅为有人从泉州传来石壁铭文,韩愈为辨识字迹而已。以情理言,此说似当为韩愈潮州驱鳄鱼事之原始版本。而因所述事不如其卷四所述韩愈“驱鳄”之事更为生动具体,首尾完具,且与韩愈自撰之《鳄鱼文》自然参合,故《旧唐书》作者刘昫弃此而取彼,《新唐书》作者宋祁亦乐享刘昫之成,皆在情理之中也。
《宣室志》卷二所言韩愈之第三事,丘述尧先生并与前二事总括为:
另一则谓韩愈病死,是奉天帝命,随神人去征讨骋悖肆奸、觊觎中原的威梓国。综观这三则记载,很明显是神化韩愈。其书诸多怪异,与其外祖父牛僧儒《玄怪录》同一性质。[7]

则《旧唐书》作者刘昫作《韩愈列传》取材失当,误用荒诞不经之书,自不待言矣。
如此说来,韩愈之后,终唐之末,文献资料中无任何韩愈除潮州鳄鱼事之可靠证据。换言之,史家所记韩愈除鳄鱼之事,纯系杜撰;谓韩愈自作文章记其事,以神话自己,更是子虚乌有,冤哉枉也。

三、结语
推其事,完全有可能如此:韩愈知南方有鳄鱼之害,而适值其任潮州刺史,遂心血来潮,偶生灵感,而戏撰讨鳄之文,以增刺史之威、安反侧之心,与他戏撰《毛颖传》《送穷文》以消胸中块垒为同一类事。
不料韩愈既身为名人,潮州又适有鳄鱼为害,好事者遂杜撰韩愈驱鳄事,而援韩愈所撰游戏之虚文以为其驱鳄事之实证。原史家之本心,盖欲美化韩愈,而殊未料其所述之事荒诞不经,反成丑化韩愈之败笔。
若韩文忠公泉下有知,见己游戏之文反成身后玷污自己操守之“确证”,能无太息痛恨于张读、刘昫、宋祁、苏轼之笔乎?新、旧《唐书·韩愈列传》、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昭然如此,则吾恐韩文忠公若泉下有灵,必如芒刺在背,而不遑宁息也!
原其终始,韩愈戏撰《鳄鱼文》,因其文高而可乱真,遂为文人、史家所误解,适成病己、毁己之口实,几为百口莫辩之不白冤,不亦悲乎?然而我辈亦大可不必为韩愈惋惜,以为其翻不如不为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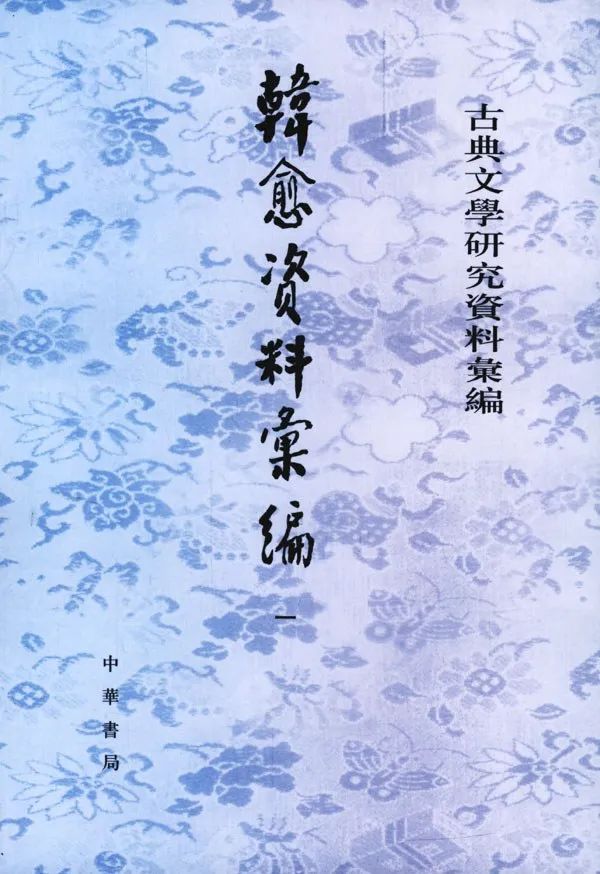
愚以为,此文自有此文之妙:无此文则韩集固不必有阙,有此文则韩集增趣。且孟子不云乎:“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17]320
韩愈在哲学、文学方面之影响,千秋耿耿而在于中华文化史册。纵使因史家、文人固陋之见、拙劣之笔,其传遂成不实之文、不信之史,而滋生误解,然事实终将大白于天下,新、旧《唐书·韩愈列传》妄加于韩愈之诬枉辞,可以休矣;胡适等现当代学人因此而误评韩愈者,其言论亦必因学术研究之深入,而为过眼云烟矣。
参考文献:
[1]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363页。
[2]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吴世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J].文学评论,1979(05):10-14.
[4]郭朋.隋唐佛教[M].济南:齐鲁书社,1980.
[5]赵二超.论韩愈的鬼神信仰[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29(04):1-9. 王琳.韩愈潮州祭鳄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反思[J].兰州学刊,2007(02):183-186.
[6]王仲镛.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实事求是——《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一文读后[J].四川师院学报,1980(01):26-29.
[7]丘述尧.韩愈《鳄鱼文》考辩[J].语文月刊,1999(04):11-12.
[8]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9]韩愈.韩昌黎全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5(民国二十四年).
[10]苏轼.苏轼文集[M].茅维,辑刊.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吕祖谦.宋文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吕大防.韩愈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3]张煜.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4(02):87-89+96.
[14]张读.宣室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263页。
[17]孟轲.孟子:尽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