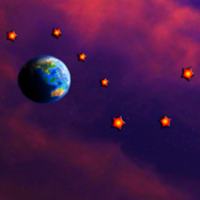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曹旭
前接:萌一、生二、存三

初秋晨风,四岁的斐斐,扯着母亲的手,走过坟路,到学校提前入学了,背着外祖母用布料剩角五花六彩百缝的书包,不像个学生,当然辜负那神志与羽嘉的热望,所以小学、中学、高中,分别蹲下了一个年级,才与贺鹏和付西城持平,同一时期。上小学的斐斐穿绿色的小军装,高年级还是,当年他父子三人的留照,翘腿微笑的是父亲,一高一矮一丝惊讶和畏缩神情的是李非兄弟。李非上身绿衣小棉裤,提不起一样裤脚,在童年的鞋子上皱褶。他们仿佛没有背影,看不到他们已经转身离去。
十几年后,着蓝色制服的夏老师家访了,推车走过那棵秋桐,仿佛又非秋天,晚夏萌秋,不见落叶的黄色和阴雨的冷风,这可来和正来的荒凉,要到冬天才能看清。或者也是生前的一帧照片,看不到背影。李非听到了敲门声。
仲夏时节的三楼房间,大多绿色上衣的同学们,围着那辆崭新的绿色自行车,看何鹏和李非摆弄脚蹬,支其机器车架,看轮转动,摇铃响声有点家里那个闹钟的语音,那个已经破碎的红色的闹钟。但是母亲回来了,众人羞涩的鱼贯而出。蒙月兰教训李非退回赃物,作深刻检查,李非无言面对,不久辍学闭门。
已非李非班主任的夏老师着中山装家访了。李非颔首坐在红衣铁矮凳上,一言不发,在学校打架,何鹏和李非站在政教处夏老师的桌前。高过统统的桌椅好多,不敢仰视老师的工整军帽,只是盯着他残损的鞋子,还有一点一滴的悔意,落在斑驳的水泥地上,不敢仰头唯恐泪流满面。夏老师默默地告诉,拍拍李非的肩头:“还没下海的,没事的”。
贺鹏在副厂长父亲的走动中,同样免于公安处理,不堪学校处分,和李非先后辍学,毫不喜乐。你不怕吃苦,御煤车去!贺副厂长大声斥责儿子,只要多动脑就能吃得饱。卸煤车跟着师兄学,速度和收益竞增。或者到烤烟厂拉烟包,量重力怯,装好几百斤货物的架子车,斜形翘着,他两个人一块儿吊起才能压平轩辕,一推一拉还算默契,下工后看着彼此的黑红花脸,莫不嬉笑。只是后来贺鹏被父亲叫走,李非一人是干不动的。
又是一个立春时节,一群蓝色制服,骑车到铁路南侧的水泥厂家属院,是给付西城送喜报的。城西考取了新乡师范专科学院,意味着毕业国家分配,着正装站讲台了。微笑或严肃是妆容,感受是肉躯的外套,志向是人的心魂和大脑。
依着浅蓝色校服装的付西城在日记中写道:“时代的热望和蓬帆已经撑满,万物来归的大海,正在召唤,我必须登船。”李非也默念:“未知的大道,不知何处,却已在征途。洗去伪饰,褪去外套,扔掉包袱,不可滞留,坟场也能踏开出路。”那是贺鹏与他前后,集体工入厂上班,穿上浅蓝色的劳动布制服。

橡胶厂炼胶车间,高悬而照亮不远的银灯光下,右边那棵巨大的梧桐,已开过满树的紫色花朵,童年时可以捡拾起来,吸入花儿根部的甜味,也是母亲曾蒸煮时的往昔岁月。而此午夜,梧桐静默地团聚在不远的房墙之间,其冠及叶落满水泥厂飘来的层层灰烬,无雨涤净,无风吹落。
不远处的更衣室传来李非所在班组的说笑声,是评选季度奖的小集会,值班长说这个春节大家都干得好,撇开缺勤请假,还有这九个优秀,看看怎么评。几个人推荐年长者,干瘦的老师傅,吐口烟说,我儿子也上班了,家里面好多了,这季度奖还是给李非吧,刚上班,也勤快。这一岁的年终奖也给了李非,一九八七年在塑料棚下的七十二元,当晚李非请客,在厂外夜市摊点吃酒,饱醉而归。
多少个夜晚,包括凌晨寅时,也会和小组三个人一同饮酒,每天的工作计划渐渐少了,甚至海南岛的原材料因款额不足,无法供给而停工,大家却不胜欢喜,又可以休息。茫茫的灰色前景,无际的黑暗前途。李非知道自己上路,和分配到检查处的贺鹏,也常常探问未知的一个声音,我们会到哪里。
那声音终于爆响了,一同进厂上岗培训的同龄者,东城回民街人,侥幸同分在炼胶车间的,虽不在一个小组,在偌大的灰尘满间的房间里,彼此常见。第一个季度上班不久,嗷嗷勤劳的一群集体工,东城小伙出了事故,他的组长生嘶喉破的疾呼,爆裂中,铁板车拉着他急奔医院。李非快跑不动了,汗流进了棉衣颈脖,快死一样坐在急诊室外的台阶上,一头凉汗。那只被卷起双钢辊之间的手,倒车出来时,连筋带骨足有一尺多长,耷拉在碗上,似乎血无痛无惨叫,却是一声巨响:“李非默默自问,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吗?”那残损的手掌已无法失去,无法抬起,模模糊糊在惨痛之中,却指引了方向。
从那时起,在灰暗的路上到处询问。初中毕业时介绍李非入体校未成的曹师傅专门找了他。说有一个成人自学考试,现在热门,你去人民路的工会问问吧,从那时起他开始偷偷的报名。在母亲的支持下,首次参考的《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史》竟然一次通过,不负那夜班里灯下的苦读,前夜班后默写到伏案睡下,醒来已是色晴天蓝。
路径似乎明朗,在清白色的窗口出发。
贺鹏借助父亲的关系,调往市档案局上班,未参加橡胶厂三十年大庆,千多名员工,人手一套灰色防水防油的工装,人手一台银电子挂钟。大家毫不喜乐,李非却有不祥之虞,因为母亲家里发了两台,不如送给付西城一台。西城悄悄地说,钟表不能送啊,送终送终啊!李非猛然醒悟,哦,难怪童年时的那只红色闹钟不知去向。
要断了自己的后路,置之死地而不悔,天志要绝处逢生。李非辞掉了工作。蒙月兰莸悉,惊诧之余,忧思而不多言。亲朋的暗嘲明讽等等,约有一岁春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李非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那银色的电子钟卡卡的旋转,仿佛是一个春天。

黎明在院落里未有声响时,已然寸寸而临;时间在中原处悄然无形之中,城市来到乡村。弯路无处不在,许南公路是千年古道,旧路成沟。曹操征张绣,刘秀战昆阳,必经此途,确又不死,记忆如萌。此路过关公挑袍处灞陵桥,所以,解放后筹建的这所中学,以桥誉为名,第一任校长阴差阳错,却又萌芽生长,岁岁更新,姓贺,是许县人物贺升平的族人。
同样的南风习习,缕缕不断,那年春季,蝗灾天降,麦天荒芜,大暑晚期,竟然发省,呼呼吹落人家晾晒的残布旧衫。一九三三年,贺升平贺仲莲父子,在原许县市场前街,变卖房产,筹建霸陵中学,招生聚力,传播马列主义,那是市郊七中的孕育时期。八十年代,合村本校的高潮,80年代中许昌霸陵中学诞生,后更名为市郊第七中学。贺家后人贺鹏父亲指点,母亲蒙月兰同学私助,按“电大、自考等五大生”分配原则,李非下许南路,走小径百米进校,到校长室报到,是夏老师的同学夏校长。
不比别人,李非是搭上地方政府政策最后的一班夜车,在深秋入职,公办教师待遇。母亲蒙月兰不再怨气儿子决绝,病躺在床也不禁叨叨的日月,暗喜儿子当年所言:怎么会没有出路?深谢亲朋相助,不惧歧路乖舛,祈祷成长茁壮。
别于早来几月上班的分配生,李非总是默默翻资料,听堂课,练毛笔,也是从那时开始日记,工整的在薄薄的本子上写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晴。开章,我只谈起你,多少美的向往,全是悲剧,因此我再次耿心浪漫于现实的距离。对面小学的夏老师,看着李非写字,当面赞曰:噫,厉害,有前途,了不起,众人暗笑了。
翌年春天,李非由助理转任语文教员,可以在两节课后,搬藤椅,去校外百米处的麦田看绿浪麦子,看岁岁兰花开,田埂上寻野菜,读鲁迅,写笔记。他的第一篇文章,《麦田里的野味。》被入伍的胞弟,地在自办的小报上刊登,无不喜乐。而且这一年的春节,他被举荐人选为许县十大优秀青年教师,唱票结束,多人震惊。
翻开九零年的生长日记:“似乎理想,只记得是努力于目前的英语学习,铭刻于心的考研究生与生命的升华。再次想到人的意志力,人的深不可测和初长的伟大的力量,因此,我运用这可怖的力,来完成悲壮的一生。”同盟会会员贺升平一九七三年秋,病逝郑州。共产党员的贺仲莲一九四六年夏牺牲于大别山蕲春。未曾断绝,还在延续,一切生命,不息存活。

窗外的梧桐树,万叶飘零,庞杂的千条枝杆向上向周围,有些痉挛者伸展,繁杂的万条根须向下于黑暗,那里执着的探索。“如果不靠意志来加强生存能力和使生存无痛可言。物质决定意识,生存决定生活及写作,就是一句谎言。我不建议你退伍,要不调查研究,你回来看看”。
在东北从军已有三载的胞弟,给蒙月兰说要转业回来,并不知道老厂矿,纷纷倒闭,橡胶厂已物是人非,水泥厂苟延残喘,回来住的吃的?如何生活?李非说什么生活?生存都困难。写信说服不了自己的弟弟,让他回来看看吧,实地看看吧。不说东北国企改制,数以万计的老工人,一腔心酸,痛苦流涕,眼睁睁看着奋斗一生的事业,毁于一旦。于国则是改革阵痛与个人万劫不复。壮年工人下岗,无计养家,无事可作,醉酒致瘫致。青年妇女呢,到关外吧,笑泪求生,大多陷落。
从丹东回去的胞弟,回到熟悉的几乎陌生的家属院,已有三寸的白雪落满故园。李非晨起,见梧桐枝披满绒绒晶莹,无风无声,万籁俱静,人家皆在酣睡。不由想起“独钓寒江雪”的心灵自由和冷切生活,那梦想幻境;想起寄往东北凤凰山军营的那句顿悟:观察伦敦,研究英国人民及其生活方式颇有乐趣,此外的心中,有大自然,有艺术诗情,人生足矣。
母子团聚,又逢寒假,蒙李一家莫不欢喜,卧床的蒙月兰闻讯儿子归来,病态一改,披衣起来,精神振作。让小儿子汇报在部队的工作,在军区《前进报》发表的文章《弱者的新坐标》,以及油印的自编报纸,况且又发的第三个喜报:东北的山梁,谷壑野产的人参、木耳、蘑菇,给李非带回一条军裤一只腰带。
春节更为热闹,雪晨割肉买菜。见肉馅儿不足,胞弟顶朔风小雪,踏来时几乎无人的街头,在水泥厂的僻巷中,尚有进城卖肉的摊架。虽然下午四时吃上饺子,这样的团聚,胞弟记录在撰写的母亲传记《那年的烛光里》。
七年后的又一场大雪,中原胞弟起草李非修饰的《墓志铭》,碑立塚蒙李西北角的七层塔下,其曰:壬午年月十二日,生塚蒙显赫之家,少明慧励志,名冠枢苑;长柔顺闲淑,手不释卷。婚不幸,寡居流离,筑栖身,与两儿相依为命。腹无饱餐,朝夕忧戚,药饮常年。
伫立凛凛寒风,中原许县,亿万雪花,纷沓盛开。“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那林冲把两扇草场门,反转上锁,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玉,迤逦背着北风而行。”没讲课或阅读至此,李非自信或留言:“是生存还是生活?是生活还是反抗?是反抗还是死亡。”母亲逝世,满四十九周岁。

“一道刀刃般明亮的闪光突然爆发,奔行加速的自行车和步行者是何等地富有人味儿?”这几乎是葡萄牙 佩索阿的诗句。李非写在《惶然录》的扉页上,修饰在清明节。和母亲蒙月兰一块儿祭祖,没有到七奶奶的坟茔,而是越过李庄过往蒙村,到外祖母的坟头,摇火祭拜。蒙月兰不胜悲哀,并未到墓前,一切由李非替代,夕阳西下,泪水未尽的蒙月兰随去了她二姐的家里。也好,这是同学可以相聚的时间。
不知道人众,亦不能打扰母亲居住稍大的房间,大家挤在李非四平米的斗室,一张课桌,伏在那里背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凌晨,夜里收听考试题案录音的那张水泥厂的木床,以及那台当年外祖父嫁妆的方桌,却狠心锯短的四腿,可以推进木床下,拉出来就是酒桌,九个人挤满了清明的斗室。
“不用站起来了,你在床上,敬你一杯荣升为办公室主任,我们院里的桐花还开着呢,清明的雨刚刚迎候,我代表橡胶厂家属院在我们的迎宾楼恭敬你们的光临。”贺鹏说着自己笑了。付西城也笑了:“才下学几天就说官话了,什么主任,主任助理呀?我副主任助理”他女朋友也笑着解释。同学有两个,一同分配到五一路百货商店,一个在劳教所,一个是司机,两个待业,却不料一群青年海阔天空,待业的同学调侃说,我怎么也没有想辍学的李非会做教师,还是班主任?付西城说就凭李非敢辞职,方向凭远,市长也敢干来,老同学敬一杯,李非谦虚道:有口饭吃,生存不是吗?
贺鹏劝酒给几个同学被戏弄:你好好的政府官员不干,半个厂子虽小,也算下海,折腾什么呢?另一个同学说乡镇企业人只有七人,也算厂长。七人,总是七,李非默然想,又回答说,唉,付班长,我只是生存,干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和环境也都还好,跟着电视学英语也放下了,本科学到了《美学》及格,已经看花是花,是看到自己唯心主义了。大家才注意到李非的房门背后,写有“无论成败,过程为上”的毛笔字。大家无不疑惑,也有人心领神会。那仍然寒冷的风趁着夜色,吹落了几瓣紫色桐花,众人不晓,直吹到女同学说凉,看不到那紫色的花了,跳到床的里角,挤在西城的怀里。
说到东北丹东的从军者,贺鹏特有兴趣:哎,那个弟弟将来肯定有出息,春节回来。说要考军校,那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却敢有这样的志向。李非说,他绝对可以,不比我学英语半途而废,敢于决心自学高中科目,来信说睡在水房,天天对着竹子悟道呢。西城女友说,什么悟道,还是说说你的女朋友吧,李非笑笑不语。
与付西城那个相挤的售票员大声的念道:“为了一个非我同类的女人,糟蹋了我的一生。词语是永恒的,而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已。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他无疑将以书结束。一本文字不如一双鞋子踏上重要”。
李非去夺笔记,不料打瞌睡的警官,刚俯身到床沿,一口吐出来,浸殁了人的喜笑,玷污了那行行萨特的《词语》。而醉归的何止两人,为了生存和生活,众人醉断寸肠,醉卧凉风。

“谈到书,唯有李非知道的多呢。”城北的大院里,贺鹏他们看秋叶之下的梧桐。柳树和中原的梧桐最难凋零,那明媚的醉心的圆月,在梧桐黑色的叶片下,以左其上,可以诗曰:明月松间照,水其石上流。贺鹏对李非说:你甭说我抢你的朋友,你看上她的时候,我已经约她出来了。
贺鹏说的是汪明月,高干子弟竟然在胖东来去收银。李非抬头啊,怎么是你呢?贺鹏
当年参加自学考试的人民路,戳戳李非看课堂门口,一个大美女站在那里,巡视整个课堂一周,整个教室一百多人,顿时寂静。她却走过到李非的旁边,那过道一侧:“你这里有人吗?”李非慌乱的掩饰,移动着桌子上粉红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史》。
“她的屁股好大啊,你没有追,你呆呆的我追到手了。”李非不难过,尽管有遗憾,却想可怜了那女孩子,当年为了一个女同学,还是运粮河的,只是郊区的桥头,他和两女同学郊游回来,从塚蒙李向东回城,高二年级,清明踏青。那另一群人在桥东看着他三人打呼哨,喊话调戏,李非说,你们俩走河堤往北走。
那里的河水将是母亲蒙月兰骨灰撒过的地方,当时谁会知道呢?他在桥西,对一个卖甘蔗的摊主说,你不认识我,我是塜蒙李的,用一下,抄起了削皮刀,装在绿军裤的鞋兜里,可以让他们看到,一个人向东,到那群人一旁,对着其中的一个说,我是三高的李非啊,你忘了,我们是一中的同学?那挎着自行车和站在清明中的一群同龄人,听春天的犀利风声,不知道如何是好,“哦哦”不言语。李非说我走了,有时间三高过来找我。那是命中注定的吗?什么是红颜知己。
李非回过神来没有说汪明月的漂亮,只记得汪明月邀请他在月下的运粮河畔,那岸边说话。汪明月说:“你师弟现在追着我呢,你师弟现在还追着我呢。”这简单的话语谁会料到呢。十几年后八月十五的早上,竟然与汪明月在胖东来人民店邂逅。贺鹏已经远走,已婚凤凰的李非给儿子要排骨,那收银好像收钱的时候,脱下口罩:“李非,你不认识我了。”哦,是汪明月那月亮般的脸庞。其他的无从知晓,没有必要再问青春之心杳杳,他和汪明月也只有月下一次相会吧。
然而,那汪明月和当时的同学,几人看了雅思斯贝尔斯、桑特、尼采,还有阴冷下的光辉,叔本华?当年的青葱岁月。高干子女的汪明月后来在哪儿呢?工厂最后倒闭的贺鹏又去了哪儿?不管谁的身躯部位如月,但她娇美而教室寂静中的脸庞,一存一生谁堪?忘记那是贺鹏西城几个同学,梧桐月下的勾连诗意,却不知桐叶早歾,青月碧落。

蒙家与夏家有远亲,已在几天前的冷夜,蒙月兰和李非去了趟夏庄。一个女孩子齐耳短发,洁白的脸色,泛着月辉开门,李非没有看她,她有些冷傲,瞥了来客一眼,回头喊着家人,转身走了。那幽暗的灯光里,李非提着罐头跟着母亲进去,蒙月兰你怎么不多看一眼那个女孩呢?那双银亮的眼睛和精致娇媚的鼻翼。
蒙月兰早已患病,放学之后辅导学生,坐在那只红漆小铁椅上,血常常渗透在那枣红色的椅子面上,无人知晓,还是孩子的李非怎么会了解妇科病呢?书生一样的蒙月兰,怎么不去检查呢?你的二姐在哪里呢?为什么不管不问,嚣张跋扈在哪里呢?
李非扛起藤椅前往野麦田的路上,已非原来的斜土小路的校园,可以走水泥道。走水泥道那刚植的幼桐之间,有一枚泛黄的叶儿落在他的头上,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称《叶歾》。谁谁家的小伙子歾了,“殇”的口语千年流传,以为是“伤”,却是早夭与早逝的本义古语。
蒙月兰住了几次院,已忘记了。县医院两次李非捡到了一本部队自卫拳术的小小册子,爱不释手的看,也是后来练武术的诱因吧。伏在洁白的床头翻看,那是母亲遭家暴住院。第二次住医院是小便失禁的大病了,已经上班的李非抱着尿液干湿不知多少次的被褥,对着医护说:“我们穷还要买走你们的这些,也好,我买回去结婚用。”医护白色的衣服很尴尬,自嘲苦笑。
而最末的一次呢,李非也是在五一节开始请假,班里的孩子们也要照料呢,夏校长说:“该请就请假,那样的重病。”李非回想着学校,杂想着母亲,不知为什么又看到了梧桐,那尚未发芽开花的梧桐,远远地看清,在旷野的河岸上枝枝隆隆,团团若人脑的血脉。母亲已是子宫瘤晚期,蒙月兰的二姐叫自己的儿子,来看李非如何孝道。临床的大婶儿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尚未婚嫁,大婶子以为可以和李非对象,以习俗的婚办冲喜。李非只是默默地用弯好的铁圈,给母亲掏坚硬的粪便,用了一生的时间,听到那石块一样的惨痛,掉落在红色桶里的回响,余音袅袅。顾不得伤痛,那又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李非还是个孩子,没有见过女人的孩子。
从春季前的住院回家一段,直到蒙月兰又对李非说,斐斐,不行啊,还得去医院啊。不谙妇道人事的李非,连忙安排学校医院的时间,两相照料。但最终还是病逝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李非一直没有哭,却在摔瓦盆的瞬间,仰天伏地的大吼,那个叫做父亲的李贵生,蹲在太平间门口的梧桐树根处,无言可发。近在咫尺的那个仇人二姐,正在哭诉:“月兰啊,那我伺候你半年也没有得你的好啊!月兰啊,我闹了水泥厂是为你出气啊”。付西城知道内情,一直跟着李非的身边,李非的后腰别着一把改制的发令枪,还有一只贺鹏的手气枪。
那运粮河北段,医院太平间周围站满了观众,头裹白孝的胞弟,一言不发,他从南京军事学院匆匆而回,只见母亲一面,已无声回复,即便是冥冥中,李非和谁争执是火葬还是土掩之时的愤怒。“火”字也无法吐出的蒙月兰,许县一高的“小清华”无以生存。葬礼那春天里,桐花落尽,碧叶荣荣;隐于人群之中的汪明月,不住拭泪;还有运粮河西岸,推着自行车的夏芳,哪知悲音?
蒙月兰凤凰一生,龙蛇一世,已逝世无声,她的二姐和她的丈夫不敢火并,是李非放出狠活:“谁再借此大丧闹事,我一枪打死他。”胞弟红着眼睛,盘膝而坐,一声不吭,哪怕谁哭泣,无论父亲跪倒灵前,痛哭道:“月兰啊,我对不起你啊。”晚春的满树紫色桐花已经凋零,夜夜清雨过后,碧叶嫩生。

“我的灵魂对现存的一切感到厌倦,我再也不会为什么世界伸出我的双手,我毁灭我的世界,倘若死亡敲门,我会毫不犹豫的打开,因为我空荡荡的室内,母亲仿佛没有离开。清晨醒来,不由得喊她,却知道她已经真的离开,满室的虚空,还失落若狂风过后的青桐丛林,已是旷野。只有春天来临,夏风将至,在溢满芳菲的丛林,那女孩在圆月之下舞蹈,她的眼睛,是一枚万千晨露织成的银星,千万双翅膀在她的双足之下舞动”。
已经退休的夏老师敲门进来,不是死神,却并不言语在一大一小两个房间,阳台改成的厨房,四处看看,只有一金光闪亮的热水器,是常用的煮皿,皿壁是面汤满溢而淌下的道道遗痕。方便面,半只火烧,一缺黑褐色的酱豆。这是井冈山的斗争,还是陈毅的梅岭饥饿,方志敏的清贫?一人吃饭,全家不饿,李非自嘲。
李非梦想不到,夏老师介绍的对象是夏校长的女儿,那是冬天,夏芳着红色大衣,从延安小学校门推车而来,是夏老师退休之后创办的私立学校。李非找到她,炸了花生米,西红柿鸡蛋,依然忧郁的两个年轻人,相继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还是之前,夏校长病休在家时,听闻蒙月兰往生,前来看望,夏芳推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站在运粮河西畔,似乎听到谁悲伤的声音,也并不知道三月过后的夏天,父亲病亡,李非特来吊孝。夏芳梨白色的衣裤,泪痕斑斓,浸湿的刘海看不到她露珠一般的伤眸,只是月白的肌肤似曾相识,是汪明月的月亮吗?汪明月还与贺鹏在恋爱吗?夏芳和李非的婚礼,在第二年的冬天,真的在城东贺鹏的饭店举行,店名大书:宴宾楼。
冬天的街头,一对新人站在那里,李非腼腆青涩,难饰淡淡的忧伤,一身灰色而有些胖大的西装,像一个孩子。不料夏芳竟落落大方,粉红色的头花在暖暖的阳光下,无风的冬日里,频频颤动。
来客并不多,是市郊七中的老师们,还有付西城,刚从南非回来,带来了把兄弟的指甲和头发。那把兄弟去非洲打工,夜晚睡于铲车之下,翌晨车辆发动,不及躲避,命丧异国。一红一百的两个事儿,情何以堪,但他依然若蒙月兰姨的丧事般,忙前忙后。老家四叔的邀请他们到上海旅行;胞弟寄来了新办的刊物:《无墙大学》,其中编辑了李非的文章《爱我的只有一个女人》。为什么在这年轻的岁月里,满溢了自己的痴情,瑟瑟冰冷的地域中,燃起新的火焰;漫漫冬夜的沉寂里,送射阳光的辉影。
为何不顾老言少劝,世说俗识,一意孤行,宁可悲哀着瑕疵,仇视着污点,又拥抱一切,欲罢不能,千回百折,素湍深潭,难舍难分。是美颜吗?是晨雪的肌肤,还是满树的芬芳?是心的目光和柔情。我只知道,我只知道,我的她为我而来,我的爱人,为我而来,因为母亲走了?
累累诸端,是向天地的深情告白吗?还是天志的林谷幽门?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曹旭,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教师进修学校干部,笔名陈草旭变,近年来有数百篇散文、小说见散文在线、红袖添香、古榕树下、凯迪社区等文学网站,合著有人物传记《那年的烛光》。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