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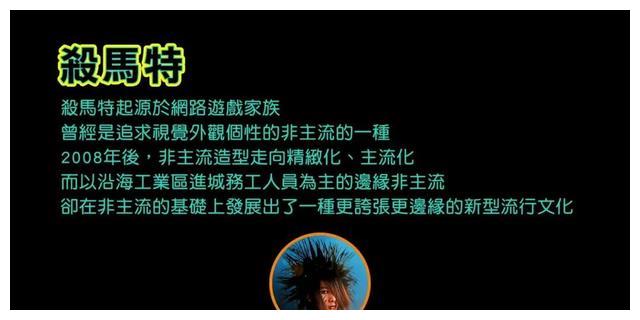
底层的缩影某年某月,东莞石排镇。“啊”的一声惨叫,宛如平地惊雷,掀起一阵骚乱。这间不起眼的工厂门口,竟然聚集了大批量的小混混,手持利器,凶神恶煞。他们都是工厂老板叫来的打手,专门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员工。

有员工试图求和:再不发工资,我们饭都吃不起,真的没办法工作了。话音刚落,就被恼羞成怒的老板当成出头鸟,一把大锁直接砸了过去。那名员工顿时头破血流,倒在地上,被紧急送去医院。

老板威胁大家:谁敢把这事说出去,谁就死定了。最终,这场几乎要闹出人命的斗殴事件,仅以老板赔偿500元,草草了事。而且,狡猾的老板,连500元赔偿都没给够,只是承诺结薪日再一次性结清。

15岁就外出打工的韩亚杰,隐匿在闹事的员工中。为了自保,他不敢供出老板的恶行。回想当年刚踏入社会,他年纪小,害怕被欺负,故意去纹身壮胆。左青龙,右白虎,一身霸气。后来才发现,徜在社会的大染缸里,纹什么都没用。社会的风浪扑棱下来,多少底层走投无路...

不过,日子还是有盼头的。只要等到老板说的结薪日,一切都能迎来解放。他打电话告诉妈妈:等我发工资了,我就带女朋友回家结婚。全家人都很开心,一起等待着这个神圣的发薪日。

只是没想到,黑心老板将工资一顿克扣,本应7000元的工资,最后只剩下29元。没钱,所有的希望都破裂了。不能回家,不能团聚,更不可能结婚...很多年后再提起往事,韩亚杰对着镜头有些落寞:现在那个女生,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韩亚杰身上的故事,不过是众多底层务工青年的缩影...辍学、欠薪、被骗、身无分文、穷困潦倒...他们的命运很重,一层又一层沉重的枷锁,压得他们几乎喘不过气。可他们的人生却又那么轻,就像漂流的浮萍,在社会这趟浑水中掀不起一丝涟漪...

他们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农民工。但比起其他农民工,韩亚杰还多了一层特殊的身份:杀马特成员。一个承包了无数人青春印迹的,略显中二的名称。一个曾经让众人闻风丧胆、避之不及的非主流群体。它的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杀马特的真相2012年,46岁的导演李一凡,第一次见到了满身夸张造型的杀马特。望着那些五彩斑斓的头发,李一凡很兴奋:这简直就是中国的嬉皮士啊!通过自黑的手段来抵抗消费主义,多么了不起的审美文化!那飘逸的长发,那缤纷的色彩,那爆炸的造型,无一不彰显着另类又独特的朋克文化...他在心中暗下决定:我要拍杀马特!一定要拍杀马特!

辗转4年过去,李一凡经过多方打听,才终于找到了一名杀马特。这位杀马特大有来头,竟然还是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李一凡怀着激动的心情前往采访,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廉价又简陋的旅馆里,坏了的空调早已宣布罢工,两位陌生人正满头大汗地,大眼瞪小眼...罗福兴的话很少,来来去去都是些家长里短,关于父亲、关于游戏、关于杀马特家族的温暖...李一凡很纳闷:这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想听的是文化抵抗啊...

2017年,为了拍摄杀马特,李一凡走遍大江南北,在深圳、广州、中山、惠州、重庆、贵阳、黔东南州、黔西南州、毕节、安顺、昆明、大理、玉溪、曲靖,以及红河州等地,共计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拍摄期间,他还搬进东莞石排镇(中国杀马特最多的地方),并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买下了工厂流水线生活录像915段。


最后剪成了一部125分钟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网友评论:题材好,切入扎实,素材充足,很多人只看到了杀马特的猎奇外形,没看到杀马特的卑微人生,看似坚固的外壳下面是脆弱的心,让他们讲讲自己的故事多好。

这是一段详实又残酷的调查活动。当李一凡走进杀马特的世界后,他才惊讶地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嬉皮士,更没有精彩的杀马特,有的只是,生命极其匮乏的杀马特...

这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大热天在工地扛钢筋,又晒又热,一天下来,肩膀肿了,皮晒脱了...如果不幸摔倒受伤或者死亡,没有赔偿不说,连工资都岌岌可危...


磨砂布,磨着磨着,指甲盖就磨掉了;

喷漆,天天待在劣质油漆的环境下,浑身过敏起疱疹;

为了多挣一点钱,在工厂连轴转,手中的活干个不停,眼里的泪也流个不停...有人在流水线上困到睡着;有人孤独抑郁到想自杀...



很多人不知道,虽然进厂打工这条路遍地泥泞,满是荆棘,却是他们大多数人唯一的选择。奶奶生病要花钱,弟弟读书要花钱,13岁的小辉只能辍学打工。不敢吃不敢喝,把加班加点挣的钱,全往家里寄回去...

少川的妈妈,早年被摩托车碾到脚,因为家里没钱,体内的钢钉至今还没有取出来...

小X永远记得,妈妈当年为了供他们上学,在砖厂背砖摔伤去世。这之后,他便跟着初二的姐姐,辍学出来打工...

事实是,他们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爸妈在他们3-5岁时就外出打工,没有父母陪伴,在原生家庭里得到的关爱和教育,少之又少...没人爱、没人教、没人管,没钱、没学历、没见识,他们所能选择的谋生手段,只有进厂打工。用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廉价的薪水,人生所求不过一顿温饱...罗福兴说过:我从来不会抬头看一眼大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因为我知道,它们与我无关。

而比起肉体层次的疼痛,或许精神上的空虚和寂寞,才是最令人煎熬的...工厂的生活,枯燥、乏味、看不见未来和希望。他们没有童年,没有未来,似乎也没有现在,只有轰鸣的机器声、刺鼻的药水味和暗无天日的流水线...他们那么孤独,那么迷茫,那么苦闷,无处宣泄。没钱,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玩头发。幸好还有头发。唾手可得,任人折腾,便宜实惠。将头发立起来,用梳子拼命梳上去,不断喷发胶,再用夹板夹下来,让头发蓬松又独特,成为人群中最闪亮的那道风景线。


然而,怪异的造型下,藏着的不过是一颗,渴望被关注的内心。有人故意染红发,穿红衣,去人多的地方晃荡,只想吸引多些目光。有人故意从跳广场舞的大妈群中走过,就是为了得到片刻的关注。有人说:就算有人来骂我也好,至少有人跟我说说话了。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一群故意闹腾、故意叛逆、故意浮夸来换取关注的小孩。就像陈奕迅唱的那样: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


后来,浮夸的造型,成了他们安全感的来源。不管现实有多操蛋,只要梳起非主流发型,他们的生活就有了色彩。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发型聚在一起。相同的人生背景,类似的发型着装,让他们一见如故。不用称兄道弟,只需发型认人,他们自成一派,在这个处处压抑的社会,找到了同类。

他们自称smart,时尚,潮流,又为了更加霸气,音译为“杀马特”。自此,杀马特家族横空出世。短短一年时间,从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上万人。五湖四海的人,因为家族聚在一起,畅所欲言,称兄道弟,一呼百应...

他们将杀马特家族当成避风港。现实中无法宣泄的苦闷,都在家族里得到了慰藉。有人说,在家族里得到的关爱,比家里还多。之前抑郁的姑娘,开始有了希望,她说,想办一场杀马特的婚礼。

以前他们的生活,睁眼闭眼就是流水线,但现在,他们有朋友,有交际,有个性。他们开始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每天,他们最期待就是夜晚下班,去溜冰场,跟朋友一起大肆玩闹。在家族里,交友不看家世,不看金钱,只看发型。有钱就去溜冰场,没钱就去逛公园。这样的生活,简简单单却又多姿多彩...


全网封杀可谁也没想到,事情的变故竟然来得这样快。因为学历低,没文化,审美另类,造型独特,他们被定义为“低俗”,成了社会公认的负面形象。网络上兴起全民反对杀马特,微博、贴吧、QQ群,对杀马特的辱骂,随处可见...


很快,对杀马特的围剿,从线上蔓延到线下。工厂拒绝接收杀马特造型的员工。走在街上,杀马特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还会被保安拉去派出所...有人故意趁杀马特落单,提着棍子就去打他们...还有一次,跟朋友去吃烧烤,隔壁桌的人突然跑过来摔桌子砸东西,将杀马特按在桌上,用打火机把头发烧掉...


似乎一夜之间,所有的杀马特都消失了...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剪掉自己的头发。曾经,他们对头发的热衷,高于一切。发型就是他们的信仰。宁愿睡觉时在头底握个拳头,也要守护着头发不变形。两个家族打架的时候,第一条规定就是不能弄到对方头发。然而,往事不可追,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为了生活,不得不妥协...杀马特说:第一次剪长发的时候,特别痛苦,就像把自己的自尊丢了一样...


为了多守护几天头发,安晓蕙跟堂姐,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进厂打工。身无分文,流浪街头。饿了就只能喝点自来水,免费,能填肚子...堂姐饿到不行,去路边捡甘蔗渣,被别人当成乞丐...


没办法了,还是要妥协啊...安晓蕙只能拉着堂姐,将五彩斑斓的头发染回黑色,成功进厂。不为别的,就为工厂饭堂那一口饭。终于,她吃上了她人生中最好吃的一顿饭。不是它有多好吃,而是真的饿太久了...但这也意味着,自由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从此过上大众眼里的“主流”生活...

自从杀马特被打压以后,罗福兴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李一凡每次听到这句话,都觉得特别难受:为什么要洗心革面,凭什么要重新做人?他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洗心革面?谁又有资格,要求他们重新做人?

在我们的国家飞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父辈来到城市打拼,留下他们在贫困山区当留守儿童,自幼活就在精神和物质双重贫困的环境下。大部分人连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十几岁就被迫外出谋生。当他们乍然从封闭的小山村进入光鲜亮丽的城市时,才发现自己与城市格格不入。很多人初来乍到就被骗,被欺负,被抢钱...因为这个大染缸一样的社会,跟他们过去接触的熟人社会完全不一样...

为了谋生,他们背井离乡,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却成了城市化进程最坚实的那块砖。他们的血与汗,泪水和苦痛,藏在微薄的工资下,藏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下,藏在一件件琳琅满目的商品里...至于主流社会所追逐的车啊,房啊,学历啊,文凭啊,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法企及的梦想...所以他们只能在同类之间抱团取暖。

他们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却被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人,肆意打压。在大众看来,他们非主流,低俗,审丑...却不知道,他们并非以丑扬美,而是真诚地热爱着这标新立异的造型。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不一样的审美。对他们而言,杀马特就是生命里唯一一片净土...城市是他们到不了的远方,农村是他们回不去的故土,而杀马特则如黄粱一梦,那么美好却又转瞬即逝...他们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弃子,被肆意嘲笑和玩弄,最后消失在浪潮之中,被永远刻在耻辱柱上...

纪录片的最后,导演李一凡为他们写的歌曲响起:好想我的头发象孔雀一样/带我飞翔/飞过工厂的高墙...有个女孩梳着最普通的黑发,对着镜头有些羞涩:两套婚纱照,必须要有一个杀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样子,要珍藏起来回忆很多年...这就是他们最朴素又真诚的热爱。我们没资格去抹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