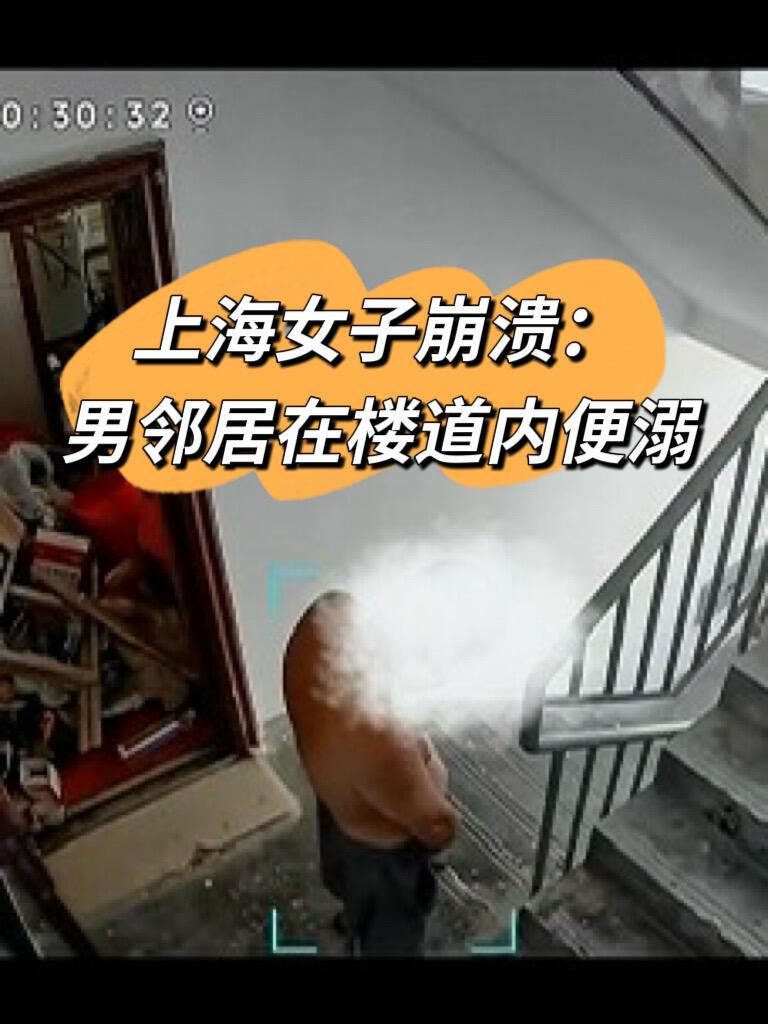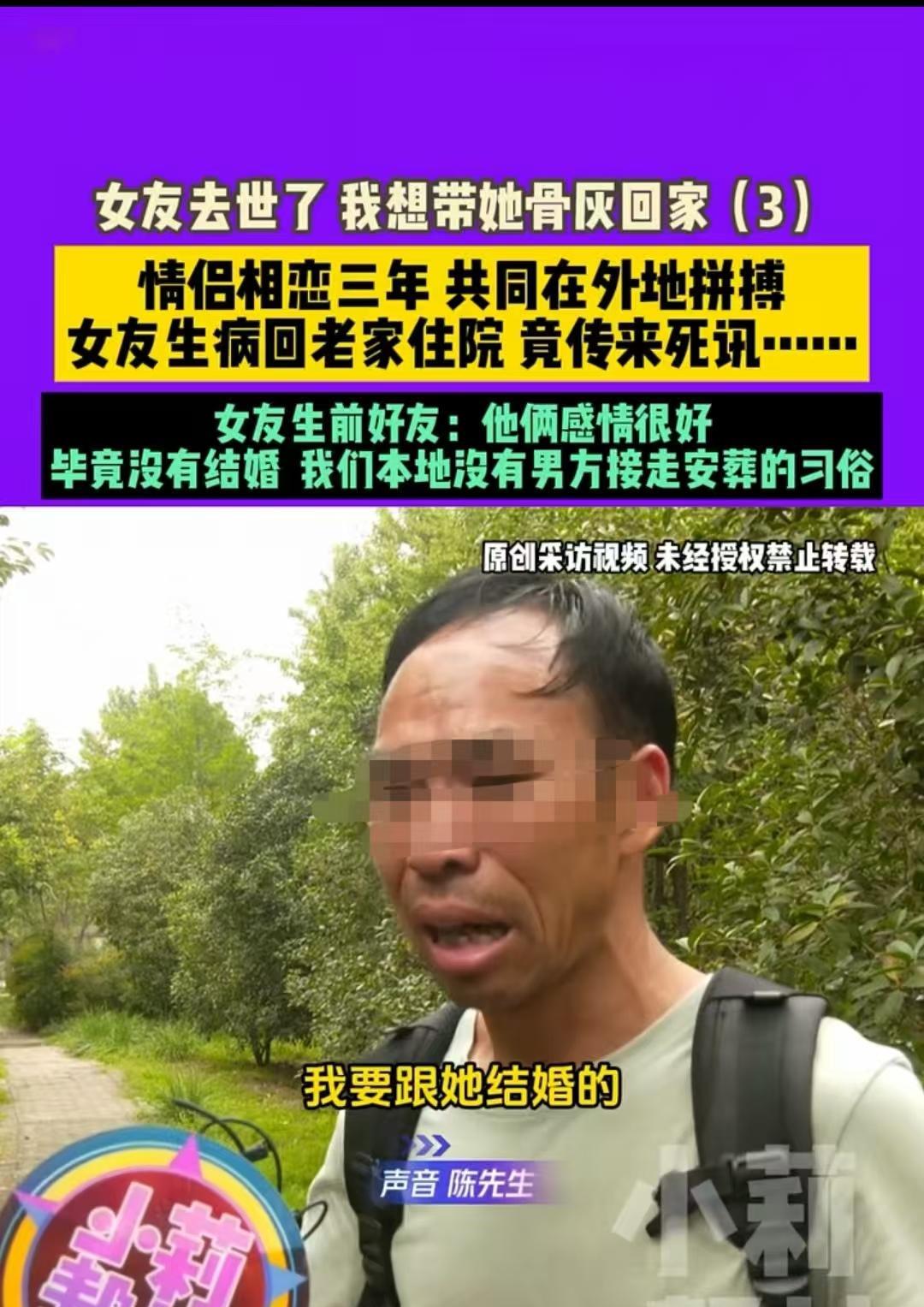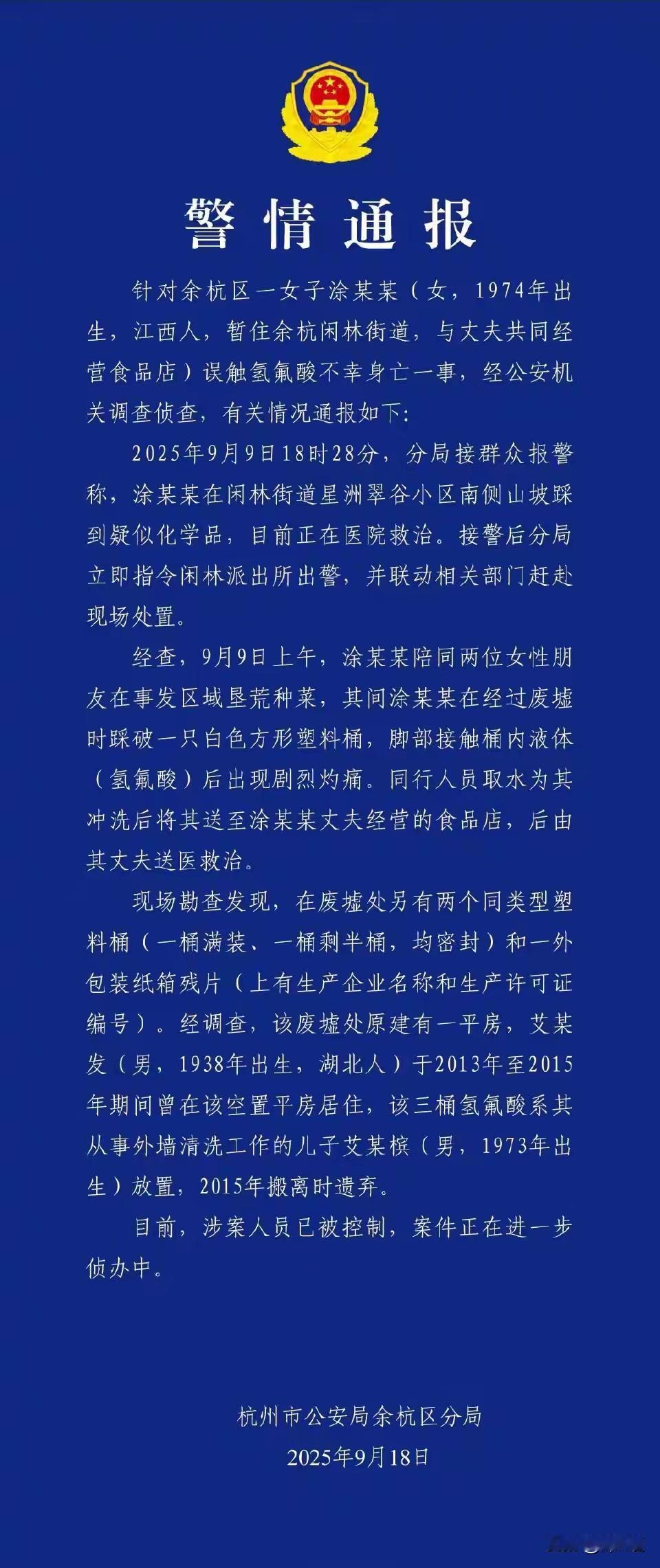父母去世多年后,我想把老宅卖给邻居,妻子却劝我把房子送给堂弟。 老宅位于城郊,如今城市扩张,这里竟成了黄金地段。邻居老陈多次找我,言语间透着想买下老宅扩充自家院落的意思。价格出得公道,我有些心动。 “卖了老宅,咱们手头就宽裕多了,孩子马上要上大学,用钱的地方多着哩。”晚上我和妻子秀兰商量道。 秀兰织着毛衣,头也不抬:“我倒是觉得,该送给堂弟小军。” 我愣住了。小军是我二叔的儿子,比我小八岁,自幼没了爹娘,是在我家老宅长大的。 “送给他?你知道那房子值多少钱吗?”我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知道,”秀兰放下毛衣,目光平静,“但你记得吗,去年小军回来,看着老宅那眼神,像是看着自己的命。” “他说什么了?”我问。 “他说,姐,我这辈子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回到这儿。” 我心里一阵烦躁。情感归情感,现实归现实。老陈出的价钱,足够我们付首付换套大点的房子了。 周末,我独自回了老宅。 我走进堂屋,墙上还挂着一张全家福。 “哥,以后我挣钱了,一定把老宅买下来。”那天晚上小军对我说。我当时只当是孩子话,拍拍他的头说:“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哥把这宅子留给你。” 没想到一句玩笑话,他记了这么多年。 回家后,我对秀兰说:“我再想想。” 一周后,小军突然来了电话,声音哽咽:“哥,我下岗了。厂子搬越南去了,我们整个车间都解散了。” 我心里一紧:“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回来,”小军沉默片刻,“哥,我知道老陈想买老宅。按理说我不该开口,但我...我能不能租住一段时间?找到工作就搬走。” 那晚我失眠了。凌晨三点,我摇醒秀兰:“要是我们把老宅卖了,小军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秀兰睡眼惺忪:“那你决定吧。” 第二天,我约老陈见面。在他家装修一新的客厅里,我艰难地开口:“陈哥,那宅子,我可能不能卖了。” 老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价钱好商量,我可以再加点。” “不是钱的问题,”我说,“是我堂弟,他最近要回来,没地方住。” “老宅不只是财产,还有些情分在里头。” “情分?”老陈笑了,“这年头情分值几个钱?我出这个数。”他在纸上写了个数字,比我预期的多了三分之一。 我心跳加速了。这么多钱,足以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让我再想想。”我声音干涩。 “哥,你太慢了!”他总这么嘲笑我,然后把最大块的肉夹到我碗里。 推开院门,我惊讶地发现小军正站在院里,脚下放着行李。 “你怎么回来了?” “失业了,不想在南方待了。”小军苦笑,“哥,我就来看看,明天就去城里找工作和住处。” 他黑了不少,眼角有了细纹,才三十出头的人,看起来像是四十岁了。 那晚,我和小军坐在老宅门槛上喝啤酒,就像小时候偷喝父亲酒那样偷偷摸摸。 “记得吗,有一次咱俩偷喝酒,醉了,把爹的渔网当吊床睡,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小军笑着说。 “怎么不记得,爹追着咱俩打,还是娘护着的。” 小军望着星空,突然说:“哥,你把宅子卖给老陈吧。他出的价钱我听说了,够你们换套好房子。我不能拖累你。” 我鼻子一酸:“说什么胡话!这宅子有你一半。” “不,”小军摇头,“我只是个堂弟,没资格的。这些年,你和伯父伯母待我如至亲,我已经很知足了。” 那晚我回到家,秀兰已经睡了,餐桌上留着纸条:“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三天后,我做出决定。周六早晨,我敲开了老陈的门。 “想通了?”老陈笑着问。 “想通了,”我说,“老宅我不卖,但我想和你谈笔生意。” 老陈疑惑地看着我。 我继续道:“老宅临街的那面墙,可以开个门店。我出房子,你出资金,咱们合伙开个便利店。你儿子不是正愁没事情做吗?让他来管理。小军有零售经验,可以帮忙。利润分成谈。” 老陈愣住了,随后大笑:“你这脑子转得真快!” 一个月后,老宅临街的墙被改造成门店,“邻里便利店”开业了。小军做了店长,老陈的儿子负责进货,我偶尔周末来帮忙。生意比预想的还好,周边新建的小区缺个便利店,居民都爱来这儿买东西。 老陈有天对我说:“没想到啊,你这主意真不错。我儿子以前整天打游戏,现在居然早起去进货了。” “哥,谢谢你。”小军突然说。 “谢什么?” “没卖老宅,也没白送我宅子,”小军笑了,“你给了我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 我拍拍他的肩:“兄弟之间,不说这些。” 美国作家罗伯特·弗罗斯特曾说:“家不是当你不得不去而不得不接纳你的地方,家是当你也许可以去而他们也许可以接纳你的地方。” 读者朋友们:在现实与情感之间,您会如何选择?当传统价值与现代商业碰撞,我们又该如何找到平衡点呢? (免责声明:本文源于生活故事适当虚构演绎,原创内容观点仅供参考,旨在反应现实社会和人性弱点,欢迎理性评论 ,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