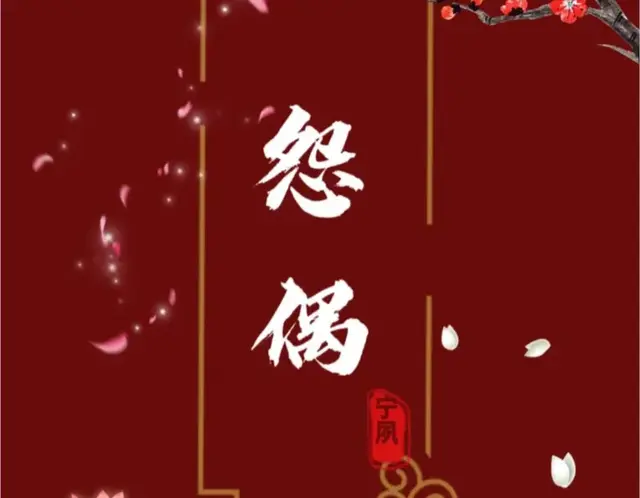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乖前夫黑化了怎么办》
作者:绿药

简介:
扶薇隐去长公主身份在江南散心时,偶遇一超尘脱俗的郎君,似坠落红尘的璞玉。她见色起意,使了些手段诱他签下一纸婚契,婚期一年。契约之婚,却也琴瑟调和柔情蜜意。
一次意外,她和夫壻那个古怪的双生弟弟发生了些风花雪月的错……
傍晚,她指了指唇角,勾清冷哥哥主动吻她。
夜里,弟弟偷偷覆吻哥哥留下的痕迹,阴暗地疯狂觊觎。
扶薇以为自己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可没想到哥哥和弟弟是一个人???
一年之后,扶薇回京,一向温润端方的夫壻立在雨中死死盯着她,狼狈脆弱。
扶薇望着他湿漉的脸,只是笑笑。她说他是一时消遣的乐子,她说京中像他这样的有千千万,她还说从未对他真心真情。
后来京中再遇,昔日短暂的乖前夫,成了阴鸷乖戾的新帝。
白璧无瑕的夫壻死在那场淅沥的雨,阴暗的另一半灵魂占据了他。
于是她被囚在长欢宫。
长欢宫内,他恨声质问:“你到底喜欢谁?”
“你……你喜欢谁,我就是谁。”
精彩节选:
六月江南,雨膏烟腻。栉比的临街商铺笼在朦胧水雾之中。雪腮杏眼的红裙少女一手护着个牛皮纸袋在胸口,一手提裙,脚步轻盈地穿过长街,翩飞的红色裙尾在蒙蒙雨雾里曳过一道亮彩。引得街边闲散商贩直勾勾盯着她,竟是看痴了。直到少女的身影消失在绘云楼,众人才回过神。
“也不知道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千金!”看呆的路人抿了抿发干的唇。
“嗤。”蹲在一边的商贩扯嘴笑了,“什么千金,不过是个丫鬟罢了。”
在水竹县这样的小地方,红裙少女是罕见的美人。可这样明眸善睐的美人,不过是个婢子。
想到这里,众人望向绘云楼的目光不由多了几分探究。连婢子都美得不食人间烟火,主子该是怎样的姑射神人?
灵沼扶着楼梯扶手跑上二楼,探头一望,没瞧见人影,脚步不停,哒哒登上三楼。
她推开房门,刚要开口,蘸碧竖起食指抵在唇前,向她轻轻摇头。坐在另一边的花影已然皱起眉。
灵沼咬了下舌尖,蹑手蹑脚走进去,将抱了一路的牛皮纸袋轻轻放在桌上。
楼下的商贩们若见了蘸碧和花影更是要痴上两回。不同于灵沼仍稚气的明灿甜美,蘸碧柳眉凤眼像仕女图里走下来的温柔佳人,而花影则英气许多。
内室忽然传来几道微弱的咳声。
这下,三个婢子都皱了眉。
不多时,里面的咳声越来越频密,柔柔碎碎,一声又一声,听得人心焦、心疼。
蘸碧起身,悄声走到门口往里瞧,见长公主醒了偎在引枕上咳着。她赶忙转身倒了温水,折回门口的时候换了寝鞋,送水进去。
知道主子醒了,灵沼这才小声给自己辩解:“主子前几日这个时辰都翻话本呢,我才没放轻脚步……”
花影横她一眼,视线又落在桌上的牛皮纸袋上。
灵沼收到提示,赶忙抱起牛皮纸袋走向内室,她还没进去,先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笑:“主子,京里来的信。”
扶薇放下温水,慢慢抬起眼睛,亦抬起姑射神人真容。
扶薇五官极其艳绝瑰丽,却被那份骨子里的高傲压着,艳而不媚丽而不俗。她半倚着引枕,优雅里透着高高在上尊贵,如今大病初愈瘦了一大圈,人又不在朝堂之上高坐,少了往日深不可测的淡漠,多了几许易碎的柔。
世人对美的偏好不同,可没有人会否认扶薇的天资绝色。一切都是那样刚刚好,多一分少一厘都造就不了她如此登峰造极的美貌。
扶薇望向灵沼怀里的东西,潋眸微凝,神色难辨。
蘸碧柔声劝:“离宫几个月了,陛下的信寄来几十封都没拆过。主子您就拆一封吧?陛下虽完全有独自理政之能,但以前都是您处理大小国事。眼下您突然放权离京,万一是陛下在政务上遇到了难处,想要向您征求意见呢?”
蘸碧觉得自己这样劝不会出错,因为长公主向来以国事为重,这几年为陛下、为国民殚精竭虑。
扶薇却不为所动,只淡淡道:“收起来吧。”
蘸碧不再劝了,心里却在忧愁长公主和陛下一直这样僵持着可不行呀。
灵沼已经换了寝鞋进来,踩着柔软的蚕丝地毯,将牛皮纸袋里的信收进北窗下雕云刻鹤的黄梨木箱中。箱子里,堆了厚厚一摞陛下寄来的信。
这些信都没有被扶薇拆看过。
灵沼走向床榻,蹲在扶薇足边仰起脸来,笑出一对小酒窝:“主子要听曲儿吗?我给您唱一支?”
扶薇抬眸,瞧着少女特有的朝气蓬勃,心里的郁色稍霁。她唇角浮现一抹柔笑,抬手捏了捏灵沼脸蛋上软乎乎的肉。
“主子笑了就对了!”灵沼笑得更真挚,“来江南就是散心的,管什么京中的事儿呢?不管不管,就该怎么开心怎么来!”
扶薇也觉得灵沼这话说得很对。
“把我昨天翻的话本拿来。”扶薇说着下了床。
灵沼赶忙帮她穿了寝鞋,扶她到南窗前的软椅坐下。蘸碧已经将扶薇昨天读了一半的话本放在小几上,又转身给她添了一杯温水。
扶薇以前喜欢喝精致的茶、浓烈的酒、香腻的甜饮子,一切有味儿的东西。但是中毒之后坏了脾胃,如今只喝温水。
扶薇让灵沼支起支摘窗,让窗外的景色泄进来。外面雨已停,潮湿的水雾仿佛还飘在红尘里,天地之间朦胧又干净。
扶薇望了一会儿窗外,才垂眸将目光落回话本上。蘸碧已将话本打开到扶薇昨天读停的地方。
这七年,扶薇翻阅最多的是奏折,其次是史册政律天文地理,根本没有精力和心情翻阅杂书。此次来江南散心和养病,她想重拾小时候午后坐在树下看故事书的趣味,可话本翻了几册,仍是兴致缺缺。
这些蹩脚的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情情爱爱故事,有什么可看的?
可她总要换个活法。
贪玩贪吃的黄毛丫头能培养出掌权执政的能力,如今也能培养出闲散人的心态。
扶薇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认真看下去。
时间缓慢流走。以前扶薇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如今倒觉得白日夜晚都漫长。
良久,蘸碧估摸着扶薇手边的水该换了,捧着温水进来,瞧见扶薇并没有在看话本,而是望向窗外。已经傍晚了,街市上明显热闹许多。
蘸碧顺着扶薇的目光往窗外望去,瞧见那道闹市中静坐的白色身影。微怔之后又了然,略思忖,她缓步走至门口柔声唤:“灵沼?”
“主子有吩咐?”灵沼立刻小跑过来。
蘸碧摇头,微笑着说道:“你总是往外跑,对水竹县了解得最多。你知道那个奇怪书生的事情吗?”
灵沼转瞬间心领神会,她甜声:“知道呀!那人叫宿清焉,远近闻名的大才子。因为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有科举,让不少同窗替他惋惜。他经常会来街边支摊子,替不识字的人写家书。”
“身体不太好?是有什么隐疾?”蘸碧追问。
“听说是有容易昏厥的毛病,不能长途跋涉。而且家中母亲身体也不大好,胞弟又常年在外,他就一直留在家乡不远行。”
“哦。”蘸碧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扶薇一眼,再问:“家里除了母亲和弟弟还有什么人?可有什么作奸犯科的?”
“就三口人,母亲和双生弟弟,身家清白得很。”
“那……可有婚配?”
灵沼迟疑了一下,才说:“他不娶妻的。前几年有好些主动的姑娘家找媒婆登门说亲呢。可他八字太硬,既克母又克妻。他亲口说不会成亲害人,后来就再没有媒婆上门了。”
“他母亲不是还活着?怎么克母了?”
灵沼眼睛亮晶晶的,兴趣盎然:“本来就八字硬,双生子双份八字双倍硬。只要他们兄弟相见,他们的母亲就会大病一场!过年的时候就克了这么一回,让他母亲躺了两个月呢!”
外间的花影听不下去了,冷声:“都是些什么神神叨叨的说辞?被人编故事骗了吧?”
灵沼嘻嘻一笑,道:“都是我听来的。听来的嘛,必然有真有假。这是蘸碧问,又不是主子问。若是主子问,那才该让暗卫查个清清楚楚哩。”
蘸碧和灵沼相视一笑,目光若有似无地朝支摘窗旁瞟了一眼。
扶薇望着坐在闹市中读书的宿清焉,神色淡淡地抿了一口温水,令人捉摸不透她的意思。
灵沼和蘸碧当然不可能蠢到在长公主面前随便议论他人闲事——她们本就是说给扶薇听的。
这几日,扶薇窗前翻看话本时经常多看那白衣书生几眼,甚至随口夸赞过——“乡野间竟有这般璞玉之姿。”
能在长公主身边近身伺候的,自然不会处处都要扶薇吩咐。察言观色是最基本的能力,只要扶薇一个眼神,她们就会恰当地主动做事。
花影也明白她们两个的用心,只是花影对她们弯弯绕绕的行事风格嗤之以鼻。她站起身,走到门口,直截了当地说:“主子,您要是看上那书生了,我去将人弄来。一个乡野书生,能得长公主青睐,是他三生有幸!”
蘸碧蹙眉,给花影使眼色让她赶快住口。毕竟长公主退婚之事还没过去多久呢……现在尚且摸不准她的意思。
扶薇却笑了。
她垂眸,视线睥向手中杯。盏中水面映着她的五官。她纤柔的指端在杯身轻叩一下,水面徐徐漾起,她的五官也跟着浮动。
伴着轻轻一道落盏声,扶薇道:“出去走走。”
绘云楼是水竹县最奢华气派的酒楼,高高耸立在长街最中央,在一众平房里显得十分令人瞩目。于绘云楼中,不仅能看见近处的热闹,也能将整个江南小城的景色纳入窗内。贫民百姓鲜少能来这地方,地方官也不可能日日来,是以绘云楼一年里大多数没什么客人。
可上个月来了位外地的贵人,将整个绘云楼包下来不说,还嫌脏嫌旧,将楼内重新布置了一番。平日里只能见到几个丫鬟外出,那位神秘的贵女几乎不出门。有那见过扶薇的人将扶薇夸得天花乱坠,信誓旦旦地说她是仙神下凡,引得整个水竹县的人都对这位美人抓耳挠腮地好奇。
是以,当扶薇迈出绘云楼,整个热闹的长街一刹那寂静下来,不管是行人还是商贩都将目光落在扶薇身上。
一袭龙胆蓝的柔纱襦裙裹着她婀娜又挺拔的娇躯,耀眼的蓝衬得她裙上胸口一片欺雪赛玉的白。珠帘面饰挂在鼻梁上遮了下半张脸,是含蓄遮面更是增媚的点缀。
习惯了满朝文武的跪拜,扶薇对这些灼热的目光毫不在意,她款步而行,径直朝着不起眼的代书小摊走去。
所有人都神色各异地打量着扶薇,唯有宿清焉浑然不觉专心读着手里的一卷书。
似乎街市的喧嚣不入他耳,奇异的安静也不被他所觉。
灵沼将小杌子摆好,蘸碧将怀里的软垫放在其上,扶薇才在宿清焉对面缓缓坐下。
宿清焉视线未离开书页,声音清润询问:“可是需要代书?”
扶薇有些诧异。原以为书呆子看书看得入了迷对周围一切浑然不觉,原来是她猜错了吗?
扶薇更细致地打量起面前的书生。于楼上窗前遥远,只觉他举手投足间脱俗优雅,与周遭格格不入,似坠落红尘的璞玉。如今近处端详,瞧出他更多的昳色。扶薇目光在宿清焉轻垂的眉眼多停留了一会儿,有些惊奇他的眼睫这样长。她从未见过男子有这样蜷长浓密的鸦睫。他坐在对面,润柔安和,岁月静好。
宿清焉抬起眼睛。
四目相对,扶薇一瞬间撞上一对静谧幽明的漆眸。平静、真实,又无暇。这样一双眼睛的主人恐怕是个良善到有些天真的人。
这枯燥又漫长的养病散心之旅,似乎找到了点乐子。
扶薇的唇角慢慢漾起一抹笑,贴着脸颊的珠帘跟着晃了一下,在落日余晖的镀照下,撞出闪烁的璀泽。
“好看。”她忽然说。
“什么?”宿清焉漆幽的眸中慢慢浮出疑惑。
“先生的字很好看。”扶薇垂眸,视线落在小方桌上的手抄。
字迹清隽,润如其人。
扶薇收回视线,重新与宿清焉对视,缓声:“烦请先生代写一封家书。”
宿清焉不言,直接拿过一张信笺。他一边研墨,一边问:“写给什么人?”
宿清焉左手执笔,准备妥当将要落字,仍未等到扶薇开口,他抬眸,望向扶薇,安静地等待着。
写给什么人?
宿清焉这个问题把扶薇问住了。她能给谁写家书呢?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都死光了,堂表皆不剩。恩重如山的养父母也不在了,留给她一个如今在宫里当皇帝的弟弟,想起这个弟弟……扶薇心里就来气。
“母亲。”扶薇念出这个有些遥远的称呼。
宿清焉落下这两字,又等了良久,也没等到扶薇再开口。他温声道:“若姑娘不知怎么写,可以告诉我想说什么事情,在下帮姑娘润词。”
“母亲应当正因我要成婚而欢喜,可男方家里既嫌我体弱短命,又怪我强势出风头,想要毒害我性命。我该如何告诉母亲?”扶薇抬眸,望向宿清焉。
宿清焉望着扶薇眼眸里的一汪幽潭,愣住。
扶薇慢慢移开了目光,垂眸轻声:“先生只帮我写……一切安好,这四字就够了。”
良久,宿清焉才收回目光,一笔一画地写完。
他放下笔,颔首轻吹信笺上的墨迹,直到浮洇的墨汁完全渗进纸张里。
“姑娘,不管遇到了什么难事,家人总是会站在你身后,相陪相助。”宿清焉双手捧上家书。
可是扶薇没有家人呀。
“多谢先生。”扶薇浅浅一笑,伸手去接。薄薄的一张信笺下,她指尖若有似无地轻轻碰了一下宿清焉的指背,又须臾离去。
扶薇若无其事地垂下眼睛,纤白的指捏着信笺,慢条斯理地将其从当中折了一道。
宿清焉静静看着她指上的动作。
扶薇抬眸对他笑了笑,而后扶着蘸碧起身。
走之前,灵沼放下两枚铜板。
宿清焉看向小方桌上的两枚铜板。可是……他帮人写家书向来是不收钱的。
不远处包子摊的许二等扶薇离去,立刻凑到宿清焉面前。不仅是他,周围几个商贩和行人也都凑过来,转瞬间将宿清焉的小方桌团团围住。
“清焉,离得近看得清,她是不是真的美得跟天仙似的?”许二急忙问。“她下半张脸戴着珠帘是有疤还是歪嘴?或者龅牙?你离得近肯定能看清!”
宿清焉看了许二一眼,再茫然环顾周围凑过来的一张张看热闹的脸庞。
他认真回忆了一下扶薇长什么样子,而后缓缓摇头,认真道:“没注意。”
浓密的鸦睫下一双干净的眸子将人望着,无辜又真诚。没有人会怀疑他说假话。
许二一噎,气得翻了个白眼:“你这个书呆子!”
其他人也一哄而散。
宿清焉的手虚握成拳置于小方桌上,拇指指腹不自觉地贴了一下食指和中指的指背。
他抬眼,望着不远处的垂柳。夕阳细碎的光粘在随风拂动的柳条上,仿若贴着娇靥轻晃的珠帘。
他真的没注意珠帘之下,他只记得她的眼睛。
宿清焉回头,人海里已然看不见扶薇的身影。
扶薇已经回到了绘云楼。她将信笺随手放在桌上,抬起手臂,蘸碧习惯性地帮她褪去外衣。扶薇外出归来第一件事必然是沐浴更衣。
花影早就将沐浴的热汤备好,扶薇沐浴过后换上舒软的寝衣,独自待在寝屋里。
以前总有处理不完的政务,如今空闲着,扶薇尚不能适应这种无所事事。她呆坐了一会儿,视线落在北窗下那一箱书信。
忽想起蘸碧的话,扶薇忍不住想阿斐会不会真的遇到了什么难事?
扶薇走过去,终于拆了一封段斐寄来的信。
只看了两行,扶薇就气得拂袖。信笺翩翩飘落于地,其上字字句句皆是一颗赤诚之心的款款深情。
扶薇不是陛下亲姐姐,陛下也不是太上皇的亲子。这事还要从多年前太上皇的一场恶疾说起。那一年向来龙体康健的太上皇突然瘫痪在床,言语也困难,不能处理朝政,只能退位。
可宫中并没有皇子。
太上皇便从宗亲中挑选新帝。许是太上皇寄希望于自己还能再康健,又或者想着日后将皇位还给自己的亲生骨肉,太上皇挑选了容西王独子段斐——段斐当年七岁,刚刚父母双亡,家里更是和朝中重臣毫无联络。
一个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权势的七岁幼帝,日子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那一年扶薇也只有十二岁,半大孩子罢了。荣西王夫妇对扶薇有大恩,她一直将段斐当成自己的亲弟弟。身为姐姐,她不得不强撑着,牵着弟弟一步一步往前走。姐弟二人经历过许多共苦的日子。
段斐被推到这个位子,只能迎难而上,不再有回头路。她要保护姐弟二人,也要争一口气。她希望阿斐长大成为千古流芳的明君,让天下不再有战乱和流民。
心怀希望,纵使熬坏了身子,纵使惨遭歹人毒害差点丧命,扶薇也不曾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弟弟对她的感情过了界,早就不再是姐弟之情。
当段斐抱着她的腿哭着说要丢下皇位和她逃到没人认识的地方生活时,扶薇直接气得吐了血。
她气他这有违纲伦的心思,更气他不争气将皇权天下当成儿戏!
一想到段斐的不争气,扶薇又觉得不舒服。一阵反胃,想吐吐不出,最终又变成断断续续地咳。这是当初中毒后催吐留下的后遗症了。
蘸碧小跑着进来,给她端来药。喝了药过去许久,扶薇才好受些,辗转睡去。
忙时睡得少没有精力做梦,扶薇最近倒是常常被梦魇缠着整夜,总梦到小时候逃亡的日子。
第二日傍晚,扶薇又出了门。既是来江南散心,哪有一直待在屋子里的道理。
她沿着长街缓步,偶尔在某个商铺或摊贩前驻足。不多时,恰好赶上孩童下学,几个孩童清脆笑着你追我赶往一家茶肆去。他们不是去吃茶的,而是蹲在茶肆外听说书先生讲故事。
“主子。”灵沼压低声音,“好像是在说您呢。”
扶薇听了听隐隐听见“长公主”,刚好又走得有些累了,便进了茶肆,找了个僻静地方坐。灵沼给扶薇在长凳上铺了软垫,又从自己带的水囊里给扶薇倒了温水。
“这个长公主是荣西王从外面带回来的,刚被带回府,就想爬荣西王的床!”
扶薇笑了。现在对她的编排已经这么离谱了吗?她被荣西王带回家的时候才六岁呢。
“所以说这个和皇家一点血缘关系没有的女人厉害呢!命好运气好,自己也有手腕。陛下登基之时年幼,朝野都在猜是平南王夺位,还是两位丞相主持大局,又或者摄政王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你们猜怎么着?”
天高皇帝远,在这偏远小县城的人竟能肆无忌惮地议论这些了。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长公主是出了李大人家的门,裤子还没穿好就往孙大人府上赶。她那宫殿人来人往,文官武将都能去。忙的时候,还要在外面等着……”
扶薇单手托腮,认真地听着。珠帘下的唇角勾着一抹淡淡的浅笑。
她突然想起好几年前,她学着史书上说的出宫体察民情,第一次听见外面的人如何用污言秽语编排她,接受不了,气得大哭了一场。
扶薇恍惚那个时候的自己还真是年纪小。她如今再听这些黄谣,已经浑然不在意了。
“李叔。”宿清焉立在茶肆外,提声打断说书人。
说书人正说得起劲儿,给宿清焉使眼色,让他有什么事情一会儿再说。
宿清焉就站在扶薇身后,一张长桌之遥。她听见宿清焉轻叹了一声。
“李叔,你说的不对。”宿清焉再开口,清润的声线越发坚定。
李四海愣住,嘀咕一声:“又来给我找事儿……”
蹲在茶肆外的孩童们交头接耳,又好奇地望向宿清焉。
李四海无语,朝着宿清焉走过去。两个人隔着茶肆的半墙,一里一外。
“你干什么?”李四海质问。
“你说的这些事情没有根据,都是些添油加醋的谣言。略加斟酌,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
李四海无语:“说书讲乐子,我又没说你家女人乱搞?众人听个乐子,没人介意真假。享福的长公主也没那么小心眼介意!”
“她介意。”宿清焉认真道。
李四海被宿清焉认真的样子唬住了。“她介意?她告诉你的?你认识她?人家是长公主,位高权重养尊处优,享了福被百姓议论两句怎么了?”
“人非神佛也,皆有喜怒哀乐,怎会不介意?不管她是什么身份,对是对错是错,不该因为她站在高处就要承受污蔑。”
李四海颇有几分气急败坏:“那你小子,就能保证我说的全都是错的?”
“不能。”宿清焉道,“李叔前几日说到前朝的几位掌权者或重臣时,讲的是建树功绩,而不是这些男女私事。长公主纵使私下混乱,也不该对她的政见成果只字不提,而是一味说些不能确定的荒唐事。”
“李叔,若是私下闲谈,晚生绝不置喙。可这些孩子在听。您对孩子们说这些,不合适。”
宿清焉向后退了一步,深深作了一揖。
李四海望了一眼外面的孩童,气得胡子都在颤。他指着宿清焉,半天憋出来一句:“怪不得都说你有病!”
李四海转身,恼声:“今天不讲了!”
一个孩童站在宿清焉身边仰起小脸,问:“他真的是瞎说的吗?那先生跟我们讲一讲长公主吧!”
宿清焉微笑着:“我不认识长公主,不能妄议。”
宿清焉转身离去。孩童们围绕着他。——宿清焉有时候会去学堂给孩子们上课,是他们的老师。
听着那些稚嫩的童声渐远,扶薇才慢慢转过身,若有所思地望着宿清焉如松柏挺拔的背影。
原来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人。如白纸一般的人,欺负起来会有负罪感吧?不过……应当也会很有趣吧?
第二天,扶薇再次出现在宿清焉的代书摊前。
她不坐,宿清焉抬起眼睛仰望着她。
“我这里有一份繁琐的差事,只有先生能接手。”扶薇微笑着开口。落日荼蘼的光斑令其珠帘闪烁,不敌她眸色璀然。
扶薇淘来些闲书,有些书年岁长了破旧不堪。她要请一个抄书人,为她重新誊抄一份。
扶薇说完需求和报酬,等着宿清焉的答复。
宿清焉沉默望着扶薇,半晌才开口:“你识字。”
扶薇坦然回望他,唇畔慢慢漾开柔笑:“我也没有说过我不识字。先生更没有说过不给识字之人代书。”
宿清焉想了想,确实如此,就此揭过,道:“我单日要去学堂授书。”
“那双日静候先生。”
宿清焉还欲再言,扶薇已经转身离去。婀娜的身影走进人群,渐远。
宿清焉刚要收回视线,看见两个人似乎在跟着扶薇。水竹县地方不大,互相就算不认识也打过照面。这两个人游手好闲,在水竹县是人人嫌又人人不敢招惹的二流子。
“清焉!”许二又跑到宿清焉面前,挤眉弄眼:“她怎么一直找你,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
“没有。不要这样说,影响姑娘家的名声。”宿清焉垂眼,重新将目光落在书页上读起书来。
许二摸了摸鼻子,有些无趣,不过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宿清焉,对他这反应也不算意外。
“对了,昨天你又去找李四海麻烦了?”许二问。
“没有。”宿清焉否认,“只是说理。”
许二幸灾乐祸地笑着说:“昨儿个傍晚,李四海回家的时候,在双燕胡同被人揍了,四颗门牙都没了!哈哈,最近都不能去胡诌了……”
宿清焉对这些闲事没什么兴趣,继续读着书卷。待许二走了,他望着满页文字慢慢皱了眉。
双燕胡同?他昨天傍晚好像去了那里。
宿清焉漆亮的眸中慢慢浮现疑惑。他去双燕胡同做什么?那并不是回家的路,甚至是与回家相反的路。
应该是记错了吧。
他摇了摇头,继续心无杂念地读书。
扶薇沿着长街闲逛了一会儿,在一个卖花的小姑娘前驻足。小姑娘亮着眼睛望着她,试探着小声问:“姐姐要买花吗?”
像扶薇这样的人,一眼看去就和小县城里的人不一样,小县城里的人摸不清她的底细,颇有几分不敢得罪的远离。
扶薇扫了一眼,随手一指。蘸碧立刻蹲下来,拿着一方帕子包着花枝递给扶薇。鲜花离得远瞧着不错,可送到眼前了,才瞧见已经有些蔫了。
不过扶薇还是将花买了。
“谢谢姐姐!姐姐你真好看!”小姑娘高兴地站起来。
扶薇没什么反应,转身离去。
只是蘸碧多给了小姑娘一块碎银。
扶薇如今体力大不如从前,这就要回了。她刚转身,就看见远处树后有人鬼鬼祟祟地朝这边看。
蘸碧低声:“跟了一路了。”
扶薇点点头,早有所料。所谓财不外漏,像她这样招摇,难免会惹恶人生歹心。
不过扶薇还不至于把几个地痞当回事。
第二日,宿清焉去学堂给孩童上课。暮色渐染时,他姗姗来迟,在街角摆好小方桌,继续翻阅未读完的书。
人群熙熙攘攘,他孑然自处。
天色逐渐黑下去,沿街商铺一盏盏亮起灯。宿清焉抬头,望向显眼的绘云楼。绘云楼一片漆黑,没有掌灯。
雨滴忽然坠落,打湿他珍惜的书。他将书收进牛皮纸袋又仔细藏进怀中,然后慢慢收拾其他东西。雨越下越大,他却完全不急。在小跑着归家的人群里,宿清焉闲庭信步,任雨浇身。
这一场雨下了一整夜,时大时小,天亮时方歇。这一场雨一下子将春送走,江南的夏日突然降临。枝头的蝉声好似在一夜之间变得更加响亮。
午后,宿清焉如约去了绘云楼。
蘸碧将他领进二楼的书房,微笑道:“先生先坐,我去请我家主子。”
“多谢。”宿清焉道了谢,仰头望着满墙的古籍。
书房并不是一间屋子,而是将二楼的大厅改成了书房。一座座书架上摆满了书籍。尤其是北墙更是整面墙都被书卷填满。
宿清焉是嗜书之人,立于书海之中,不自觉将呼吸放得轻浅,直到脚步声敲回他的心神。
宿清焉后知后觉地转过身。
扶薇一手搭在楼梯扶手上,一手提裙,垂眸踏下一级级楼梯。蓝白相叠的纱裙如云似雾围绕着她,她整个人仿若也腾云驾雾而来。走廊尽头的小窗有热风灌入,吹起她的裙摆晃动,裙尾下若隐若现一小截光着的脚踝。
几乎是视线碰到她脚踝的那一瞬间,宿清焉立刻守礼地收回目光。
“先生。”扶薇迈下最后一级楼梯,轻唤了一声。
宿清焉望过来,看见她没有戴珠帘半遮的芙蓉面。宿清焉的目光停滞了一息,温声问:“哪些书需要誊抄?”
“先生稍等。”
扶薇款步走向一座书架,随意拿了两卷书,放在书案上。宿清焉跟过去,立刻研磨誊抄。
一立一坐,扶薇立在书案旁垂眼看他浓密的眼睫。若是拨弄起来不知道是怎样的触觉。她的手轻轻搭放在书案上,指端于桌面悄无声息地捻了一下。
可这样天真的人,钱权似乎都无用。强囚也没什么意思。
宿清焉刚开始抄录,扶薇捧了一盒香器而来。
宿清焉于文字间抬眸,入眼,是她执着香扫的纤柔玉手。
残余的香灰被她轻扫,飘起又落下,细密似避不开的红尘。
“呲”的一声响,火折子迅速亮起一簇光,也燃起一股香。
扶薇将盖子放上,一道香从孔洞升出,倔强地笔直而燃。
“抄书枯燥,给先生燃一炷香。”扶薇言罢抬眸,对宿清焉施施然一笑,不等他言,已经转身而去。
扶薇没有回楼上,而是拿了卷书坐在窗前的软椅里打发时间。
窗外夏日的光将整个书阁照得大亮,纤尘可见在光线下跳跃。
她于窗前而坐,照进屋子里的大捧日光都先拥过她。宿清焉看向她,她坐在日光里,好似成了光源。
宿清焉又很快收回目光,专心抄起书。
“啪”的一声响,是扶薇手里的书落了地。
宿清焉抬眸,见扶薇不知何时睡着了。
而这卷书的落地声又将她吵醒。扶薇蹙眉醒来,如画的眉眼间浮现几分不悦。天气突然热起来,她脊背浮了一层香汗。这份炎热让她身体不太舒服。她甚至没心情顾及宿清焉,径自回到楼上沐浴。
沐浴之后,仍觉不适,又是一阵干呕,喝了药,她昏昏沉睡去。待她醒来,已经是落日时分。
摆脱不了的糟糕病身,时常让扶薇情绪低落。
当扶薇走到书阁,微微泛着紫的暮霭洒进屋内,宿清焉坐在暗下去的书案后抄书,一下午没有起身。
扶薇神情恹恹地立在门口望了他好一会儿,才走向一座书架取了本书。
“换一本书抄吧。”扶薇将书册放在宿清焉面前。
宿清焉也不多问,直接将书拿过来。将其打开,才发现是本写满淫词艳曲的床笫欢记。
宿清焉不言,拿了本空白册子,开始抄录那些不堪入目的词句。他神色无常,仿佛誊抄的句子和刚刚那本严肃的史书并无区别。
扶薇垂眼看着他快要将一页抄完,才开口:“我是故意接近你的。”
宿清焉习惯性地将一句话写完才停笔,他抬眼,平静望向扶薇,道:“我知道。”
扶薇与他直视:“既知为何不避?”
宿清焉不答反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姑娘的吗?”
扶薇望着他,微微蹙了下眉,默了默,才说:“先生帮我写一份婚书吧。”
宿清焉因为她这摸不着头脑的提议愣了一下,想起上次帮她写家书时她所言,宿清焉想着兴许是和她那门不太好的婚事有关。
他从一旁拿了一张红纸,问:“新郎和新娘的名讳?”
“先空着。”
宿清焉不多问,将婚书写完,放下笔,看向扶薇,问:“还抄书吗?”
扶薇望着他这双永远平静的眼眸,沉默了一会儿,才道:“我抛头露面经商本就遭家里人不喜,如今婚事有了变故,又怎敢告知母亲让她忧心。”
宿清焉无意探听别人的私事,可有人对他倾诉,他会认真地听。听着扶薇轻远的声线,他眼前浮现扶薇上次说到“一切安好”时的眼睛。
柔情沉静,藏着故事。
扶薇站得久有些累了,她微微倚靠着长案,垂眸去看书案上的婚书,缓声:“我想母亲来看我的时候,我有夫君在侧,琴瑟和鸣。”
宿清焉皱眉。
他刚欲开口,扶薇抢先道:“我身体不太好随时都可能去世,想来先生是不愿意做实克妻之说的。”
“我……”
“又或者先生嫌晦气,不想沾染重病之人。”扶薇轻轻一声笑,“一年就好。一年之后我要么病死要么离开了这里。到时候绝不再给你添麻烦。”
她提笔,在婚书上的“携手一生”的“生”字上划了一笔,改成“年”字。
宿清焉看着她这举动,语塞了半天,只无奈吐出一句:“你别胡闹。”
扶薇转眸望向他无奈的样子,终于在他永远平静的漆眸里看出别的情绪来。
扶薇拿起书案上的婚书递向宿清焉。
“你能帮我的,就是在这婚书上写下你的名字。”她深深望着他,潋滟的眸中漾起柔情的魅,“宿郎。”
四目相对,宿清焉安静望着她的眼睛,没接婚书。
若是小人,这样的好事必然高兴接受。所以有时候和君子打交道还不如和小人做交易。
扶薇轻轻叹息了一声。
她半垂了眉眼,用带着几分忧虑的声线低语:“之前想过许重金或权势威压,可这些应该对宿郎皆无用。宿郎是君子,对待君子只能用别的法子。”
扶薇将婚书放下,开始宽衣。
看着柔丝腰带缠在她纤细的指上被徐徐扯下,宿清焉才反应过来她在做什么。他一下子站起身,向后退了一步,狼狈地转过身去。
“姑娘这是做什么?”
扶薇瞧着他这反应觉得有趣,先前因病身的低落一扫而空。她饶有趣味打量着宿清焉的神色,手上动作并不停。
衣衫缓缓落地。
她慢悠悠地轻声慢语:“也不知道用责任要挟,对君子有没有用呢?”
宿清焉视线落在墙壁上,墙壁上映着两个人的影子。他的目光不由自主落在扶薇的影子上,他问:“你的下人在哪里,我去叫她们。”
“避开了。”
扶薇双手绕到腰后,去扯小衣后脊上的系带。
她的动作清楚映在墙壁上,宿清焉急声:“姑娘喜洁,落地的衣裳应该不愿捡起再穿。下人既然不在,我可否去姑娘闺房帮你拿衣?”
“你是我什么人?怎么能进我的闺房?”
宿清焉语塞,轻叹一口气,他突然转身,拿起桌上的笔,在那婚书上行云流水写下自己的名字。
扶薇看愣了。
就这?
他这就答应了?她才刚开始逗他啊。
宿清焉放下笔,仍旧不去看扶薇,低着头道:“姑娘身体不好,如今虽到了夏日,可晚间的风还带着寒气。如此之举若着凉,是给病身雪上加霜。还望姑娘多多爱惜自己的身体。”
扶薇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呆子。
宿清焉轻咳了一声,再问:“现在能去姑娘的闺房拿衣服了吗?”
扶薇回过神,道:“门口的柜子里就有。”
宿清焉立刻走到柜子那儿,拿了一件长袍递给扶薇。扶薇迟疑了一下才伸手去接。她完全不觉得冷,甚至觉得有些热。可还是将袍子裹在身上。若不然,她怀疑这个呆子不会再抬头看她。
宿清焉又叹息一声。他终于抬眼,定定望着扶薇的眼睛:“若姑娘需要,清焉愿意相伴。只是希望姑娘不要一时冲动,不能因为别人的错误反而伤害自己。时辰不早,我先走了,姑娘早些休息。”
宿清焉向后退了半步,工工整整地朝着扶薇作了一揖。
扶薇捏着衣袍未系的衣襟,问:“明天过来吗?”
“明日是单日。”
扶薇轻笑一声,轻轻的笑柔柔吹入宿清焉耳畔,带来一阵酥痒。
“那后日来吗?”
宿清焉垂眼,视线里是书案上那张婚书鲜红的一角。
“来。”
扶薇满意了:“慢走。”
宿清焉转身,刚走了两步,忽想起一事,又回过身,迟疑了一下,才开口:“还不知道姑娘名讳。”
“扶薇。”
扶薇拿起书案上的笔,在那张婚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后提着婚书给他看。
——浮薇。
宿清焉看了一眼她的名字,轻颔首,转身辞去。
扶薇一直站在原地,听着宿清焉下楼的脚步声,直到他的声音彻底听不见。
良久,她走到窗口架起窗扇。可外面漆黑一片,并寻不见宿清焉的身影。
而此时的宿清焉已经被蹲守在绘云楼外的两个地痞拉进了阴暗的小巷。
“那女人身边有多少人?钱财都放在哪儿?”
“你不是会写写画画吗?现在把绘云楼里面的布置画出来!”
“齐哥,干脆让他带着咱们翻窗进去吧!蹲了那么久,我已经等不及了!那娘们神神叨叨的,还不是会被咱们降得服服帖帖。”
紧接着又是好些句污秽之语。
宿清焉皱眉,听得有些生气。
另一个人拔出一把匕首,森然的光在夜色里闪出一抹寒意。他拿着匕首逼近宿清焉,威胁:“你小子老实点,要不然宰了你!”
宿清焉浓密蜷长的眼睫轻轻扇动了一下,他望着匕首的目光里缓慢浮现一抹好奇。
他若有所思地歪了下头,清隽如玉的面庞霎那间浮现一个诡异的笑容。